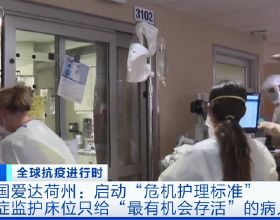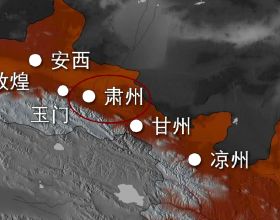1986年10月的一天,老山和者陰山頻繁地傳來炮聲。在後方的戰地醫院裡,一位帶著紅十字袖標的女戰士正在吻著一名傷員,一位叫王紅的戰地記者站在一旁的按下了快門鍵。
這張照片是擺拍的,準確地說是對前幾天發生的一幕的補拍,後來這張照片刊登在各大報紙的頭版,被命名為《死吻》。
而照片中的原型人物分別為戰士趙維軍和衛生員張茹。
越南人不服,兩山輪戰
1979年3月16日,我軍完成對越南的懲戒性打擊,解放軍全線回撤至國內,就連中越邊境地區的制高點地區也沒有軍隊留守,僅執行一些邊境巡邏任務,維持邊境治安。中國政府本想與越南政府進行邊界談判,用和平的方式徹底解決中越邊境問題。
越南人在前一個月的自衛反擊戰裡吃了大虧,表面上和和氣氣,在私底下卻調兵遣將,將大量部隊集結在北部邊境,佔領了中越邊界上的一些制高點。
此時的中越兩國正在圍繞邊境問題進行談判,我方對此也不好發作,但越南得寸進尺,不斷向我國境內發射炮彈,甚至是派出小股部隊越境騷擾我邊民,邊境地區百姓的生活再次遭到炮火的威脅。
從1979年從越南撤軍到1984年發動兩山輪戰之前的四年時間裡,越南軍隊炮轟或掃射我國麻栗坡高達690餘次,累計發射炮彈達28000餘發,造成我國邊民傷亡三百餘人,三百餘座村落被迫內遷,一百多座房屋被炸燬,一萬多畝經濟作物田完全被毀,兩千多畝農田不能耕種。在這種情況下,有家不能住、有田不能耕,中央軍委對此已經是忍無可忍。
1984年,我國已經經濟體制改革5年多時間,國內經濟狀況已經大幅改善,中央認為有能力支撐起一場邊境新的反擊戰。於是中央軍委突然決策,要再次發動一場較大規模的,對越還擊作戰(兩山輪戰)。
其實對越還擊作戰,還有另一層的戰略意圖。就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越南正在加緊對柬埔寨的入侵行為,想要在中南半島上構建印度支那聯邦,對越還擊可以緩解柬埔寨與泰國方向的壓力。
1984年中央決定對越還擊作戰,中央軍委決定動用優勢兵力,對中越邊境地區的制高點發動進攻。集中優勢兵力,採用速戰速決的方法,要以最小的代價拿下制高點,化被動為主動,徹底轉變在邊境問題上的防禦態勢。
並且要在正面給予越南軍隊足夠大的壓力,支援柬埔寨和泰國反抗越南的鬥爭。經過研究之後,中央決定從廣西雲南兩線出擊,分別對被越軍侵佔的老山、者陰山兩地發動攻擊。
老山、者陰山相距距離較遠,而又位置偏僻,距離敵方中心城市較遠,是越南軍隊的薄弱點。高山峻嶺,地形地勢十分複雜,對於部隊集結與後勤運輸十分不便,我軍對這兩地的攻擊可以隨時改變戰爭規模和戰爭動態,想打就打,想走就走。
因此在1984年4月,中央軍委作出決定:發動對越南自衛還擊作戰。
1984年4月28日,昆明軍區一個師對我國雲南境內老山一線展開法規的攻擊,經過一日的攻堅戰,老山一線越南軍隊的防線被全線拔掉。40師在7分鐘內就收復老山662.6高地,僅用5小時20分鐘就攻上了老山主峰。
當日下午,40師下屬兩個營繼續向前推進,越南軍隊佔領的十餘個高地也相繼收復。4月30日,11軍31師以傷亡不到百人的代價,佔領者陰山全部制高點,越軍兩個連隊遭到我軍全殲,越南軍隊三個團建立的防線瞬間土崩瓦解。
收復老山、者陰山之後,為防止越南軍隊的繼續進犯,也為了拖住越南軍隊對柬埔寨和泰國的入侵,中央軍委決定在兩山地區對越南給予持續性的壓力,這場還擊作戰持續了十年,史稱兩山輪戰。
趙維軍犧牲
趙維軍,甘肅省榆中縣魯家溝村人,1965年出生,1985年1月入伍,中國共產黨黨員,1986年7月24日犧牲,榮立一等功。
對老山、者陰山第一波攻勢結束之後,中央決定實行輪換制度,每個軍區輪流到前線作戰,而趙維軍所在的部隊1986年被派上戰場。
1986年4月30日,蘭州軍區第47軍共3萬餘人奉命進駐梁山地區,此時的趙維軍是蘭州軍區47軍141師421團的一位副班長戰士。
戰爭動員發起後,趙維軍隨47軍全體將士一同在文山州完成了戰前集訓,之後便趕赴梁山地區,接手濟南軍區67軍的的作戰任務。
趙維軍被分配在老山的毛松嶺,負責毛松嶺的一線防守任務。從這之後,趙維軍就像是一顆釘子一樣,死死地釘在了這座越軍進攻老山的必經的山頭上。
老山的生活條件很艱苦,越軍頻繁向山頭上發射炮彈,趙維軍和戰友們只能躲在低矮潮溼的山頭上,抵禦敵人的炮火攻擊。
在炮火攻擊之後,往往會有偷襲或者衝鋒。在短短的3個月時間裡,趙維軍和戰友們已經打退了敵人近百次的偷襲行動,也頂住了數萬發炮彈的轟炸。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僅僅在駐守毛松嶺的三個月之後,趙維軍的生命便走向了終點,他永遠屹立在了毛松嶺的山頭上……
1986年的毛松嶺山頭上,佈滿了越軍遺留下來的地雷,稍不小心就會觸雷。7月的一天,越南軍隊像往常一樣發動炮擊,一顆炮彈在趙維軍身旁落下,一顆地雷因此被觸發,瞬間地雷的碎片炸進了趙維軍的身體中,趙維軍身負重傷。
短短几分鐘後,地雷爆炸引發的劇痛使得趙維軍昏死了過去,戰友見此狀況,迅速將其轉移到後方。
此時的趙維軍已經昏死了過去,是死是活不得而知,而野戰醫院的醫生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奮力搶救。張茹等幾名護士抬著重傷的趙維軍,一路狂奔,將趙維軍送到了手術室。
雖然是戰地醫院,但也只是幾個帳篷搭起來的臨時救治所。不要說是醫療裝置,連醫生和藥品也是短缺。最終在選擇留命還是留雙腿的兩難境地下,醫生截去了趙維軍的雙腿,得以保全了性命。
由於戰地醫院條件簡陋,趙維軍剛剛逃離了死神的魔爪,傷口卻再次感染化膿,趙維軍也因此高燒不退,進入了昏迷狀態。
張茹等人當機立斷,乘著趙維軍傷情還未繼續惡化,幾個人抬著擔架想將趙維軍送去好一點的後方醫院。
在途中,趙維軍的身體狀態突然惡化,趙維軍意識也時而模糊時而清醒,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傷情不容樂觀。
張茹也知道,如果趙維軍不能馬上得到救治,那他的時日剩下的也不多了。某一天清醒的時候,趙維軍跟張茹說:
把我的頭朝著自己家甘肅的方向,你們也停下來歇一歇吧。
運送隊伍停下後,趙維軍對著家鄉的方向說道:
爸爸媽媽,為國盡忠我做到了,我無怨無悔,但是我不能為你們二老盡孝了,你們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啊!
在最後,趙維軍有些欲言又止的樣子,因為在他的心中,也期待著一顆愛情的種子萌發。張茹見他欲言又止的樣子,便鼓勵他道:
還有什麼要說的,就說出來吧。
終於,趙維軍鼓起了勇氣,對著張茹說道:
姐姐,你能抱抱我嗎?我十八歲了,可還不知道愛情是什麼,就這樣走了會有些遺憾。
張茹聽了,既心酸又悲痛,站在一旁抹著眼淚,她俯下身體抱住了趙維軍,輕輕地在趙維軍的額頭上吻了一下。
趙維軍笑了笑,非常滿足,似乎心情很好的樣子。
當日,老山上的天氣很好,太陽穿過樹林,透過樹葉照在趙維軍的臉上,斑斑駁駁地隨風搖動,趙維軍的臉上的光點忽明忽暗。
忽然一片雲朵飄過天空,陽光逐漸消失在了雲層之下,趙維軍在張茹的懷中,閉上了眼睛,黯然離世。
一張擺拍的照片
趙維軍犧牲之後,一位叫做王紅的攝影記者走進了老山戰區。無意間王紅打聽到了張茹,張茹講述了她與趙維軍的故事。講到趙維軍慢慢地閉上了雙眼,走完了他短暫的人生時,王紅感動不已,當即決定,要將這裡的故事講給全國人民聽。
王紅希望張茹能夠幫助他,補拍一張張茹吻趙維軍的照片。最終在多方協調下,王紅補拍了張茹吻趙維軍的那一幕。這張攝影作品被命名為《死吻》,向全社會刊發。
照片中一位佩戴紅十字袖標的女衛生員,揹著一把步槍,俯身抱著一位身負重傷的戰士,並緩緩地親在了這位戰士的臉頰上。
由於這張照片擁有極強的社會傳播能力,因此這張照片一度被社會認為是真實抓拍的圖片。但是從照片的布光和場景上來說,這是一幅經過構思的照片,抓拍的圖片很難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對此王紅後來也多次澄清,這是一張藝術攝影照片,王紅自己後來談起過這張照片,他說道:
這張照片我從未標註過‘新聞攝影’。
用當下的攝影分類,這張照片屬於“觀念攝影”的範疇。
這張照片還曾入選過攝影國展,但由於種種原因沒能進行展出,當年《大眾攝影》雜誌還因為此張照片產生過爭論,最終走向了兩個極端。評委之間就《死吻》是否能獲得金獎,以及是否能夠入選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正方認為這張照片揭示了戰爭中的人性,是難得一見的紀實類攝影作品。而反方則覺得這張照片是補拍的,且照片內容不符合中國國情。最終反方說服了正方,《死吻》這張照片被取消了參展資格。
即使是補拍,《死吻》所帶來的積極意義也不亞於一個獎項,這張照片是整個對越還擊作戰的一個縮影,是兩山輪戰中的一座豐碑,是前無古人的。
照片是否有藝術性不是普通人討論的範疇,而我們要記住的,是這張照片背後的那兩個人,趙維軍和張茹,以及全體人民解放軍。
張茹後況如何
張茹,1965年出生,江蘇揚州人。1983年10月入伍,1985年11月奔赴雲南參加兩山輪戰。
老山作戰期間,她擔任“戰地女子救護隊”的隊員,參加了搶救一等功臣徐良、排雷大王駱牧淵、一等功臣趙維軍的救治工作,著名戰爭題材作品《死吻》的原型人物。
兩山輪戰結束後,張茹退出現役,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但戰爭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她始終無法忘懷一個接一個的戰友在身邊倒下。
戰友們回不去了,張茹想去見見那些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們的故鄉,去拜訪他們的家屬。
2011年,張茹已經年近半百,他覺得他應該做一些什麼,來延續戰友們的生命。在工作之餘,張茹蒐集了很多資料,想要去祭奠這些曾經的戰友。
張茹和戰友們發起了一場使命之旅,用5年的時間,走遍了9個省份和32個縣,幫忙去的戰友們看了看他們的故鄉,看了看他們的家人。
2015年勞動節期間,張茹與來自全國各地的戰友們聚集在甘肅省榆中縣烈士陵園,祭奠趙維軍烈士。張茹撫摸著趙維軍烈士的墓碑。張茹淚如雨下:
“為國捐軀的戰友們啊,我是你們的精神血親!29年前我擁抱你的那一刻,你是否能聽到我的心跳。如我能留住你的微笑,我願意一直抱著你,儘管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擁抱。”
滿含熱淚,道不盡對戰友的思念與緬懷,那段歲月依舊可歌可泣。
後來有記者問到張茹: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還會當兵嗎?
張茹說:
我外公是一名老紅軍,《東進序曲》和《南征北戰》都能看到我外公的身影。我父母也長期從事航空科研工作。所以我參軍是必然的,是刻進骨子裡的。
戰友已經越走越遠,張茹帶著戰友們的希冀,重新走上了“回家”的路。每走到一個戰友家,家屬與張茹都是痛哭流涕。
張茹的行為也逐漸引發社會各界的共鳴,越來越多的老兵,開始尋找犧牲戰友的故鄉,去緬懷曾經身邊的,那一個個有血有肉,為國犧牲的戰友。
他們的韶華已經不再,而犧牲的戰士永遠沉睡在了老山、者陰山的山頭上,但他們的精神不會消失。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人會站出來為他們證明,他們曾經來過這個世界,他們做的事情,是為了身後的人。
就像是《芳華》的經典臺詞:“一代人的芳華,早已刻上了時代的印記,成為永遠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