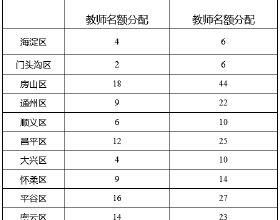一座山,像一堆燒軟了的蠟,努力地往下墜。
太陽露出山脊,像一張透明紅圓餅,踟躕著不肯出來,突然,跳一下,在山巒上旋轉,又靜止在那裡。
幾個後生,守在豬圈門口,正在往外趕年豬,豬似乎已經知道大限已到,蜷在裡面不出來。後生將繩子綁在豬腰上,豬嚎叫著,被拽出來。兩邊躍躍欲試的後生猛撲上去,拽尾巴的,捉耳朵的,被拉到木板上。
老嫗腿抽筋似的軟,唸叨著出門看,早晚飼養,她和豬有了感情。一個腰捆麻繩的後生,左膝壓豬脖子,刀把在豬脖子磕兩下說:怪刀子,不怪人,插豆腐一樣,尺五長的刀刃不見了,殷紅的熱血蛇一樣順刀刃扭出來,流進放了鹽的盆中。
楞窮一年,不窮一天。兒子打工,媳婦城裡供孫子唸書,過年才得團圓一次,殺頭豬好過個團圓年。
二
一群人,笑著從車上跳下來,腋下夾著尼龍袋,朝同一個方向走去。司機伸出車窗,大聲叮嚀,兩點半發車,準時來,那群人回過頭,稀稀拉拉回答一聲,消失在人流中。
菜市場,幾個女人昂著頭走。“辣子三元五,蘑菇一塊,大白菜一元。”攤主大聲喊,她們繼續昂著頭,眼睛斜看著,耳朵聽著,不應聲,一路走一路比較著價錢,生怕一搭聲就脫不開身。
看夠了,比到了,才選準了一家,是她們平時的熟交。來了噢,今兒想要些啥,攤主堆著笑問。
後生挺著肚子,端著一箱年集,架到車上,少婦拎著大袋小袋的菜,也架車上,公交車坐滿了,她們眉飛色舞,興尤未盡談論著花了多少錢,賣了什麼東西,把什麼忘了,此刻,她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男人在外打工,將錢交給女人,由她們任意花。
三
臘月的天,多陰沉著臉,雪片不緊不慢落著,一顛一顛的。
一個女人,擔著一擔土糞,一閃一閃,盪盪悠悠,從土路上下來,她將土糞倒在地裡,用凍土疙瘩苫了,朝著對面的村莊唱起秦腔來。
祖籍陝西韓城縣,杏花村中有家園。
姐弟姻緣生了變,堂上滴血蒙屈冤。
……
霧從對面的溝裡湧出來,霎時爬上山頭,樹林和村莊若隱若現。女人略微沙啞的嗓音穿透濃霧,傳到山頂的村子,惹得小狗狂叫,公雞打鳴。
有霧的早晨,是最讓人相思的時候。
農閒時間,舉辦廟會,戲是必不可少的,是本縣劇團。明天才演戲,街道兩旁卻佔滿了攤位。
城裡的女人回來了,也帶來她們的燒烤裝置,擺在街道兩旁,有賣菜的,豆腐蔬菜肉,應有盡有。
閒置的空房臨時搭起鍋灶,麵食肉食都有。一時間,小街道變富態了。從遠方來的親戚,大把大把花錢,比過年還排場。
四
一群麻雀從梨樹上旋下來,跳躍著覓食,尾巴一翹一翹,太陽給土院子抹了一道金黃。
女人坐在炕上,聚精會神的扭草辮,麥稈上下翻飛。短的沒了,嘣,輕輕咬斷,接一根繼續扭,白色的草辮在女人的腿圈裡盤曲成一堆。
一陣香味鑽進女人的鼻子,“洋芋熟了。”女人丟下草辮,溜下炕,火鉗往外夾洋芋。貓“咪兒咪兒”叫,伸懶腰跳下炕。女人鉗出洋芋,在爐盤上磕幾下,焦皮,土灰抖落在爐盤上。輕輕掰開,“噝”,熱氣衝出來,一半遞給剛睜開眼的男人,一半扔給貓,貓圍著燒洋芋打轉兒,下不了口,幹叫喚。
五
太陽剛冒花子,此起彼伏響起雞唱聲。兩隻喜鵲在柳樹上朝著上房喳喳不停地叫,尾巴一翹一翹的。
三個男人,在大門口兩面釘四根木樁,綁好繩車,幾疙瘩胡麻毛線放在旁邊,男人捏著線頭,在木樁之間來回跑,麻線疙瘩隨男人來回滾動。拖搖柄的男子,甩開兩臂,開始搖動,分散的線慢慢合成四股,漸漸緊起來,坐著吸菸的男人撿起破鞋底,捏起一根,“噝”跑過去,繩子馬上鬆下來,捏起另一根又跑。繩子合緊了,兩個男人雙手捉著繩頭,啪啪啪一陣猛摔,然後二四對摺放下。
六
牛“哞”地一聲長叫,就把太陽拉到房脊上,男人坐在房廊上,將剛割來的榆樹條用刀破開,接著舊茬編糞簍,新生的榆樹條既細又勻,也柔軟,編的簍耐用又結實,雖然笨重了些,用起來格外應手。
女人坐在炕上磨洋芋,哧哧哧幾下,半個洋芋沒了,摩鑔下面堆起白色的汁液,先磨的汁液已經變紅。
女人把一勺面倒進磨好的洋芋汁液裡,攪拌均勻,舀一勺子倒進油鍋裡,再用鐵鏟刮均勻,一會兒剷起來一張薄餅。案板上已經壓了一沓洋芋麵筋,女人切成細條,和臘肉一塊炒,飄了一院子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