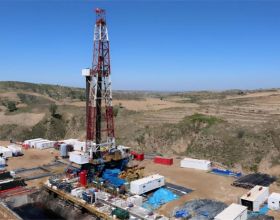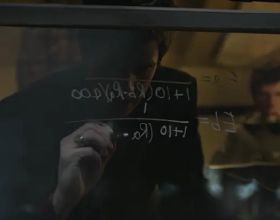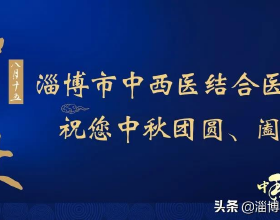王軫走後,杜衡將信將疑。先前幾位醫生開的藥都很奇特:蜂房、頭髮、銅鏽、蛇皮、槐花……王軫診治時太草率,開的藥也太平常,她抱著試試看的想法,依照吩咐讓姆媽服藥。
第四天晚上,杜衡來到姆媽床前探視。姆媽猛一把拉著她的手不放,淚水順著眼角直流,臉憋得通紅,喉嚨裡咕隆咕隆直響。杜衡嚇壞了,急忙喊陳媽。
“衡兒……”姆媽一聲輕喚,細如遊絲,可在杜衡聽來,無異於空谷足音、三伏炸雷。
“姆媽,姆媽,是您喊我麼…… ”
“我的兒啊!”兩人抱成一團。聞聲趕來的陳媽也高興得直抹淚。
第二天,姆媽就完全可以說話了,只是身體還弱,一時起不了床。杜衡命陳媽在門口擋住所有的客,她要專門接待王軫以表謝意。劉松竹自然是主要的陪客。她清晨就開始著意打扮,描眉、抹粉,後又覺不美,乾脆洗去了。她拿起琵琶、三絃調了調音,想彈上一曲練練手指,又彈不下去,乾脆下樓去等著。慌慌張張地惹來了剛進門的劉松竹的調笑:“別急,是我,棄愉還沒到呢。”
沒想到七等八等,只等來位麻臉青年席特庫。
“師傅正準備出門,從北京來了位朋友,有事與他商談,來不了了,託我將這劑藥送來,說病者服後就可痊癒。”
劉松竹暗笑:這傢伙也吊起胃口來了。
杜衡囑咐席特庫:“回去告訴你師傅,就說我姆媽已能說話了,我不便前往致謝,請他拔冗前來寒舍容我們表表心意。”
“我一定把話帶到。”
“小兄弟,這樣疑難的病症,你師傅怎麼診察出來的?”
“聽師傅說,新建之宅,溼氣尤重,病人心氣本來較虛,加上飲酒後毛孔大張,溼氣乘虛而入,致病人失音。”
“你師傅的藥怎麼這樣靈呢?”
“聽師傅說,此病倒古已有之,有醫案可查,他不過依樣畫葫蘆。”
愈說得平淡愈顯出王軫的神奇,杜衡陷於沉思遐想之中,以致席特庫什麼時候走的都不知道。
王軫沒來,杜衡覺得飯菜也無味了,好在劉松竹談起了席特庫的故事才又勾起了她的興致:
“這“席特庫”是滿文,意為“尿炕的孩子”。他是京城一個旗兵的獨生子。棄愉在京那年,他只十歲,突患急症,高燒不退,渾身發紅發燙,像火炭一樣。好多醫林高手見之即走。夫婦倆跪求棄愉。棄愉診視後說‘有兩條要講明:一是診好後面容難保,二是診治時慘不忍睹,如同意我就下手'。夫婦倆只叫‘快請快請’。
棄愉傍晚時將病孩綁在草塘邊的樹上,拿皮鞭抽得他鮮血淋漓然後退至幾十尺以外。入夜,蚊子聞到血腥味飛來叮滿他一身,哭叫聲呼天搶地。其父母和圍觀者不忍,都要上去解救。棄愉厲聲喝退,半個時辰後才令將病孩抱回家中,當夜,孩子天花猛然發作,高燒退去,撿了一條命,留下一臉疤痕。其父母硬讓席特庫給棄愉當小廝以報恩。棄愉見其誠實好學,就收他為徒了。一晃成了個小夥子!棄愉還常嘆息:‘救其命毀其容,造福乎?作孽乎?’”
杜衡自那天后一直琢磨,莫非王軫鄙視自己,避而不見,由此黯然神傷,情緒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