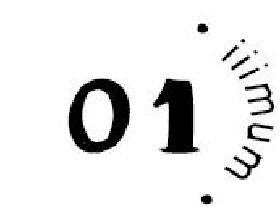1
蔡敏呆望著窗外,忍受著膝關節處和腳踝處的陣陣隱痛。這幾年,她的風溼性關節炎比天氣預報還要準,關節一痛老天就準會下雨。
突然,突兀的手機鈴聲響起,看了一眼名字後,她猶豫了好幾秒才接起。
“姐,她的病又加重了,你還是回家一趟吧。”
蔡敏的臉,瞬間也隨了外邊的老天,一時間找不準真正的情緒,像晴又似陰,像陰又似有雨,有雨卻又滴不下來。
電話裡的“她”,是指她們的母親肖麗芳。弟弟電話中說的是“病重”,她也沒有聽錯,而且她心裡還非常清楚,重到什麼樣子,依醫囑還能撐多久。
可是唯獨回去,她不願意。
手指重新撫上了鍵盤,可彷彿又僵住了。試著輸了幾個字,定睛一看,卻有一半是錯的。
身子頹喪地往後一靠,她索性又拿起了手機,開啟微信,找到“蔡智勇”,回了一句:“我就不回去了,轉點錢給你。你帶她去醫院拿點藥吧,拿止痛效果好一點的,貴點沒關係。”
然後,給他轉了一萬塊錢,無視弟弟字裡行間的責難,輕嘆一聲,才又坐正了身子,視線也隨之回到了電腦顯示屏上。
2
不是蔡敏不孝,也不是她心腸硬,而是那個女人,作為親生母親,帶給了她太多惡夢般的記憶。
從記事開始,她就只記得一種情緒:恨。
她的媽媽肖麗芳,對女兒蔡敏,就只有恨。蔡敏甚至有一段時間不知道這恨從何而來。
五歲時,她被要求幫媽媽洗衣服,沒洗乾淨就要捱打;掃地時,角角落落沒掃乾淨,劈頭蓋臉不是罵就是打;她想去上學的時候,問要學費,想要不捱打不捱罵,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有外人在的時候,還不許她哭……
有一次,她放學回家時不小心把鞋子弄溼了,媽媽竟然讓她把鞋子脫掉,在白皚皚的雪地裡站著,不知道站了多久……
她只知道自己沒站多久腳就失去了知覺,醒來是在床上,身邊只有小姨。她問小姨,自己到底是誰家的,為什麼別人家的媽媽不那麼對小孩子。
她至今仍記得小姨的回覆。小姨伸出手來幫她擦掉眼淚,嘆了一口氣,勸慰她:“也許你再長大一些,就能理解她了。”
這是她第一次感覺被人尊重,作為一個獨立的、平等的個體被尊重。所以一直記憶猶新。
可是,儘管她後來長大一些,她明白了媽媽之所以那麼歇斯底里,全是因為父親和奶奶嫌她生了個女娃,父親更是經常不回家,據說還在外邊有了別的阿姨。
可是她還是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別人嫌棄她的孩子是個女孩,她就會恨不得自己孩子死掉呢?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她終於熬出頭了。
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是個女兒,和老公也會吵架,女兒還時不時會讓她抓狂,可是她從不捨得伸手打女兒,就是罵也捨不得重口。
她至今無法釋懷,母親對她所做的那些。
而且,自己的風溼性關節炎,就是拜她所賜,自那個冬天以後,她的腳踝就會不定期地痛。
3
一年半前,她三十一歲,母親剛滿五十五。
也是弟弟打來電話,說媽媽身上總流血不止,去醫院檢查了是宮頸癌晚期。這時的蔡敏早已是一家外企的格子間討飯客,卻還是請了四天假,強忍著不去回憶那些過往,去了醫院。
已經沒有了手術的機會,只能放化療保守治療。
她陪了兩天就走了。那兩天裡,她也總是輾轉於醫生辦公室和超市或洗衣房,寧肯去打水洗衣,也要找盡機會逃離她的病床前。
那次住院持續了五十多天,她沒有再回去。
只是往弟弟微信上前後一起轉了四萬塊錢。又往父親蔡正陽的微信上轉了五千,父親是早已收心回家了,和母親的關係卻也已潰成了爛泥。
然而,那之後,蔡敏還是時不時會想起“宮頸癌”這三個字來。
她也特意向學醫的高中同學諮詢過這個病種的常規惡化過程,甚至還聽信一個同事婆婆的老藥方,諮詢過醫生後,由快遞發回去好幾大包的中藥。
每個月她也會轉兩到三千的生活費回去,還會和弟嫂打聽老太太的身體狀況。
大到吃多少飯,小到上廁所需要多長時間,詳細到非得弟嫂把老太太用過的廁紙拍照過來給她看,但她就是沒有再回去。
蔡敏固執地以一種隔空的方式控訴著那些年所受的苦,也維持著不原諒的姿態。哪怕是明知媽媽已經身患重症,時日無多。
蔡敏認為,只有在這種堅持中,她才能找到情感上的平衡。
4
接到父親的電話是在她給弟弟轉那一萬塊之後的第二十四天。
“你還是回來看看吧,她已不吃不喝,也不能說話了,眼睛卻老往門口瞟,應該是在盼你。”
“錯在爸爸,不在她。還是儘快回來吧……我好怕,我怕她等不到你……”
也許是父親前所未有的口氣鎮住了蔡敏,也許是一種揪心的離別氣息擊中了她,她聳了聳鼻子,迅速又幹脆地回覆了父親:“好的,我馬上去請假。”
深圳到湘潭,近九百公里路。她沒有去定高鐵,選了最直接方便的方式:開車。到家時,已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了。
家裡的氣氛有些沉悶,只有四歲的小侄子在三樓看著電視,電視機裡熊大憨憨的說話聲和侄子的笑聲透過門窗隱隱地傳了出來。
她站在母親的房門口,把身子隱於門外,猶豫著不敢上前,直到父親把她帶進了房間。
床上薄薄的棉被下,一個條狀的人形靜靜地躺在那兒。乍一看,還真不一定能發現那兒有個人。
明明只是微涼的十月,她卻感覺房間裡散發著一種說不出來的難聞的味道,和一種說不出來由的冷。
腳步越來越沉重,床上的臉也越來越清晰。
父親先她幾步走向了床頭,輕聲呼喚著:“麗芳,你看,你睜開眼睛看看,看看是誰回來了?”
縱使蔡敏再不願意承認,她還是準確無誤地感知到了床上那具形如槁木的軀體,正是她的母親肖麗芳。
她痴痴地望著那張沒有一點血色的、瘦得變了形的臉,眼窩深陷,整個一張臉也找不出二兩肉來。
她的腳開始不聽使喚地往前衝,手也不由自主地朝床上的人伸了過去。
5
那隻手已經沒有了多少溫度,但蔡敏還是如獲至寶一樣地用雙手把它握了起來,輕聲叫著:“媽,媽媽。”
肖麗芳在認出蔡敏後,嘴唇往上翹了翹,眼睛貪婪地在她的臉上轉了幾圈之後,又閉上了。
蔡敏伸出左手來,輕輕為母親拂去了眼角的眼淚。
那一晚,蔡敏送走了自己的媽媽。那個恨了她好多年,又被她恨了好多年的生她養她的人,終於提前離開了她。
她之所以覺得提前了,是因為她還沒有來得及和她和解,當然也認為五十七歲的年紀終歸還是太年輕了,甚至連老都算不上。
她一直認為自己總有一天會和她和解,卻並不知道具體是哪一天。直到,辦完喪事,她去整理她的衣物。
蔡敏發現了衣櫃最裡邊有一個塑膠袋,裝了好幾層袋子,每一層都整整齊齊的。看得出來包的人很用心,也很認真。
蔡敏直覺這裡邊的東西很重要,可光拆袋子就花了她差不多兩分鐘,越是性急手就越是使不到位。好不容易拆開後,她發現,裡面是一件羽絨服,有面熟的感覺,卻又想不起在哪見過。
她把棉衣抖散開來,這是一件新棉衣。蔡敏在腦海裡飛速地尋找著關於這件棉衣的記憶,磚紅色的羽絨服……
突然,她想起來了,棉衣是她當年置辦結婚衣物時買下的,是她買給媽媽的。當時覺得大紅的太刺眼,就買了個磚紅色,喜氣又不至於太張揚。
蔡敏把棉衣抱在胸前,在旁邊的凳子上坐了下來,陷入了沉思。
6
她給買的棉衣,這麼多年了,捨不得穿,拿個塑膠袋左一層右一層地包著,幾個意思?
蔡敏知道家裡這些年因弟弟成家和建房花費蠻大,所以母親不太可能會有什麼鉅額財物留下來。
想到這兒,她的手下意識地往棉衣口袋伸去。
忽然,一個細細長長的東西落入了她的手心裡,還有一個被塑膠袋裝著的小紙包。
細細長長的,是一個銅髮簪!塑膠袋裡,是一張發黃的小紙條,還有一把小銅鎖。
她不假思索地打開了紙條,沒等她看完,淚水就把那張紙條打溼了一半。
紙條上的內容是:
敏敏:
媽錯了,媽媽對不起你,不該打你,原諒媽媽吧。
這個,給你。
因為字跡歪斜,筆劃也不整齊,還有好幾個錯別字,蔡敏反覆看了幾遍,才找準字條想要表達的全部意思。
紙條最後的落款是:壞媽媽。“媽”字的“馬”字都比左邊的“女”字大出很多,也高出一截。
蔡敏雙手捂面,哭到不能自抑,淚水順著指縫流向了她的手肘,消失在衣袖深處。
原來,想和解的,不只是她一個人,認為她們母女終有一天會和解的也不只是她。
聽到哭聲的小姨迅速衝了進來,看到蔡敏膝上的衣服和髮簪,默默地把蔡敏摟進了懷裡,右手輕輕地拍打著她的肩膀。
好一會兒之後,蔡敏才停止了抽泣。在小姨抽抽嗒嗒的敘述中,蔡敏才得知一些媽媽當年的事。
7
事非經過不知難,每一隻刻薄精明的刺蝟,必有一段悲苦的命運,肖麗芳就是一隻這樣的刺蝟。
蔡敏生下來不到兩年,蔡正陽就在外邊有了人。
肖麗芳找他鬧過,可蔡正陽就是不收心,還減少了往家裡拿錢的次數和數目。肖麗芳小時候讀書時成績很好,也一直想出去做點事,可是蔡敏奶奶認為她就是想出去做壞事,找盡辦法阻攔。
還說肖麗芳唯一該做的就是為蔡家生個男孩。
蔡正陽不往家裡拿錢,可家裡吃穿都要用錢,那邊老太太又擠兌,日子一天天都是像在火上烤著。
有好多次肖麗芳都把衣服疊好準備一走了之,可每次看到蔡敏時又心軟了。
有一次她還把蔡敏送到了奶奶家,走了一個多小時之後不放心,又回來了。遠遠地就聽見三歲多的蔡敏嗓子都哭啞了,跑近一看,只見蔡敏一個人站在烏七抹黑的門外哭,裡面卻沒有一個人出來看看她。
自那以後,肖麗芳就徹底斷了離開的念頭。
只是,也把蔡正陽和生活給她的所有負面情緒,都甩給了年幼的蔡敏。她固執地認為如果蔡敏是個男孩的話,蔡正陽就不會在外面有人了,她也可以不受這些折磨。
即便蔡敏外婆和小姨無數地勸她說,蔡正陽的壞只和他自己相關,完全和孩子沒有關係,肖麗芳也聽不進。
蔡敏考上大學後,肖麗芳其實就已經後悔了。只是那時候,蔡敏也如離巢之鳥,一心只想逃離囚禁她的牢籠而不願回家。
8
後來,肖麗芳見蔡敏嫁了個好人家,又透過自己的努力有了份好工作,心頭的愧疚才慢慢地減輕了一些。
她也感到欣慰,自己欠孩子的,老天終於看不過眼在幫她慢慢償還。
紙條大概是肖麗芳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後,蔡敏又不願意回家時留下的。髮簪和銅鎖是蔡敏外婆留給肖麗芳的。
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蔡敏對於母親的所有負面記憶,在那張紙條上的內容慢慢進入她的大腦後就都不見了。
十指有長短,痛惜都相似。在淚眼朦朧中,她看到的那個人,雖然表達方式有些不同,但也如同千家萬戶的媽媽一個樣,真切而又深沉地愛著自己。
母親的悲苦,她不想作任何評價。母親是不是有過那麼一些時刻恨過自己,或嫌棄過自己不是個男孩,她也不想去深究了。
母親再怎麼樣她,但終歸還是沒有棄她而去。
她明白,自己能順利長大成人,學有所成,和母親的堅守是分不開的。而反過來說,自己又何嘗不是母親離開路上的攔路石呢?
一直以來,她夢寐以求的母愛不是不在,而是她選擇了忽略,選擇了不去求證。或者說,是被那蒙在表面的恨給遮住了。
蔡敏把銅簪和銅鎖緊握在手心裡,走出了房門。
門口,老公牽著女兒的手,正凝神等著她,小魔獸女兒也難得地乖巧。見她出來,父女倆同時朝她張開了雙臂。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