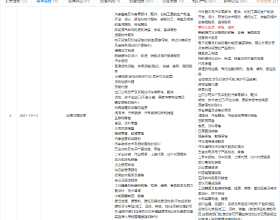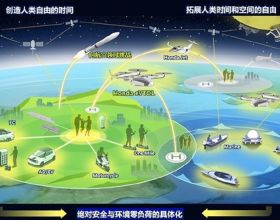網友們已經許久不見胡歌在熒幕上的身影,但最近,他卻在一檔紀錄片中以幕後配音的身份悄然迴歸,它就是——
《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

有網友評論,胡歌的配音專業又有溫度,彷彿梅長蘇在講話,一聽就愛上了。
和第一季一樣,第二季依然口碑很好,剛開播就獲得了豆瓣9.5的高分。

紀錄片以書為物件,專門講述了主人公與書的“愛恨情仇”,第二季延續上一季的敘事風格,擴大采訪者行業,記錄那些可愛可敬、對書籍懷抱熱忱的編舟者、創作者、愛書人,展現他們豐饒有趣的精神世界,定格這個時代爛漫動人的閱讀風景。

第二季的前兩集以圖書館和漫畫家為主題,聚焦書籍的傳遞者,創作者,為讀者揭開人物背後跌宕起伏有如傳奇一般的故事。

在四川的塔公草原上,僧人久美為藏族孩子們建立起了第一座社群圖書館。
久美原本並沒有常駐家鄉的打算,但是在參與了一次家鄉地震救援後,久美看見了家鄉與外面世界的差距。他意識到,一個地區的發展,離不開教育,但是教育,是這片肥沃草原上最最缺乏的資源。
沒有資金,他就透過售賣自制青稞醬獲取收入,沒有設計師,就自學建築知識,沒有材料,就人力搬運三四百斤的石頭建蓋房子。很難想象,這個沒有一滴水泥製成房子是久美憑藉著一己之力耗時一年多完成的。

圖書館建成後,久美邀請自己各行各業的朋友,為這些孩子們進行授課。

在圖書館的一次講座中,老師問有沒有人想當作家,良久的沉默後,女孩拉姆隱蔽地舉起了自己的手,又倏忽之間放下,露出靦腆羞澀的笑容,然後再次堅定地把手舉高,那個模樣,讓我想起上課時自己想回答又不敢回答問題的樣子,懷抱著純粹的渴望和期盼,但又對自己的未來不自信。
拉姆問:寫作的前途是什麼?

一個貧困地區的孩子,她很在乎,自己所熱愛的事物,是否能夠給家人帶來安定的生活,其實這也在問,書籍是否有意義。

這個女孩曾風雨無阻地連續三年來圖書館,閱讀自己熱愛的書籍,或者是趴在窗邊構思筆下的故事。但是每天下午放學回去,她就看見媽媽在路邊幫別人打工,那一刻她覺得自己很無用,讀了十二年的書,太無用了,什麼也幫不上。

我們不知道當時的答案是否有真正解答拉姆內心的困惑,但是一年後,拉姆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學的藏語言系。在花絮的採訪裡,拉姆像所有青春靚麗的大學生的一樣,臉上洋溢的活力,神采奕奕。她說,他想成為一名老師,離家近一點,可以照顧媽媽,閒暇之餘還可以翻譯藏文作品。

95後僧人久美對於後輩的影響,已然根深蒂固,發芽生長,“閱讀的意義”脫離了老生常談的抽象概念,落入泥土長出具體的果實。
我想這就是久美建設圖書館的意義所在,久美對於教育事業的執著,開始從每一本圖書上,慢慢流轉給下一輩。
“於無可救藥之地,療人寂寞,是菩薩行。
於無可奈何之地,與人希望,是菩薩行。”

如果說第一集為觀眾創造了一個如天堂般理想的國度,將小眾的事物浪漫化,第二集則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採訪的人物,也更加接地氣——三位漫畫家。
許先哲一開始不會畫漫畫,但是他想要創作自己的武俠世界,於是在開始自學漫畫四年,創作漫畫《鏢人》的時候,光是一座山就畫了一個月,廢稿加起來有兩千張;

他翻遍了《隋書》,《資治通鑑》等史書,觀察它們對於遊俠的解讀,將故事建立在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原型上。

那是每一個創作者都會經歷的暗黑時刻,拖稿,瓶頸,斷更,才思枯竭,生活的軌道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掉頭。

以懸疑科幻型別見長的才女趙佳,在連載漫畫《黑血》的巔峰時,父親重病,黑白漫畫時代開始退場,雜誌停刊,自此漫畫也斷更了好幾年,最終不得不以向時代妥協的方式再度出版——彩漫。

沒有電腦的時代,她曾一筆一筆地描速度線,用一塊一塊的網點紙填充人物的灰白底色,就像把自己的生命一點點填滿。
站在海灘上的趙佳喃喃自語,像古代生不逢時的詩人,生出一絲悲壯和苦澀。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突然就火了,把一幅幅圖畫和文字排成一列,契合豎屏手機的觀看順序,竟然創造了一種叫做條漫的新模式。
匡扶無奈又迷茫地嘆了口氣。


匡扶的狀態更像是大多數新時代的自媒體創作者的剪影,沒有說一輩子就要和漫畫死磕到底,也許回去組建個樂隊也可以玩得風生水起,一切都是源於興趣。



但是創作漫畫裡的故事,讓他開始重新審視身邊細碎的生活痕跡,一坨狗屎應該長什麼樣,人物的鼻孔多大才合適,田螺是一顆顆還是一個個的,腳上的泥點是否可以用星空來形容。

這大概就是每個創作者不變的匠心吧,從圖書館的建設者,再到漫畫的創作者,他們對於做成一件事的執著和刻苦,與這部紀錄片給人傳遞的感覺,始終自洽。

從配樂,到空境的選取,再到人物細節動作的展示,這部片子的每一個畫面都看不到模板化的痕跡,每一個運鏡都讓你相信這就是採訪者所思所想。
當畫家用筆觸向讀者傳遞故事角色的內心想法,他們背後的記錄者也在用人物最熟悉最接近的方式,完好地傳遞出角色心底的本意。

在許先哲對故事的走向冥思苦想時,他化身為漫畫中的一部分與角色進行靈魂對話;

當趙佳提起她父親的那一段往事,鏡頭轉為黑白動畫,一個父親和女兒在一起放煙花,煙花散盡,只剩下趙佳一個人孤零零的背影和浩瀚無邊的海洋,柔軟至極;

當匡扶去菜市場溜達尋找靈感時,導演把他所到之處都以彈幕和漫畫的形式呈現出來了,一時間彈幕評論中充滿了驚豔和盛讚。

或許這的確是導演擅長的部分,用視覺化的動畫代替文字的講述,但是,在三十五分鐘的一集紀錄片中,三個風格截然不同的採訪者,用了三種漫畫形式去傳遞人物內心所想,我願理解為那是對創作者的尊重。


紀錄片編導和採訪者的共同之處就是匠心,就是這種工匠精神,才會讓整個片子自成一體,毫無違和感。
對採訪者虔誠至極,對觀眾負責至極。
而這種用心,又與晦澀難懂的長記錄風格所不同,他很清楚受眾是一群年輕的群體。

對每個人物長達一年半的拍攝時長,無數鏡頭刪刪減減,最終只呈現了35分鐘一集的精華內容,算下來,每個人物的呈現時間,也只是10分鐘而已,插入足夠的淚點和笑點,在短頻快時代對待觀眾留存率小心翼翼的呵護,只有傾注了無數心血,才會有這樣殷切的期盼。


為了找到一個理想的採訪者在浩如煙海的網際網路資料裡竟然翻出一個八年前的帖子,順藤摸瓜聯絡到當年的主人公,過程就像開盲盒一樣驚喜。

同樣,這部片子的驚喜之處也非一篇文章的長度所能完全囊括,更希望大家閒暇之餘能夠去真正切身體會書籍創作者和記錄者們的這份虔誠與專注,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