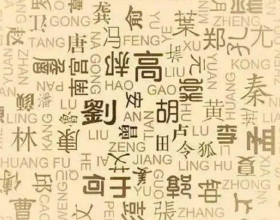1953年9月的一天,福建永定縣牛牯撲村的一位普通農民收到了北京發來的專電邀請,邀請人是毛主席。
這件事情在永定縣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那位農民陳添裕很快就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物件,毛主席邀請他去北京的事情也成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談資。
陳添裕看到毛主席親自邀請自己去北京天安門觀禮,他心裡萬分激動,但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最終卻選擇不去北京。
但是他不想直接拒絕毛主席,所以讓堂弟陳奎裕代替自己進京觀禮,沒想到在天安門的觀禮臺上,毛主席一眼就認出了此人不是陳添裕。
1929年6月,36歲的毛主席陷入了他人生的一段低谷期。紅四軍的“七大”在福建龍巖召開,毛主席在會議上受到了打擊。
他在會議上提出了很多正確的主張,但是沒有被同志們所接受,而且還撤掉了毛主席在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
這件事意味著毛主席在紅四軍沒有話語權了,他的很多正確方針無法再指導部隊了,萬般無奈之下,他離開了紅四軍。
毛主席來到上杭蛟洋,他在這裡指導閩西農民的土地革命工作,他的工作進展很快,沒多久就與當地的農民們打成了一片。
僅僅一個多月,就在閩西成功召開了一大會議,使得當地的革命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
那時候很多人以為毛主席失去了話語權後會選擇去蘇聯留學,但是毛主席沒有離開革命陣地。
他不想就此逃避,於是選擇去閩西苦苦堅守,他相信,那點星星之火一定可以燃燒得更旺,更廣。
毛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中,在部隊沒有了話語權,那他就進入到群眾的身邊,無論在哪裡,他都會為革命隨時獻身。
不巧的是,閩西一大剛剛開完,毛主席就得了瘧疾病倒了,在當時這是很嚴重的病,有很大的生命危險。
閩西特委的領導們見狀趕忙商量辦法,最終決定先把毛主席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休養休養,等身體好點了再做安排。
但是在那個時代,沒有什麼地方是絕對安全的,所以組織上為了保護毛主席,特意派了一個紅軍連跟著他,連長粟裕負責這次警衛工作。
也正是因為這次警衛工作,讓毛主席對粟裕欣賞有加,後來委以重任,使他成為了讓敵人聞風喪膽的“戰神”。
安排好警衛工作以後,大家就為休養的地方發起了愁,想要找一個環境好一點,又不容易被敵人發現的地方太難了。
後來有人提到了牛牯撲村,大家一拍即合,當即就定下了,因為那裡山高林密,空氣較好,也適合隱藏。
當時毛主席化名為楊子任,在粟裕連隊的保衛下來到了牛牯撲村,住進了陳添裕的家裡,這是毛主席與陳添裕第一次見面。
陳添裕當時只有二十出頭,比毛主席小十幾歲,是一名赤衛隊員,對當地地形非常瞭解,而且老實忠厚,所以組織上安排毛主席住在他家。
陳添裕也不知道毛主席的真實身份,他只知道能有一個連在身邊保護的人,肯定很重要,所以他暗下決心:哪怕豁出性命,也要保護好他。
當時陳添裕的家是祖輩留下來的兩層土樓,他把前間騰了出來,打掃得乾乾淨淨給毛主席住,他還把自己都捨不得吃的雞蛋都做給毛主席補身體了。
毛主席剛住進來不過三四天,就收到訊息得知敵人在附近活動,這個地方可能快要暴露了。
正當大家一籌莫展的時候,一旁的陳添裕開口說道:“我們可以把楊先生轉移到五公里以外的天子崠山,那裡是深山,暫時不會被發現。”
大家也覺得這個地方不錯,但是山上什麼都沒有,連房子都沒有,怎麼住人啊。
陳添裕看到大家疑惑的表情,笑了笑說:“房子不是什麼問題,我們自己搭一個出來就好了。”
第二天,陳添裕就帶著村民們上山裡搭起了竹屋,他們一輩子生長在大山裡,這些事情做起來得心應手,一盞茶的功夫就搭好了。
後來大家把毛主席接到竹屋時,他被眼前的屋子深深地吸引了,高興地開懷大笑,然後隨手在地上撿了一塊木板,在上面寫了:饒豐書房。
這間房子從裡到外全部都是用竹子做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裡面食具和床都應有盡有,但是唯獨缺了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毛主席有讀書的習慣,無論走到哪裡,都要閱讀各種書籍,而這間竹屋裡,沒有辦公桌,陳添裕毫不含糊,當下就現做了一張桌子擺了進來。
這讓毛主席和身邊的警衛們感到頗為驚訝,也對陳添裕他們這些樸實的農民感到更加敬佩。
毛主席瞬間就想明白了,自己不想逃避,帶病堅持究竟是為了什麼,他在陳添裕這些人身上看到了答案。
就是要讓這些樸實善良的農民徹底站起來,過上更好的日子,這不正是自己搞革命的初心嗎?
毛主席完全想通了,這些一貧如洗的農民都能笑對生活中的任何困難,接受一切挑戰,並且永遠對未來充滿希望,那自己這暫時的打擊算什麼呢?
毛主席在竹屋裡住了28天,如飢似渴地看書,閱讀了各種各樣的書籍,陳添裕則每天在家裡做飯,然後跑五公里給毛主席送過來。
他們二人在近一個月的相處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牛牯撲村的其他村民們也都在竭盡全力地掩護著毛主席。
到了九月份,毛主席的行蹤還是暴露了,國民黨的偽團總林蔚民和胡道南帶領了六百多人進入了天子崠山。
粟裕連隊只有一百人,其中還有一半在山外佈防,真正在山裡保護毛主席的,只有五十個人,對抗六百人有些吃力,所以只能緊急撤離。
牛牯撲村赤衛隊的同志們熟悉山裡的地形,他們帶著粟裕連隊邊抵抗邊往山裡撤,眼看就快頂不住了,只能先把毛主席轉移出去。
當時安排陳添裕和另一位赤衛隊員護送毛主席,將他轉移到五千米以外的雨頂坪村,那裡有更多的赤衛隊可以保護毛主席。
但是這五千米的路全是山路,而且生病的毛主席身體虛弱,不能奔波。陳添裕和另一位隊員就架著毛主席往前跑。
敵人越追越近,毛主席身體吃不消,實在是跑不動了,陳添裕立即跨到毛主席前面彎下腰說:“楊先生,我揹你,快上來。”
毛主席不想讓陳添裕辛苦,也不想給他們添麻煩,死活不願意讓陳添裕背,還讓他們不用管自己,趕快跑。
陳添裕急得臉都漲紅了,跺著腳說:“哎呀,楊先生,你不要再客氣了,敵人馬上就追過來了,我們一定會保護好你的。”
話音剛落,還沒等毛主席接話,陳添裕就把毛主席背了起來,為了更快到達雨頂坪村,陳添裕選擇了更加難走的小路。
比毛主席小十幾歲的陳添裕個頭也沒有毛主席高,身材也沒有毛主席魁梧,但是他把毛主席穩穩當當地背在背上,從來沒有喊累。
還沒跑多遠,陳添裕的鞋子就跑掉了,他也不回頭撿,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鞋子掉了。
當時還是陰雨天氣,山上雨水大,地上都是黃泥水,他的腳就泡在泥水裡,地上的石頭和荊棘全都紮在他的腳上,他也絲毫沒有慢下腳步。
跑到一半路程的時候,毛主席覺得已經擺脫了敵人的追捕了,可以停下來休息一會兒了,他跟陳添裕說:
“陳添裕同志,我覺得這裡相對安全了,你把我放下來休息一會吧。”
但是陳添裕沒有回答,也沒有做出任何反應,只是不斷地往前跑,直到跑進雨頂坪村,陳添裕才把毛主席放下來。
陳添裕把毛主席放下來後,就一下子昏倒在了地上,當地的赤衛隊員們趕忙把他抬到屋子裡休息。
把他放到床上以後,大家注意到他的腳已經千瘡百孔了,鮮血淋漓的雙腳上還扎著很多的小石子和木刺。
他們找婦女借了一些縫衣服的大頭針,把那些刺一根根地挑了出來,毛主席在一旁看到這個情景,眼眶微紅地說:
“幸好有陳添裕同志,他為了我,受苦了。”
第二天,組織上派人來雨頂坪村接毛主席去更安全的地方,他非常捨不得牛牯撲村的人們,尤其是陳添裕,他對自己是有救命之恩的。
臨行前,毛主席找同志借來了紙和筆,寫了一張三塊錢的欠條,交給了躺在床上的陳添裕,當時陳添裕已經醒了但是還站不起來。
毛主席俯下身親切地說:“辛苦你了,你好好養身體,等革命勝利後,一定要來找我!”
三塊錢對當時的閩西農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字,這是毛主席第一次寫欠條,這既是對陳添裕這段時間悉心照顧的感謝,也是希望以後可以報答他的恩情。
其實欠條上的數字並不重要,毛主席只是希望革命勝利後,他還可以再次憑藉這張欠條見到陳添裕,親自報答他對自己的救命之恩。
毛主席離開後,陳添裕再也沒有見過他,自始至終,他都不知道自己救的人究竟是誰,也不知道他的行為對中國未來的影響有多大。
毛主席從深山出去以後,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因為大家都以為毛主席已經犧牲了,就連共產國際都在新聞上釋出了訃告。
大家雖然無法確定毛主席是否去世,但是在以五十敵六百的險惡環境下,毛主席生還的機率很小,而且毛主席還生著嚴重的病,就更沒有希望了。
所以大家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毛主席已經犧牲了,最終以訛傳訛,甚至傳到了蘇聯,以致於共產國際釋出了訃告。
三個月後,毛主席在上杭縣參加了第九次代表大會,又稱古田會議。大家在會上見到毛主席,都覺得他清瘦了很多,但是意志更加堅定了。
毛主席這次在會議上終於再一次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並且重新擔任了紅四軍的前委書記一職。
經過在牛牯撲村和天子崠的這些日子,毛主席已經鑄造了無比堅強的信念,從此以後,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所向披靡,無往不勝。
陳添裕也在毛主席身上看到了紅軍革命的意志和決心,他一如既往地在牛牯撲村生活,積極參加赤衛隊的任務。
沒有任務的時候,他就回歸到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種種茶,墾墾荒,維持著自己清貧但是快活的日子。
由於村子裡面沒有報紙,電話等通訊方式,所以他再也沒有收到毛主席的訊息,而那張欠條,他也早就遺落了。
他當初救毛主席,從來沒有想過什麼報答,所以他就沒有把那張欠條當回事,隨手放起來,丟了也沒有想過去找。
建國以後,陳添裕才知道,原來自己當年救的人是毛主席,他心裡非常高興,但是他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沒必要再提了。而且那本來就是自己的任務,也不值得炫耀。
他也沒有想過去北京找毛主席,還是繼續踏踏實實地待在牛牯撲村,做自己該做的事。
直到1953年國慶前夕,毛主席親自給陳添裕發來了專電,邀請他去北京觀看國慶閱兵典禮,他才知道原來毛主席還記得當年的事。
一輩子都在閩西山裡的陳添裕當然很想去北京,看看新中國的首都,看看天安門,看看氣勢磅礴的閱兵,更重要的是,再見一次毛主席。
但是很不巧,他的老婆很快就要生孩子了,他四十多歲了,這個孩子對他很重要,而且他也不想拋下老婆,所以他猶豫了。
思來想去以後,他還是決定留在家裡陪老婆,但是他又不想直接拒絕毛主席的邀請,而且村裡人都期盼著他去看看氣派的閱兵儀式,回來給他們講講。
後來他想到了一個辦法:讓自己的堂弟陳奎裕替自己去北京,既接受了毛主席的邀請,還實現了村裡人的心願。
他覺得自己只是作為牛牯撲村的代表被邀請的,堂弟陳奎裕也是當年保護毛主席的隊員之一,所以他想著換個代表去也沒問題。
於是國慶當天,陳奎裕就登上了天安門的觀禮臺,毛主席一看見他,就笑著對他說:“你不是陳添裕,你是看茶桶的那位同志。”
此話一出,陳奎裕嚇得面部僵硬,大氣都不敢喘了。他以為自己代替哥哥來觀禮,只不過是站在人群中看看而已。
沒想到毛主席會親自過來與他說話,並且一眼就認出了真假,時隔二十四年,毛主席不僅能記得他們的模樣,而且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的工作。
其實毛主席能看出來他不是陳添裕,是因為他比陳添裕的個子矮一點,如果當年是他背自己的話,恐怕腳都無法離地。
陳奎裕既欣喜毛主席還記得自己,又緊張冒名頂替的事情被發現了,於是一下子慌得手足無措起來。
但是毛主席緊緊地握住了陳奎裕的手,溫和而堅定地說:
“我在牛牯撲村的那段時間是無法磨滅的,你們對我的恩情刻骨銘心,我心裡一直惦記著你們,國家也不會忘記你們。”
這番話讓陳奎裕的心情一下子放鬆了下來,淚眼婆娑地望著毛主席,感謝他對牛牯撲村的惦念。
毛主席向來是一個有恩必報的人,無論恩人是什麼身份,只要幫助過自己,他都會一視同仁,找機會報答恩情。
但是對於牛牯撲村的村民們,他並不只是感激陳添裕一個人,而是所有的村民,所以毛主席當時離開時,就把他們的名字全部記在了本子上。
因為在牛牯撲村的那段時間,是他人生低谷期,那些善良的村民們不僅救了他的命,更拾起了他的“心”。
正如毛主席在那之後所作的《採桑子·重陽》裡面提到的“不似春光”、“勝似春光”。
儘管他當時處在逆境中,就像秋天一樣,涼氣逼近,萬物凋零,但是那些村民帶給了他如春光般的溫暖和燦爛。
所以毛主席只要看到牛牯撲村的任何一個人,心裡都是萬分感激的。毛主席在得知陳添裕無法來京的原因以後,對他更增添了一份敬佩。
自建國以來,毛主席收到了很多親朋好友的來信,有尋求幫助的,有想去北京看看的,都讓毛主席感到特別為難。
反而毛主席一直在等的陳添裕和三塊錢的欠條,遲遲沒有出現在他的面前,那時候毛主席就非常敬佩他的低調和質樸。
這次他又因為陪老婆生產而放棄了來北京觀禮的榮譽和機會,可見他的仁義和擔當。
當年他擔起了組織上的任務,現在又擔起了家庭的責任,他確實是一位鐵骨錚錚的好漢。
毛主席雖然遺憾這次未能與陳添裕見面,但是他更慶幸陳添裕選擇了留在家裡,讓他更加確定他沒有看錯人,陳添裕確實值得被邀請。
天安門上熱鬧非凡,在人群中,樸實無華的陳奎裕並不好找,但是他清澈的眼睛裡彷彿透著閩西山裡的光。
陳添裕還在家裡高高興興地等著老婆生孩子,等堂弟回來後,他就把北京的故事講給孩子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