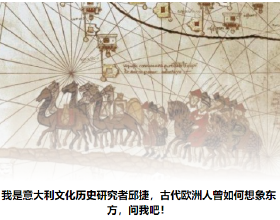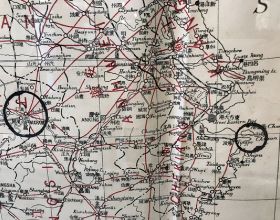其實絕大多數的末代君主都是背鍋俠,屬於招黑體質。畢竟在世人眼中,祖先的基業是在他們手上斷送的。幾代人積貧積弱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必然在末世一代暴發。所以,末世之君替父祖先輩背鍋這差事是逃不掉了。
作妖的祖先
任何朝代的治亂興衰都有一個週期,不是一蹴而就的。興是幾代帝王不斷治理的成果,而衰也是幾代亂世積重難返的結果。雖然商王朝是斷送在紂王手上的,但這個鍋讓他獨自來背,有點冤。咱們簡單回顧一下商朝的衰敗之路。
戰神夫婦
商朝最後一箇中興之主是高宗武丁。武丁年少時被父親派到民間去歷練,所以深知民間疾苦。到了他繼位後,就破除貴族的桎梏,大力提拔寒門人才,最著名的就是奴隸宰相傅說。雖然他用對了人,也得到了民眾支援,但這一舉動還是狠狠刺傷了貴族們的臉面。為了轉移內部矛盾,武丁不得不把槍口對準了不太聽話的番屬小國。所以就落下了一個好戰的名聲。
武丁不僅自己好戰,還娶了一位會打仗的媳婦兒,名叫婦好。這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女戰神,女將軍,也是武丁朝的占卜官,身兼數職的傑出女性代表。婦好經常披掛出征,先後征服了土方、鬼方、羌方這些諸侯國,還率軍跟古印歐人幹過仗。
這場戰爭的艱苦程度可想而知。這個古印歐人不是吃素的。他們發源於烏克蘭平原,是有名的遊牧民族,是草原上的雄鷹。而且這個民族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他們一直沒有建立自己的文明,但是四大文明古國,他們滅了三個。商應該是他們帝國版圖上向東擴張的重要一戰。
古印歐人有先進的戰車、熟練的冶煉技術和豐富的作戰經驗;而婦好這邊,除了戰爭經驗以外,其餘的條件都比不上古印歐人。然而,神奇的是,婦好就是憑著一股韌勁,居然把古印歐人趕回了歐洲老家。雖然打贏了仗,但實際上商王朝也沒佔到什麼便宜,畢竟是保衛戰,守家在地的,只剩下純粹地消耗戰爭經費了。
所以,窮其武丁一朝,雖然戰鬥力一直爆棚,但密集的戰爭,而且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對國力的損耗相當大。所以,歷史上凡是上一任開疆拓土的帝王,到了選擇繼位人時,都會選擇性情偏溫和的,這樣可以減少戰爭,使國力得到恢復,人民得以休養生息。不過遺憾的是,武丁在選擇和培養繼承人的上不太成功。
超頻改革家帝甲
武丁的兒子輩出了一個有名的改革家——帝甲。帝甲是武丁的三兒子,也是他酷愛的兒子。武丁覺得“此子類我”,曾蒙生廢長立幼的想法,後來被大臣勸阻了。但是這個事,還是讓帝甲晚了七年才坐上商王寶座。而這七年對他日後的執政方略有很大影響。
武丁死後,帝甲避位效法他老爹到民間去歷練,太子祖庚有順利繼位,立帝甲為王嗣。帝甲在民間一待就是七年,看到了商王朝多少年來積累的政治弊端,就萌生了改革的念頭。等到他繼位以後,也想跟他老爹一樣幹一番事業。但是仗都讓他老爹打完了,於是他就把精力都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改革大潮中。
帝甲都改了什麼呢?一共三件事:第一是曆法,第二是祀典,第三是考驗太卜。這三件事在今天看來無所謂,在當時可都是要傷筋動骨的。
曆法會影響農業生產,在農業社會是直接動搖經濟基礎的;商人重祭祀,但是帝甲改革的祀典過於繁複,一個月裡有半個月都在祭祀,剩下的時間在準備祭祀,這樣下來,社會秩序被打亂了,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導致上上下下亂作一團;再說考驗太卜,商代占卜是職業化的,而且擔任占卜的都是高階官員,在朝中既有人脈也有政治影響力,況且神權是非常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甚至已經威脅到王權,實際上帝甲的真實用意是去除神權、強化王權。但是這些人根基深厚,不是說動就能動的;加之他的改革手段過於強硬,社會矛盾一下子被激化了。
更要命的是,這三件大事,件件都傷及國本,而帝甲還把這三件事一起辦,能不亂嗎?原本他老爹武丁就因為四處征戰結了不少外仇,他再急功近利地大搞改革,內憂外患一起來,商王朝的國運急轉直下,迅速衰敗下去。
玩人偶的商王
好不容易盼著帝甲歸西了,沒過三代,又出了一個鬧騰的主兒。這位商王可是徹頭徹尾的昏君,名叫帝武乙。
武乙也是太子爺當慣了,不僅不務正業,精神可能還有問題,心智不成熟。他喜歡玩手辦,把土和泥混在一起,做成人形的玩偶,還被封為“天神”。更奇葩的是,他時常跟這些“天福”賭博,而且命令手下人作評判。“天神”輸了,他就想盡各種辦法侮辱它們。他還喜歡射箭,而且鍾愛移動射擊。不過他射的靶子很特別,是用皮袋裝的血袋。可以想象,一整袋血拋向天空,利箭穿堂而過,漫天飛血多恐怖。帝甲喜歡得不得了,還給它取了個霸氣的名字叫“射天”。憑帝甲這一番胡鬧,下場可想而知了。
據《史記》記載,有一回他到河邊去打獵,被暴雷劈死了,也算是惡有惡報。自此以後的幾代商王,也沒有什麼政治建樹,就是守著祖宗的基業,能撐一時是一時,能撐一世是一世。等到帝位傳到紂王他老爹帝乙手上時,朝政已經頹廢得不成樣子。江山風雨飄搖,偏巧帝乙又不是一個政治能力很強的人,所以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兒子了,於是我們的背鍋太子就在這種情境下上位了。
不認命的末世王
朝綱頹廢、經濟萎靡、軍隊懈怠、諸侯不臣……這種情況下要扭轉乾坤無異於亡羊補牢。但是帝乙不認命,他還是想挑選一位能幹的兒子繼承帝位,就算不能恢復武丁霸業,能守住商湯江山也是好的。
氏族擁戴下繼位
商王朝非常講究繼位者的正統。帝乙的王后並非原配,而是在生下一子後,擢升為王后的。啟和受雖然都是王后所出,但卻嫡庶有別。啟是他母親為妃時所生,所以長而庶;受是母親封后之後所生,所以小而嫡。除了這個先天優勢外,受還才思敏捷、體力過人,可手格猛獸,太史公稱其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這麼好的兒子,誰不喜歡。不僅帝乙喜歡,氏族們也喜歡。受的太子身份就很順利地定了下來。
帝乙駕崩後,受在氏族的擁戴下繼位,號帝辛。至於“紂”這個諡號是周人強加給他的。有商一代,只知帝辛,不知紂王。
年輕的帝辛很快就發現自己的政令推行不下去。每發一道指令,總有人站出來反對,說一些忠言逆耳的話。不管這些諫言是對是錯,老被臣子駁回來,一來二去,這帝王的威嚴何在?況且這些人還動不動就抬出先王來,擺出一副長輩的姿態來教育他。帝辛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整天聽一些老俗套的說教,怎麼可能不煩。
有人會說,換一批幹部不就完了嗎?事情哪有這麼簡單。 此時商王朝的核心決策層主要由王族旁支和大氏族首領擔任,比如王叔比干、箕子,還有商容等一般老臣(太師聞仲是《封神演義中的人物》)。這是他老爹最得意之作。雖然受是一個成年太子,但商王朝已經風雨飄搖、大廈將傾,帝乙怎麼捨得讓兒子獨自收拾這個爛攤子,於是就按自己的意願給他配了一套豪華班底。內外外交、軍事經濟,皆不用帝辛費力。換句話說就是——他根本插不上手。一個年輕氣盛的帝王被排除在朝政之外,他規劃的施政藍圖怎麼能實現?所以,他必須弄出點動靜來。
強推改革,動了氏族的蛋糕
帝辛打算搞什麼動作呢?歸根結底,還得換人。但不能大換!朝中大臣去一大半,那朝政就癱瘓了。他琢磨著,“你們這些老貴族、前朝老臣不跟我一心沒關係,我就找幾個跟我一心的臣子,把你們晾一邊去。”
可是怎麼找到跟自己一心的臣子呢?帝辛只有提拔新人,而且要從“小臣”集團中找。為什麼要從“小臣”集團中找呢?當時沒有後世的世家和寒門之說,但其實差不多。各朝各代都有貴族和平民(地主豪強,沒有功名爵位在身的人),貴族家的孩子世代為官,即便沒有官職,還有蔭庇之說;平民家的孩子就不同了,入朝為官都是憑本事考取的,即便是買官,也是家裡花了大把銀錢疏通來的,所以家族的人脈資源必定不差。
這些人跟貴族們相比,政治背景基本可以忽略了,而且又是帝辛一手提拔起來的,要想在朝廷中立足,就得依附於帝辛,自然也就非常聽話了。帝辛讓他們往東,他們不敢往西。這樣的臣子用著多得勁呀!
史籍記載,帝辛提拔的小臣有飛廉、惡來、費仲、左疆等。這些人中不乏能臣,比如費仲在稅收方面比較在行,後來帝辛興建宮室、大舉征伐的後援錢糧,大多都是由他負責籌集的。不過,由於當時沒有完備的幹部考察體系,即便帝辛親自面試,也很難從一兩次面試中考察出一個人的品行操守,加上這些官員大都來自底層,對上層政治鬥爭的規則並不瞭解,也給帝辛的統治生涯埋下了危機。
經過一番人員調整,帝辛另建起一套領導班子,把那些元老權貴們排擠出核心權力圈了。這回終於沒有人在他耳邊聒噪了。帝辛開始大膽改革,他要把腐朽的商王朝改變成自己心目中的樣子。他都幹了哪些事呢?
首先是推行法制改革。其實這個出發點沒錯,法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根據社會發展出現的問題不斷改革完善的。但是法律的改革牽連甚廣,一條小小的法律就可能改變成千上萬人的生活。
商王朝當時也實行了分封制度,只是沒有後來周朝那樣的大封建。商王把土地和奴隸分給自己的同族兄弟、異姓權貴、功勳新貴。奴隸通常是由戰俘和罪人組成,而且是世襲的。如果爹是奴隸,兒子也是奴隸,子子孫孫都是奴隸,除非立有大功,有貴人出面幫你脫籍,否則你們家世世代代都得給人當奴隸。奴隸不僅沒有人身自由,連經濟自由也沒有,所有勞動所得是歸土地主所有。雖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商王把土地分封出去了,土地的管理權就落到了土地主手裡,一年能打多少糧食,能上交多少歲幣,還不是土地主說了算,他們在賬目上動點手腳,那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了。所以,商王朝真正的有錢人不是商王,而是這些裂土為王的土地主們。這些人就是商王這棵大樹上的蛀蟲,瘋狂地啃噬這棵行將轟塌的老樹。
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惡性迴圈:帝辛要打仗沒錢,要搞工程沒錢,要給臣子們發點補助,還是沒錢!帝辛就琢磨,錢沒有,人總有吧?事實是,除了那個專出大力水手的戲班子,沒有一支聽他指揮的軍隊,連奴隸都招不上來。這一下可把帝辛給惹毛了。
“小臣”集團的官吏就給他出了一個主意:改變懲罰罪人的方式,命內、外服各族脫離族組織的人口,一律歸商王管轄。“服”可以理解為商王分封出去的土地,外服是指臣服於商王的諸侯。這樣一來,商王手裡就有了自己的兵馬,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這些“小臣”忽略了一點,奴隸的總數是相對恆定的,商王這兒的人多了,土地主們手下的人就少了。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勢力的此消彼長,貴族的權勢眼見就被削弱了,還能忍嗎?肯定得跟新上來的這些“小臣”集團鬥爭啊。這些人在朝中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又是王族勳貴,有封地有兵馬,不是幾個小臣所能撼動的。當然,這也是他們跟帝辛爭奪權力的資本。可帝辛畢竟是一國之君,不要臉面的嗎?於是,王權和族權兩派就開撕了。
商王朝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力機構就是占卜官。早在帝甲時期就曾推行過周祭制度,以分化占卜官的權力。而占卜官的背後是老貴族的支援,他們利用占卜奴役民眾,藉以控制民眾,維持自己手中的權力。由於族權過大,帝辛也打起了周祭制度的主意。於是,在小臣們的鼎力協助下,商王朝在全國各地施行了如火如荼的周祭制度,固定和縮小致祭神靈的範圍,以此疏遠舊貴族,弱化占卜官的權利。
如果這一招提前幾代推行,或許還奏效;到了帝辛這一代時,商王朝已經風雨飄搖了,老百姓連粥都喝不上了,還整天想著搞祭祀,不事生產,國家經濟一下子就垮掉了。這個政策屬實地堅壁清野,貴族們沒錢進賬了,商王也好不到哪兒去。國家稅賦太少,拿什麼來養兵,沒有兵馬怎麼實現帝辛開疆拓土的偉大藍圖?這就逼得帝辛加緊了稅賦改革,費仲和惡來這些小臣的才能終於找到了施展的舞臺。但光靠調整稅賦,錢來得太慢,於是帝辛就把眼光放到了東夷。
征討東夷,開闢新版圖
商朝時候的東夷主要指今天的中東部地區,面積比較大,大致涵蓋了冀州東南、山東、江蘇北部一帶的沿海地區。這些地區主要是物產比較豐富,百姓生活富足。其實自帝甲之後,不朝商的諸侯比比皆是,也不單單在東夷一帶。帝辛看中的是東夷諸部的口袋兒,可收的歲貢比較多,可以快速解決國庫空虛的窘境;還有一點是這些小國好打,比西北的土方、羌方好對付多了。
為此,帝辛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專門負責征討各地不臣服的諸侯小國。其實這三公很少出戰,真正帶兵打仗的,除了有名的商朝將領外,就是帝辛本人了。——黃飛虎是《封神演義》中的虛構人物。帝辛除了孔武有力以外,還喜歡騎射,能手格猛獸,《封神演義》中還寫了他扶梁換柱的軼事。說明他比較好動,東征的很多戰爭其實都是他親自指揮的。
你想啊,王師再弱,也是中央軍,人數、戰術,裝備輜重都是小國所不能比的。帝辛率領著這樣一支隊伍,那還不所向披靡,就剩下實力碾壓了。所以說,他在打東夷的幾十年中,基本上也沒真正遇上強敵。
打仗跟下棋差不多,一直下順風棋不是一件好事。打仗也如此。越打越順,有時候容易讓人迷失,誤以為自己天下無敵,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旦陷入自我感覺良好中,這個主將就危險了。這個時候有人偷襲,打你一個措手不及,一轉眼兒你就失去了戰局的優勢。
帝辛越打越順手,在東夷打下來的地盤也越來越大,漸漸地就把政治重心和軍隊都轉移到東夷,中原一帶就留給那些舊貴族自娛自樂。可是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諸侯——西伯。此時商周交惡已深,身邊大臣一再規勸,但是帝辛自以為王牌之師在手,根本不把西伯之軍放在眼裡,結果歷史給了他狠狠的教訓。西伯軍自西進攻,一路過關斬將,打過了居庸關,直逼朝歌。帝辛的大軍都在東部駐紮,等他醒過悶來,再調軍回師拱衛都城,已經錯過了最佳戰機。商軍士氣潰散,只剩下一路敗北。接下來的一幕就是帝辛鹿臺自焚殉國,商王朝五百多年的基業就此終結,天下真的改弦更張了。
商王朝真正的終結者
雖說商王朝是在帝辛手上斷送的,而周武王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任何一個朝代的滅亡都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導致商王朝滅亡的原因不是一個,積重難返自然是不必說,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內鬥。這個內鬥並非“禍起蕭牆”,而是王權和族權的纏鬥,進而導致了激進式改革。
武丁留下的政治隱患開始,帝甲急於求成的激進式改革就上場了。可惜,他失敗後,後人沒有繼續堅持,被族權俘獲,安於享樂,才出了那位玩人偶的帝武乙。到了末世王帝辛時,雖然也有勵精圖治之心,但還是犯了步子邁得太大、用人不當得錯誤,雖然也有短暫的興盛,但對於一位老人來說,曇花一現無異於迴光返照。
王權和族權本身是相互依存的關係。早期建國,族權是王權最大的依託,沒有這些老貴族的支援,商湯不可能反抗夏王朝;沒有這些老貴族的支援,累卵中的商王朝不可能一點點發展壯大。但到了後期,當放權與王權盤根錯節長在一起,王權被無形中分化了,這是哪個帝王也不能接受的,所以收回王權是歷代商王都面臨的一個難題。從帝甲開始,一代又一代艱苦努力,一代又一代輸得徹徹底底;最後到了帝辛手裡,當他把最後一根炭扔進火堆時,火球飛爆,直接把商王朝送去歸西了。
特別說明:以上圖片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參考文獻: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