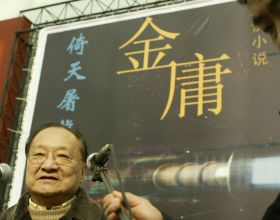呂利/文
集體主義日本對個人主義美國一說常見於各種商業評論,但在動畫這一日美各有所長的領域,兩國業界的表現恰與這一傳統印象相反。美國動畫的品牌價值往往凝結在工作室與IP名下,大部分觀眾在觀看《玩具總動員》《機器人瓦力》時很難對導演的名字或作風留下記憶。與此相對,今天即便不甚熟悉日本動畫的觀眾也知道《攻殼機動隊》與押井守、《盜夢偵探》與今敏的對應關係。一些熱忱的日本動畫愛好者將上述現象為“卡通”(cartoon)與“動畫”(ani-me)之間的關鍵區別,認為後者更有“深度”,而前者只是傳統的兒童娛樂,但日美動畫真正的分歧主要體現在製作模式上。
在美國,華特·迪士尼在美國開創了以工作室為核心的製作模式,導演、動畫師等主創人員在製片人統籌協調下形成均質可控的美術與表達風格,共同產出能夠取悅儘可能多的觀眾的商業作品。相比之下,起步較晚的日本動畫業更強調特定主力人才的帶頭作用,具有突出能力與個性的創作者可以享受更大空間。在產業規模上遠遜於美國同行的日本動畫業之所以能在這場大衛對歌利亞的較量中給人留下可圈可點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持續了半個世紀的“作者主義”傳統。
如果說美國動畫業的工業化模式肇始於天才製片人華特·迪士尼,由手冢治虫等人從1960年代在日本開啟的作者主義路線則以動畫導演宮崎駿為集大成。在當代日本乃至世界電影界,宮崎駿的地位毋庸贅言。輿論印象中的宮崎駿是定言令式般的商業品牌,一場活著的文化事件,而作為動畫導演,宮崎駿的專業能力更令人高山仰止。宮崎駿在1960年代加入東映動畫,成為主力動畫師之一,在積累了豐富的一線製作經驗後,於1978年初執導筒,主持製作了電視動畫《未來少年柯南》,其間一手包辦了劇情大綱、角色設計、分鏡繪製與大部分動畫檢查,展露出空前的精力與全面的才能。此後,從1979年開始執導劇場動畫的宮崎駿延續了這種事必躬親的風格,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對自己的導演作品施加了鉅細靡遺的把控,令與他頗有交情的押井守稱他為製作現場的“拿破崙”。
除了擁有將個人構思忠實投射到作品中的天才能力,作為動畫導演的宮崎駿也確實是一個不憚於表達自我主張的創作者。在80年代的幾部動畫長片中,宮崎駿的作者性已經表露無遺:主人公通常為具有獨立動機的少女或精力無比旺盛的少年,因關乎人類存亡的危機或單純的搬家而開始冒險。自然世界總蘊藏著友善的超現實能力,可以在劇情的重要時刻(以在觀眾看來不那麼有說服力的方式)為主人公化解關鍵衝突。國家總是以近代化暴力機關的面貌登場,其軍事力量的滅亡往往為劇情的高潮拉開序幕。故事中真正的壞人極少,大部分配角內心缺乏惡意,一些最有活力且最善良的角色往往是老人;幾乎所有人都按照一定的道德觀行動。在因《千與千尋》贏得廣泛的國際關注後,宮崎駿作品引發的討論更是從偏向技術與審美的“作者性”進入了更偏文字的“思想性”層面:他的動畫似乎寄託著一種融合了環境主義、女權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個人“哲學”,這些主張不但體現在他的作品裡,也體現在媒體在伊拉克戰爭、日本修憲、《查理週刊》事件等問題上採訪到的隻言片語中。
然而,成為日本動畫界的金字塔,並不意味著動畫創作就是宮崎駿創作活動的一切。對宮崎駿人生經歷的回顧時常強調他在青少年時代因觀看《白蛇傳》與蘇聯動畫《冰雪女王》而立志製作動畫,卻很少提及漫畫與兒童繪本對宮崎駿的影響。在加入東映動畫以前,就讀於學習院大學的宮崎駿曾加入該校兒童文化研究會,嘗試過以兒童文學之名漫畫創作;從事動畫工作後,宮崎駿曾以“秋津三朗”的筆名在1969~1970年連載了漫畫《沙漠之民》,又在1983年完成了繪本《修那之旅》。成為動畫長片導演後,宮崎駿也曾創作多部軍事題材短篇漫畫,《紅豬》與《起風了》兩部影片的雛形即在其中。
作為漫畫家,宮崎駿的代表作非《風之谷》莫屬。1981年,宮崎駿經日後的合作伙伴鈴木敏夫介紹,向有意進入動畫市場的德間書店高層提出了製作劇場動畫《風之谷》的方案,但被以沒有原作漫畫、缺乏商業保證為由拒絕。因此,宮崎駿從1982年2月開始在德間書店旗下刊物連載漫畫版《風之谷》,並於1984年將相當於單行本前兩卷的內容改編為時長兩小時的動畫長片。在此之後,雖因導演事務纏身時有休刊,宮崎駿仍將《風之谷》漫畫的創作堅持下去,直至1994年正式完結,全篇幅相當於動畫版劇情的三倍。
雖然此生只創作過這一部長篇漫畫,《風之谷》單行本七卷逾千萬冊的銷量和持續至今的文化影響力仍足以奠定宮崎駿在日本漫畫史上的地位。2019年,漫畫版《風之谷》被改編為歌舞伎,就在當年年底,日本出版界一月之內先後迎來了兩本以《風之谷》為主題的思想評論著作,其一為社會倫理學者稻葉振一郎的《娜烏西卡解讀·增補版》,其二為民俗學者赤坂憲雄的《娜烏西卡考——風之谷啟示錄》。即便以宮崎駿之盛名,一部漫畫在完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的今天能受此待遇,仍不可謂不奢侈。
1984年上映的動畫《風之谷》是宮崎駿執導的第一部原創動畫長片,也是“宮崎駿式”風格的集大成之作。在現代文明滅亡後,由有毒黏菌與巨型昆蟲組成的新生態系統“腐海”主宰了生物圈,將人類逼至陸地邊緣。軍事大國多魯美奇亞入侵小國培吉特,從其境內奪走一千年前消滅舊人類文明的生物武器“巨神兵”,試圖以此燒平腐海、開拓生存空間,培吉特遺民則故意惹怒腐海蟲群,試圖誘其衝擊多魯美奇亞軍隊,報亡國之仇。淪為戰場的農業酋邦“風之谷”酋長之女娜烏西卡歷經冒險,發現腐海並非自然的惡意,而是將被人類汙染的舊世界還原成清淨世界的良性機制,最終犧牲自己平息了蟲群的怒氣,以此換來蟲群的諒解與祝福,在經歷了彌賽亞式的復活後調停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
稻葉振一郎的《娜烏西卡解讀》脫胎於他1994年12月發表在《季刊窗》上的長文。作為對當年早些時候完結的漫畫《風之谷》的回應,稻葉振一郎從烏托邦主義的角度指出了《風之谷》漫畫版與動畫版間的思想色差。動畫版《風之谷》講述了一個從烏托邦出發、又歸於烏托邦的故事:在工業文明崩潰後,於有毒的腐海邊緣艱難求生的農業社會風之谷沒有政治權力與暴力,僅憑簡單的風力與灌溉裝置維持了自給自足的生活。以強大軍事力量挑起戰爭,甚至企圖焚燒腐海的多魯美奇亞軍隊雖然破壞了這一理想狀態,但隨著劇情高潮部分的核心衝突因娜烏西卡的死與復活而化解,侵略者不得不撤離,在腐海的“福音”庇護下,風之谷又被還原到了之前那種和諧永續的狀態。
與此相對,漫畫版《風之谷》講述的是一個不但沒有從烏托邦出發,反而在結局中否定了一切烏托邦存在,在核心思想上幾乎與動畫版截然相反的故事。在動畫中,腐海的真相暗示著和平永續的生活終將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終將得到解決。但在漫畫中,腐海寄託的含義恰恰相反:被腐海完全淨化後的世界無法生長任何動植物,在當前世界裡生活的人類只要呼吸一口“清澈但強烈”的未來空氣就會吐血死亡。隨著腐海的本質在漫畫版結尾部分得到澄清,這個在電影版中代表大自然良善力量的意象反成了人類文明技術的最高“傑作”:以不符合演化規律的速度突然蔓延到整個生物圈,不斷增殖、淨化並自我毀滅的腐海並非自然產物,而是少數古代人(即現代人)的世界重啟計劃的一環。在用幾千年時間消滅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爭鬥的一切痕跡後,被封存的人類胚胎將在毫無環境汙染與不必要的技術,只有農業、風車、動物、音樂與藝術的理想環境中發育、生活。結果,在為充滿敵意的世界尋找解決方案的冒險之路盡頭,娜烏西卡反而決定用暴力摧毀含有舊人類胚胎的改造計劃中樞,把《風之谷》世界的未來留給了似乎註定走向滅亡的現有生物界。
如果說動畫版《風之谷》只是以“風之谷”為喻體,向現實世界(即在動畫版《風之谷》開場的寓言中已經滅亡的現代觀眾)宣講某種生態烏托邦的可貴性與可能性,漫畫版《風之谷》中的那個虛構世界不但脫離了工具屬性,呈現出類似托爾金所謂“次等世界”的自主生命跡象,還直接質疑了動畫版中表達的烏托邦思想本身。漫畫版中的“風之谷”酋邦並非遺世獨立的農業社群,而是時刻面臨少子化、慢性病與腐海汙染威脅,必須為多魯美奇亞提供軍役才能換取和平的脆弱小社會;與動畫版相比,“烏托邦理想能否保全自己”的問題在漫畫版中更為鮮明。而如果一個生態烏托邦的構想解決了現實的問題,它是否也徹底倒向了選民主義,它的踐行是否也無法離開徹底的計劃性?對於烏托邦主義的這一傾向,宮崎駿在結局表達了略顯唐突、但發人深省的拒絕。
在稻葉振一郎看來,宮崎駿的結論與羅伯特·諾齊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的觀點頗為相近,這一解讀或許會令抱有“社會主義者宮崎駿”印象的讀者產生違和感。稻葉認為,在漫畫版《風之谷》結局中,娜烏西卡拒絕了一種全然計劃的、不承認對良好生活之自主探索的“帝國主義的烏托邦主義”,以擁抱一個包容多種烏托邦之可能性的“元烏托邦”。它只能體現在人與人、人與自然在無盡旅途與無盡苦難的煎熬下偶然生成的和解與共生中,無法獲得固定的形態,也不能成為歷史的終結者。
與在更廣泛意義上把宮崎駿作為思想者對待的稻葉振一郎相比,赤坂憲雄對《風之谷》的評價更重視其創作過程背後的知識考古學背景。出於日本左翼民俗學對天皇制與政治權力來源的傳統關注,赤坂注意到了宮崎駿在《風之谷》中對“風之谷”這一前國家社會的描寫與他之前的繪本、漫畫作品間的關聯。與專注於構築一個完備的次等世界的漫畫版相比,宮崎駿在動畫版《風之谷》去除了腐海背後的複雜矛盾,淡化了風之谷居民正走向慢性死亡的慘淡背景,轉而著重刻畫了以一群可愛的老人為首的風之谷居民如何伺機推翻多魯美奇亞人的軍事統治。這一改編情節的分量在動畫版中幾與娜烏西卡本人的冒險戲份相當,其內容則幾乎完全脫胎自宮崎駿講述中亞小民族對抗遊牧帝國侵略的早期漫畫作品《沙漠之民》。
用“小國抗霸”這一更具張力也更為駕輕就熟的主題填補動畫改編留下的空白,揭示了作為創作者的宮崎駿與作為動畫導演的宮崎駿之間耐人尋味的矛盾關係。如果不在漫畫中(半無意識地)思考烏托邦思想面臨的種種難題,宮崎駿也無法在動畫中勾勒出一個在充滿惡意的世界裡生動而可欲的“風之谷”意象;然而,受制於工期、商業考量以及動畫這一體裁的基本屬性,作為動畫導演的宮崎駿又不得不把一種已在自己腦海中被全面拷問、卻在感情上難以割捨的單純的烏托邦主義當作編排情節時最經濟的選擇。赤坂憲雄將漫畫家宮崎駿構築《風之谷》世界觀與故事的手法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中的“復調性”(這也與稻葉振一郎的烏托邦論相呼應——有著多種價值觀的世界必然是一種確定的烏托邦主義無法容納的),但在動畫版的改編中,只需與漫畫內容稍加參照,觀者便不難看出宮崎駿在製作動畫時對自我表達的明確節制。
透過將復調性的世界構造與單線條的、以明快的情緒為動力的冒險戲劇截然區分,80年代的宮崎駿產出了完成度與商業回報比之前更高的作品。但在他本人看來,這種“盆栽”式的成果未嘗不是一種表達上的缺憾。或許正因如此,在今天若以1994年《風之谷》完結為分界點回顧宮崎駿的作品便不難發現,從1997年上映的《幽靈公主》開始,宮崎駿作品的道德色彩變得更為曖昧了。《幽靈公主》中,在室町時代的日本大肆破壞原始森林的鍊鐵城鎮本身染上了現代企業與宮崎駿早期作品中無政府工團意象的色彩,成為麻風病人、女性等受迫害人群的公社;在2001年上映的《千與千尋》中,光怪陸離的澡堂“油屋”既是半奴隸制僱傭勞動與異化的隱喻,也與女主人公在社會意義上的成長密不可分。隨著《風之谷》的故事走向終結,曾被宮崎駿小心排除在動畫這一媒介之外的那種令他在漫畫中無法割捨的復調性終於滲透到了他的主業當中;拜這一變化所賜,宮崎駿作品原本暢快的反現實基調中也加入了一抹更接近現實的顏色。
不過,把複雜而多歧的虛構世界刪減成在時間與邏輯上有限的動畫電影固然是一種表達的缺憾,把兩種看似完全相悖的創作思路糅合在一起也未嘗不是如此。雖然在思想性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認,宮崎駿自《幽靈公主》以來的作品在敘事的完成度上時常不盡人意。某種意義上,越來越複雜的構思令宮崎駿作為敘事家的造詣在21世紀遇到了瓶頸;但正是在這一瓶頸的擠壓下,他的創作衝動才能像永動機一樣不懈燃燒。由此看來,那個永遠在路上、永遠不會被現實追上的烏托邦或許不只代表了宮崎駿對烏托邦主義情結的揚棄,也是對這位名副其實的巨匠半個世紀創作生涯的一種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