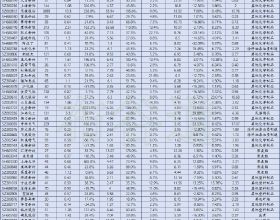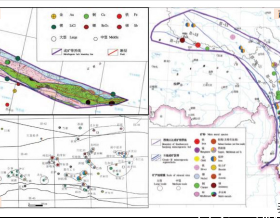我的母親老了。
我是家中七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么,虎年都快奔五十了,無論母親是否承認,她——我的母親都確實老了。
虎年春節,我陪母親過年。很多很多年都沒像今年這樣,大年二十四過小年這天就早早回老家陪著她了。
看見我回來,母親十分開心。她嘴上不說,像以前一樣,但她從病重導致的萎靡中瞬間振作起來,已經表露無遺。聽哥哥姐姐說,平時她因為病痛,都是躺著,躺著也不舒服,一會兒躺,一會兒斜倚,一會兒半躺著坐,口中不斷地痛苦的呻吟甚至喊叫。看見我回來,她努力坐起來,我扶著她靠在床頭,她撐著跟我說話,每講一句都像是用盡了全身力氣似的,聽得出她語氣中帶著十分沉重的病痛,但也明顯帶著無須掩飾的開心,甚至是一點點的興奮。
母親病得很重。都已到終末期的心衰和腎衰,把她的體力幾乎耗盡,把她原本不算瘦小的身軀幾乎掏空。每一次心跳湧入血管的血液,都已經難以支撐她走到老家的大門外了。
我沒有讓她看出我心裡的難過。我陪著她,坐在她的床邊,聽她費力地說話。母親可能是想要在我面前表現得身體狀況好一些,她掙扎著要下床來,我看見她先是把上身往後仰,兩隻手撐在身體兩邊,緩慢地把身體向右側向床邊,就這樣動了幾下,她已經大喘了幾口氣,我想扶她,她示意不用,停頓了一下後,她慢慢把右腳從被子裡挪到床邊,垂在床沿,然後再把左腳也從被子裡挪出來,再把身子也側過來,兩隻手撐著床沿,兩隻腳懸垂著,這時候她又粗重地喘了幾口氣,搖手示意我別動,她坐了一會兒,先伸出右腳哆嗦著去尋找就放在她腳前面的棉拖鞋,但一下夠不著,我幫她拿起來放到她右腳腳趾前,她用了起碼五秒鐘才把腳穿進敞口棉拖鞋裡……我扭過頭去,眼睛已經完全溼潤了。我沒有讓她發現,這可是我記憶中曾經多麼強悍的母親啊!
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們住在農村。那個時候,我家會種各種莊稼,日常生活所需的瓜果蔬菜等應有盡有,那時沒有現代化的灌溉系統,所有的莊稼都必須用肩挑手提的水去澆灌。
我記得有一個夏天,太陽很大,照到哪裡哪裡都白晃晃的,蹲低身子到與地平線幾乎平齊去看,地面上會蒸騰起好幾釐米高的像火焰那樣的熱浪。
我家有一片自家開墾的山地,在村子西頭那座名叫廟嶺的小山上,地裡當時種的辣椒,好像還有紅薯還是別的什麼,不記得了。那個夏天太熱太乾,莊稼都乾裂張開了大口子。母親和父親就帶著我和三姐去給莊稼澆水。那時我哥在外打工,二姐在長沙讀書,大姐已經嫁人(我二哥和四姐因當時條件不好早夭折了)。當時的澆水,都是用木桶,去到山腳下名叫廟塘的水塘裡,把水裝滿兩隻木桶,然後用扁擔肩挑,爬上廟嶺,再用木勺給莊稼一瓢一瓢地喂水。當時每家大都只有一擔(兩隻)水桶,我家我父親懂木工,自己做了兩擔,那天母親和父親自己各挑一擔,又去鄰居家借了兩擔比較小的分別給我和三姐用。母親和父親一樣,用的是父親做的水桶,容量比別家的大,估計盛滿水得有一百多斤。我家莊稼地離廟塘雖不算遠,也有兩三百米,母親就那樣挑著和父親肩上一般大的水桶,一趟一趟地,空桶下山,滿桶上山,一干就是一整個下午。我和三姐中途不知道休息了多少次,我記得母親就沒有歇息過,她的休息都是在挑著空桶下山的途中完成的。那時的母親,是多麼的強大。
比挑水澆莊稼更耗體力和耐力的,是挑塘泥。
那時我們村盛產臍橙。臍橙樹和臍橙掛果的生長,都需要肥料。如果肥料不足,不僅會導致臍橙成品個頭不大,還會甜味不夠,並且中途還容易落花。當時化肥是計劃管控產品,不知道是買不到化肥還是臍橙不適用化肥,每年開春後,母親和父親都會帶著我們去挑塘泥給臍橙樹當肥料。
塘泥就在臍橙園外大約兩百米的地方,是水塘枯水季節時露出來的水底淤泥,顏色越黑就越肥,由魚蝦蟲蟹的屍體和分泌物等與泥巴堆積而成,密度大,特別沉重。母親和父親帶著我們,一擔一擔把塘泥挑到臍橙園,堆在樹下,就像是給臍橙樹蓋上了一層厚厚的棉被,以提供足夠的養分直到臍橙長大成熟。記憶中那個時候的臍橙是最好吃的,以後再也沒有吃到那麼好吃那麼甜的臍橙了。
我記得父親講過,他每挑一擔塘泥,估計都在兩百斤以上,母親稍微少點,但也絕不會少於180斤左右。180斤啊,母親當時自己的體重也就120斤左右,1米6左右的個子。這還不算,關鍵是每次挑塘泥,一挑就是一個半天,來來回回好幾十趟,而在有塘泥的位置,淤泥的粘附力遠超平地,需要耗費更大的體力和耐力。
實在難以接受,當時那麼強悍的母親,現在居然連下個床穿個鞋子都是如此的吃力。我的眼睛又溼潤了,趕緊別過頭去,沒讓母親看見。
父親生前跟我們姊妹都說過,母親來到我們家時,我們家窮得什麼都沒有。父親與母親結婚時,父親是向鄰居借的一件襯衣穿著結的婚,父親祖孫三代單傳積弱積貧,到父親這一代已經是真正的家徒四壁。我們家是母親來後,用比男人更強悍的幹活掙“工分”,比男人更強悍地回擊別人早已習慣對我們家的欺凌,比男人更有計劃的精打細算……才與父親一起,漸漸地把我們家從村中的“底層”硬生生拉到了“上層”——不僅購買了全村第一臺黑白電視機、第一輛腳踏車,更培養出了全村第一個大學生!讓長期受欺負的我們家徹底站了起來、父親也徹底揚眉吐氣。
我很小還沒有記事的時候,母親是如何強悍的,只能從父親的講述中知曉,當我稍長大開始記事起,我自己看到的,親身所經歷的,還有好多好多事,母親確實如父親所說的那樣,她與父親一起努力支撐起了我們這個家,將我們兄弟姐妹都培養成了現在的模樣,她是一個長期真實的相當“強悍”的存在。
而到現在,歲月的侵蝕,病痛的無情,讓曾經那麼“強悍”的母親變成了如此的弱不禁風。
母親啊,您慢點兒,慢點兒下床來,我知道您見我回來您開心,但您慢點兒,慢點兒,儘量慢點兒走路,慢點兒老吧,讓我能再多喊幾年您有回應的——“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