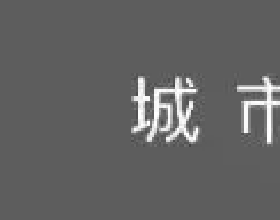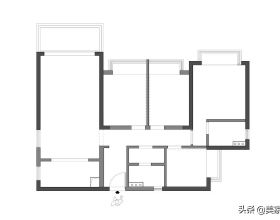原標題:【重推】蔣子龍的“文學頻道”
黃桂元
《人間世筆記》是蔣子龍最新出版的作品集。沉浸其間,一種熟悉的氣場撲面而來,那些律動著歲月潮汐和生命脈跳的音響,來自蔣子龍的“文學頻道”。此頻道的編排錄製,帶有剛正硬朗、大氣磅礴的“蔣氏風格”。蔣子龍是一位極具筆墨標識度的文壇硬漢,向來拒絕無病呻吟,他筆下的“雄性”氣息與時代脈跳、人間悲歡息息相關,這樣的事實,已被《喬廠長上任記》《開拓者》《蛇神》《農民帝國》等諸多作品所印證。《人間世筆記》表明,他的寫作力道一如既往,激情並未衰減,血性依然激盪,同時,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入木三分的觀察和思考,更多的境界深遠的悲憫與感嘆。
《人間世筆記》分四輯,主要由小說與散文(隨筆)兩類組成,總體延續了他磅礴、激越而不失深沉、凝重的美學風格,與煙火繚繞的生活現場形成了幽深而精妙的映象關係。其中小說的篇幅都不長,其構思仍對“任性妄為”青睞有加,人物性格常常出人意料,卻又與生活邏輯構成“自洽”。這個過程中,他注重用描寫而不是一般化的敘述推動故事,表現出深厚、老到的敘事功力。
蔣子龍的文字如堅韌的犁鏵,貼著地面深耕細耘。他始終關注“人”的境遇,從自己熟悉的工人生活起步,繼而瞭望大千社會,體察人間永珍,將形形色色的“人”收入自己的小說世界。在他的筆下,人世間的芸芸眾生既是社會的主體,更是被置放於複雜命運“關係”中的“這一個”。人物的命運軌跡懸念叢生,有的懸念是故事的“核”,有的懸念則瀰漫在撲朔迷離的情節氛圍中。把傳奇寫成日常事件,掌控文字的能力當然是最基本的,但同時更需要具備洞察和解碼人性秘密的本事方可透視人性,逼近生命真相。書中有的是真實人物,如郭振清、韓羽、賈大山等,更多則是作家根據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而舉一反三的各色人等。即使是寥寥幾百言的微小說,蔣子龍也能寫得方正大氣,紮實深邃。
這類小說多為筆記體,讀之像讀生活本身。筆記體小說發源於魏晉時期,魯迅將其分為“志人小說”和“志怪小說”,廣義上的“志人小說”多取材於民間,形式上幾乎包羅一切用文言體寫的志怪、傳奇、雜錄、瑣聞、傳記、隨筆之類作品,內容駁雜永珍不設藩籬。“志怪小說”則多受史書體例的影響,以史家的眼光處理筆記,與文學意義的小說創作有別。值得注意的是,筆記小說往往兼具“筆記”和“小說”的功能,融匯故事與傳說、寫實與寓言、敘述與議論,為作品提供了自由發揮的書寫空間,促成小說的敘事性和散文的自由度彼此滲透,相得益彰。
蔣子龍的“文學頻道”發出的是有感而發的聲音,正如其夫子自道,“當今這個世界多事,每天都有爆炸性的新聞,爆炸性的事故,有的事故里有故事,有的故事裡有事故,總體來講,這就是現實的人間世,我採用的筆記手法,無非是為了更真實地還原當下的人間世”。他從不刻意為小說提供形而上的思辨意味,亦不滿足於僅僅講述一個離奇古怪的俗世故事。《薛傻子》《雨夜南瓜地》,還有些小說或傳奇或荒誕,比如《狓子客》《名醫》《道爺》。此類作品語言簡約,惜墨如金,氛圍的渲染、細節的誇張、效果的靈異,都服務於筆記小說的內在張力。
蔣子龍始終有一種崇尚英雄主義的情結。《印度洋暗夜》寫了令人驚魂的一幕:巨輪天覺號正在洶湧滔天的海浪中傾斜,命懸一線,船上總價值少說也有一億四千萬美元,眼看要打水漂,公司老總餘乾寧心急如焚,拼力調動和求助一切力量,也沒能阻止船的下沉,值班電視中,出現了令人絕望的畫面,“南印度洋上雨過雲散,風平浪靜。正值午後,夕陽浴波,萬頃金光中天覺號只剩下一條白線……”很顯然,誰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事故和災難,關鍵是如何療傷,如何站起。餘乾寧默默駕車回家,不允許任何人打擾,把自己關在屋裡,呼呼大睡了一天一夜,經此大難,他的精神是昇華還是墜落?作家沒有提及。海明威《老人與海》中有句話,可做參考答案,“一個人可以接受被毀滅的事實,卻無法接受被打敗的事實”,對於餘乾寧即如此,他可以接受失敗,卻不會被擊垮。
我也很喜歡浪漫深情的《桃花水》。來自北京的畫家祝冰教授渾身充滿軍人的硬漢氣息,他在黃土高坡採風,遇見純樸健美的鄉下婦女孫秀禾,產生了為之雕塑的強烈願望,隨之誕生了愛情。
相戀者何以返璞歸真,跨越身份認同,創造人性的美和幸福,這才是蔣子龍意欲書寫之所在。孫秀禾對愛情是渴望的,也有尊嚴,“他為什麼非要給她留下那張卡?是認為農村人窮,瞧不起她?這讓她心裡很不自在。其實,她真不想要他的錢,而是想要那個塑像。可她張不開口,實際上也沒容她張口,那個瘋子抱著塑像就跑了”。如此脫俗之愛並沒有發生在世外桃源,卻有著童話般的詩意品格。
《人間世筆記》中的第四輯“碎思萬端”,也是一種別具深味的筆記。“我慶幸自己還有好奇之心。好奇才行走、閱讀、觀察、思索,或驚訝,或感動,或受益,都是一種收穫。於是才知天下之大,絕非‘小小寰球’”,可見好奇是蔣子龍寫作的動因之一。在“碎思”中,蔣子龍對“自傳性”寫作做了進一步說明,“作家分兩種:一種是把自己當寶貝,一種是把自己丟掉,又找了回來”。蔣子龍顯然屬於後者。好奇心源於不老的童心,使他敏於觀察新事物,接受新東西,與讀者分享其好奇心帶來的所見所聞所感。
蔣子龍的“碎思”如同炫目的萬花筒,聚集了豐富多樣的資訊,這得益於他的讀書習慣,“書讀得多就可以擁有多種經歷,選擇多種人生。不打麻藥便可以移植生命,將自己的一生銜接前人與古人,這豈不等於豐富和延長了自己的壽命?”
讀書使他能保持一份清醒,“無非是為了更真實地還原當下的人間世。”這個世界常常真假難辨,虛實莫測,“有真的嗎?智者答:災難是真的,痛苦從不說謊”。他的話題有巨大的包容性,“文明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有害變異的遺傳機率增加了,基因影響大腦活動,基因變異導致人類智力下降,自19世紀80年代至今,人類的平均智商已經降低了13分。”這類開腦洞、點穴位的“碎思”,在書中比比皆是。
《人間世筆記》體現了蔣子龍一以貫之的筆墨風格,進入晚境,其書寫姿態越發從容、通透、睿智、深刻,而又不失令人稱快的老辣與使人莞爾的幽默。無論小說還是散文隨筆,沒有花拳繡腿,沒有故弄玄虛,寓繁於簡,由博返約,小中見大,縮龍成寸。他不談風月,不道啟蒙,不言是非,不訴恩怨,這也正是其“文學頻道”的奧妙和魅力之所在。
(《人間世筆記》,蔣子龍著,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