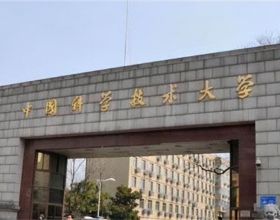1986年10月14日,我軍在老山前線組織實施了一次出擊拔點作戰行動,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
戰鬥結束後的當天傍晚,由於再沒有下陣地的車了,我便擠在一輛護送重傷員的救護車上,從老山主峰向南溫河戰地醫院行進。
戰士們給受傷的鴿子療傷
那是一個長方體的封閉式車箱,裡面的空間很小,左右兩邊是長條凳,中間有一米左右寬的空間裡擺放著一副擔架,上面躺著一位昏迷不醒的重傷員。
也許是由於情況太緊急了,誰也沒有搞清楚傷員的名字。在他的治療單上的個人資訊欄裡,只填寫著戰勤隊戰士的字樣。在病歷欄裡填寫著戰傷、胸腹部大面積創傷,昏迷等字樣。在治療措施欄內填寫著清洗、止血、取出5塊彈片、包紮、消炎、緊急轉移等字樣。
在搖搖晃晃的救護車上,我和一名我不認識的男醫生、兩名我不認識的女護士分開坐在車箱兩邊的長條凳上,誰也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注視著輸液架上的液體一滴一滴地滲進那位戰士的血管裡。
剛開始,他靜靜地躺在擔架上,像睡著了似的,看上去有20歲左右,年輕英俊的臉上,煞白煞白的,沒有一絲一毫的傷痕。
大概行進了十分鐘左右,他的左手突然伸起來,在空中揮了一下,又重重地砸在了醫生的膝蓋上,緊接著又蹬了幾下腿。
頓時,狹小的車箱裡忙亂了起來,一個護士壓著他扎著針的右手,另一個護士忙著給他量血壓,醫生左手拿著一個小手電筒,右手翻開他的眼皮觀察他的生命體徵,我怕影響醫護人員的工作,躲在車箱的后角貓著。
不一會兒,傷員變得更加躁動起來,又是蹬腿,又是抓胸,還大聲喊大叫:“班長……還有傷員……沒背下來……我去……”
突擊隊員在屯兵洞裡等待戰鬥命令的下達
醫生趕緊敲了幾下車箱,讓司機開得再慢一些,然後吩咐一個護士給傷員打針。讓另外一個護士幫著他掀開了傷員的被子,開始檢查他的傷口。
這時,我才發現,這位傷員的大半個身子上纏著紗布,從胸口到小腹的紗布已經被鮮血浸透了,溼漉漉的,殷紅殷紅的。
打完針並對傷口做了簡單處理之後,三個醫護人員背靠著兩邊的長條蹬,蹲在了傷員的左右兩側(左邊兩人右邊一人),十分小心地抓著傷員的手,拉著傷員的腿,繼續晃晃悠悠地緩緩前行。
傷員一會兒平靜,一會兒煩躁,一會兒喃喃自語地過了十分鐘左右,他忽然鎮定下來了,甦醒過來了,輕聲問道:“我這是在什麼地方?”
醫生告訴他在去醫院的路上。
他又用左手摸著自己的上身,好像在尋找著什麼。
醫生問他需要什麼東西嗎?
他有氣無力地說:“照片。”
醫生問他什麼照片?放在哪裡?
他說:“衣服。”
一個哨所前被炮彈炸在了白花花一片
一名護士趕緊開啟一包用床單裹著的東西,只見裡面包裹著的是從這位傷員身上剪下來的血衣。她對血衣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後,從上衣口袋裡翻出了一張被鮮血染紅了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個端莊秀麗的姑娘,照片的背面還寫有文字,雖然也已經被鮮血模糊了,但字跡依稀可見:“別忘了我,我在等著你回來!1985.11.2
我們都明白了這張照片在這位戰士心中的份量,那位護士眼含著熱淚將被鮮血染紅的照片遞到了這位戰士的手裡。
他拿著這張照片,微微地睜了睜眼睛,喃喃地說道:“你的臉怎麼了?我怎麼看不清了?”
話音剛落,他的身子又猛烈地顫動了一陣,拿著照片的左手不聽使喚地落到了擔架邊上,照片掉落在了他的胸前。
三位醫護人員剛要對他採取搶救措施,卻只聽他呻吟了一下,長出了一口氣,兩行熱淚從眼眶裡奔湧而出,便失去了生命的氣息……
天已經黑下來了,車子還在搖搖晃晃地向前行進,車箱內除了我們四個活人和一具烈士遺體外,還多出了一張被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的照片。
我瞅著那張照片,越瞅越模糊了,瞅著瞅著,什麼也看不見了。我只是在想,他是我在當天所見到的第26位犧牲了的戰士,他們的年齡都差不多,這張被鮮血染紅了的照片,不就是他們每個人心中的秘密嗎?
頓時,一股強烈的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複雜情感在我的心中湧動起來,憋得我喘不過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