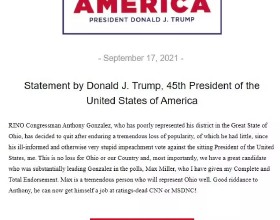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在理論層面上,古人並沒有給我們留下哪怕是一篇色彩專門的著作。在現代學術當中,也缺少一箇中國傳統色彩的學科,或者以中國傳統色彩為中心詞的話語平臺。中國傳統色彩的研究者分散在各個學科領域,他們或是語言學家,從顏色詞這個角度探知中國古代的色彩思維;或是染織專家,從紋樣的角度探究中國古代的配色規律;或是建築專家,從彩繪角度探求中國古代的色彩構成;或是陶瓷專家,從釉色角度來辨析中國古代的色彩質地;或是美術史家,從繪畫角度探研中國古代的色彩樣式與表現。
正是因為色彩研究長期分散在不同的學科,一個對話的平臺的建立才顯得非常重要。2016年發起的“中國傳統色彩年會”,經過6年的時間已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和集中的學術議題。近些年有感於年輕力量的崛起,汕頭大學教授、色彩研究者陳彥青、肖世孟發起“中國傳統色彩學術研究青年論壇(2021)”,並在最近舉辦了探討會。本屆論壇共設4場主題演講與學術討論,與會學者們圍繞色彩觀念、色彩文化、色彩科學與應用和白色專題,從繪畫色彩、建築色彩、服飾色彩、陶瓷色彩、染織色彩、色彩術語、顏料工藝等諸多視角展開,對傳統色彩的觀念、文化、歷史、形象、技術、應用等不同方面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
變化中的“色彩觀念”
色彩觀念是討論傳統色彩相關內容的一個本源性的問題,關於色彩觀念的討論,包括觀念背後衍生的問題、某些觀念的消失或者生長,觀念對色彩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歷史中的應用等等,而色彩觀念常常也在色彩研究的背後起到本源性的支撐作用。
清華大學副教授李路珂以《中國傳統色彩體系建構新探》進行了分享,她談及,在知網檢索跟傳統色彩相關的主題詞會發現,不同的學科類別在色彩的語境下是處於一種高度交織的狀態,因而色彩研究需要運用多學科的視角、基於多方共同積累的資料和資料來進行。“我覺得未來的色彩體系研究,應該要有一種色彩來源的全面性,還應該有一種表色方法的科學性,同時它的資料和文獻來源應該要詳實,這個體系也應該要開放。我們的研究視角需要解決物質材料、色度表徵、視覺感知和文化意象等多方面的問題。”
李路珂也從自己的研究領域談了中國古代建築色彩研究的一些主要的難點:“我覺得最難的是關於原狀的研究,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統色彩的實物其實都是經過變色的。比如我們對於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北宋時期彩畫做復原研究,需要透過6種不同的適應條件來模擬6種不同的引起顏料老化的自然環境,從中尋找一些色素變化的規律。其次是關聯性的研究,以地下墓葬的整體空間的色彩關聯的研究為例,首先是要做色彩復原,要基於原狀推測做一個色彩圖譜,對它的色譜和色彩的面積關係、色空間分佈進行分析,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取它的典型色的分佈。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晰看到不同的主題對色彩配置的影響,結合一些文獻和其他建築空間的分析,我們就能對色彩的適用方法進行進一步的瞭解。”
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壁畫
湖北美術學院副教授曹英傑以“佛教經論色彩研究概述”為主題進行了分享,認為漢文佛教經典中的色彩是不可或缺的,顏色在佛經敘事與教育表達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佛經色彩一定要注重色彩的抽象性研究,還有極具佛教特色的意念性的研究。比如觀想是佛經中一種很重要的修行方式,人死之後從屍體到最後消亡有4個顏色階段:青、黑青、赤、白4個顏色,這4個顏色就是一種意念色,只存在於佛教徒的觀想、意念中。”
深圳大學助理教授肖浪關注“中國傳統色彩網路化過程中的認知變遷”。肖浪檢索發現,廣東省是近幾年對於傳統色彩的檢索率最高的省份之一,而這個檢索結果也與很流行的國潮關鍵詞的檢索結果基本上吻合。國潮和中國傳統色彩有許多相似性和重疊性,這也為這個選題的立論提供了一個基礎的背景。
“中國傳統的色彩文化在新媒體上傳播途徑可以簡單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簡單的色相;第二類是色相再加上簡單的說明文字;第三類是把色相物化,將它與服裝、傢俱、包裝,甚至一些抽象的節氣概念相關聯。我們會發現,第三類的傳播最值得注意:它常常有基於流量演算法的具體受眾,並希望能夠產生經濟效益,所以它給觀眾的‘刺激’也不斷被加固,我們甚至能夠看到一系列的把這種傳統色彩固化在某一個空間,某一個環境,某一種物品上面的情況,我們承認這樣的行為帶來了無盡的商機,但確實也侷限了觀者的思維和認知,所以隨著網路經濟的發展,我們再去提取關鍵詞的時候,會發現關鍵詞的高頻詞裡面很多都是和消費主義的想象相關的。當我們再去搜索一種顏色時,會發現檢索到的內容和真正的科普內容相去甚遠。所以在不斷的刺激傳播的過程當中,越來越多的色彩文化開始被固化。”肖浪談道。
“色彩文化”:色彩落在具體的物上
色彩文化看似是一個很大的概念,而學者們在討論它的時候都必須落在歷史事物的非常具體的表徵上,色彩文化的研究涉及的是某種時空的關聯性,體現關聯的同時,色彩現象發生的差異上也顯現了。
北京聯合大學的曲音介紹了日本平安時代女房(女官)服飾的色彩搭配,認為:“平安時代的服飾其實不論是形制還是色彩,都遵循了從簡到繁,從籠統到細化的一個變化過程,雖然不能完全拋開唐風的影響,但卻是日本傳統色彩觀的一次關鍵性的轉變。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平安人逐漸明確了多層次的色彩感知方式,展現了獨特的服飾色彩、視覺與觀念體系。服飾色彩中的裡與外透過色彩逐層排列定製和疊加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連線方式。裡外的色彩模式並不是在單純製造區隔,而更重要的是創造連線,透過這種方式獲得色彩與色彩間的連線,形成平衡穩定和諧的一個視感,同時借服飾色彩的演化被連線的物件也可以指向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內在自我等等。”
浙江工業大學講師隋豔的《中國傳統園林植物色彩人文性初探》總結中國古典園林作為山水文化的載體,歷經各朝代文化的洗禮,對映的出中國傳統審美的價值觀。植物色彩作為植物造景的重要組成部分,亦彰顯出了人文性和美學性。
絕大部分關於園林植物的論述散落在文人養生著作或遊記之中,且只有文字並未配圖,這種困境阻擾了傳統園林植物色彩研究的發展。隋豔將園林植物色彩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啟蒙階段,上古神話《山海經》中對於植物色彩的描述已經存在,但經常能見到的植物顏色是紅、黑、白、黃,甚少能見到紫、青色。第二個階段為發展階段,從唐代至宋代山水畫的興起,影響到了園林的總體佈局和對於園林整體色彩的植物的把握。當時園林追求的意境為簡遠、舒朗、雅緻,至宋代山水詩、山水畫、山水園互相滲透,審美觀念深入到細節,園林植物色彩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第三個階段為成熟期,明代文人士大夫隱匿思想日甚,很多人歸隱於園林。此時園林在風格上延續了宋代的意蘊,園林的審美正規化已經趨於成熟,有大量園林著作整理歸納了植物營造的方法和植物色彩的美學觀念,後因遊記的盛行,出現了體悟式著作,如張岱的《西湖夢尋》等。
受農耕文化的影響,早期園林植物兼備實用性和觀賞性,後隨著山水文化的興起,人們對於植物色彩的關注側重於花色和果色,花色的重要性逐漸甚於果色,喬木以常綠為主,像木樨之類的江南喬木,自宋代以後備受推崇,成為了主要的觀賞樹種,植物色彩的營造上,總體呈現出由濃墨重彩向水墨淡彩轉變的趨勢。從色彩的明度和純度上來看,園林植物色彩多集中於高明度、高純度低豔度的部分。從色彩感知上看,冷暖適中,色彩輕重有較大的差距,少量暖青色起到點綴的作用。
湖南工程大學副教授王興業從民俗學角度出發,透過文獻的梳理,從五行、從禮制、習俗、公用等多個維度,分析了傳統服飾中忌白用白的特殊現象。他提出,白色是中國古代禮制制度的重要組成,白衣是自周代到現代變化最小的色彩文化現象,中國色彩裡相對炫目與稀貴的顏色,比如橙色、黃色、紫色等等,地位在歷史中是上升的,白色則相對穩定。素白也與凶禮有關,白色不單純是喪服的專屬,它也是凶禮的專用的色彩。古代在投降禮儀中,投降的一方需要著白衣、騎白馬等。
除了禮制,白色給人的感覺是平和、素簡的,但也不是一種積極的心理體驗。比如馬遠的《寒江獨釣圖》中,在茫茫一片寒冷中等著魚上鉤,其實是一種不太舒適的感覺。
江省博物館沈小琛對傳統色彩中白色觀念的梳理,試圖討論古人用白與忌白的矛盾現實之中所蘊含的美學思想。沈小琛提出傳統白色的觀念印象,主要分為三類,一種是不俗之白與美感之白,包括在對人外貌及品行的形容中也包括在工藝美術中;一種是以白延伸為虛、空、無等哲學認知,比如莊子講虛生白,這種觀念將白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層面;第三種則是常被討論的不吉之白,這一點在中國的傳統色彩領域當中、在我們的服飾器具包括喪葬工藝上面體現的最為明顯。
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磊反思了“殷人尚白”與“秦為金德”說。在五德終始的傳統下,白色作為一種王朝法統的標誌與象徵,被賦予的豐富政治文化內涵。但曾磊考證後認為,對於一個朝代的評判還要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中,“所謂殷人尚白問題,可能也是後人對前代的一種想象,王朝尚色跟用色的習俗不能完全等同起來,所以殷人可能確實有白色的偏好,但是能否能視作其確實是尚白,是另一碼事。類似我們看到漢代也經常有白色物品,漢代經常做將白色物品作為祭品,但是漢代其實並不尚白,所以殷人尚白說,它其實是一種歷史假設,它在後代不斷的推演,不斷的變化,逐漸的被人們所認可。”
責任編輯:梁佳 圖片編輯:沈軻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