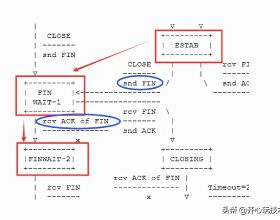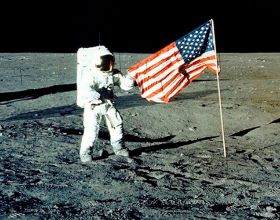“還沒有交,昨天的語文作業的同學,請現在及時補交上來,絕對不能少一個!”在講臺上,我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這聲音在教室裡來回蕩了好幾圈,才平息下來。
在我的威懾下,陸續有幾個同學把試卷交了上來。我一清點,還缺兩三個沒有交。
“有些同學經常不按時交作業,前一天剛發的試卷,第二天就找不見,這是態度不端正的表現!同學們,態度決定一切呀,啊!”我說話的聲調有些重,甚至有點嘶聲力竭。
說著說著,我的怒氣開始往上湧,右手手掌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講臺,發出“啪”的一聲,這力度說重也重,說輕也輕。瞬間,下面的同學個個屏住呼吸,大氣不敢出。
不久之後,有一道黑影從座位上躍出,像幽靈一般竄到講臺前。我定睛一看,原來是這個班的“怪才”班長李威(化名)同學。我正回過神時,只見他右手往講臺上一甩,一片片小紙片在講臺上爆炸開來,撒滿了整個講臺。這些小紙片本來是要上交的試卷的,現在已經被他撕得粉碎。試卷算交了,但這試卷卻如一顆支離破碎的心,無法復原了。此刻,我一怔一怔的,座位上的每一個同學也是一愣一愣的。
李威這傢伙扔完粉碎的試卷後,昂首挺胸,理直氣壯地走回了他的座位,那神態竟像一個凱旋而歸的角鬥士。隨後,只見他一屁股坐到座位上,歪著頭,氣定神閒地朝著我看,那神情儼然是一副“老師,我看你能拿我什麼著”的表情包。
教室裡的空氣像是結了冰似的快要凝固了……
我心一沉,又用兩秒鐘的時間瞅了一下這傢伙,只見他的眼睛一眨一眨的,一臉揶揄的神情,一副挑釁的模樣,好像在說:“語文老師,我的表演已經結束了啵,現在該輪到你上場了!”
我嘛,從教這麼多年,也不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狠”角色,我最基本的應變能力還是有的。我故意清了一下嗓門,然後笑了笑說:“李威同學,我只是要求交一張試卷的,而你卻交了那麼多張,我可改不了那麼多呀!”聽我這麼一說,底下的同學們發出了陣陣笑聲,教室裡的氣氛一下子舒緩下來。接下來的課上得很順利,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
這個李威同學,小帥哥一枚,人很機靈,作文出眾,文采斐然。他在作文《父母給的愛讓我難以忘懷》中這樣寫道:“我家有二寶:一寶,老爸;二寶,老媽。老爸給我的愛,似火,剛猛而熾烈,卻飽含深情;老媽給我的愛,似雨,點點滴滴,給我無限滋潤。這兩寶給我的愛,讓我難以忘懷。”這文字,是多麼地深情又有文采。
他在作文《來自你的關愛》中寫道:“廚房裡,你的背影如此真實,始終披著黑色的圍裙。餐桌上,你的手顫巍巍地拿起筷子,再顫巍巍地把肉和青菜夾入我的碗裡。碗裡那份僅存的青與白像極了你的臉色。你總是微微一笑,很釋然。而我心裡眼裡卻噙滿了淚。待你轉身時,我的眼淚流下來了。那淚打在碗裡,像悲愴的交響樂……”這文字,是多麼地接地氣又感人。
他還在作文《自尊在我心中永駐》中寫道:“那一天的那一幕,久不久又在我眼前浮現,它將成為我往後做人的一個座標。從此,我要對自己說:‘自尊,是我做人的根本。我要做一個有自尊的人,做一個完整的人。讓自尊永駐在我心中吧。’”這文字,點題到位,又有哲理。
有一次,我把李威同學寫的作文給他的媽媽看,他的媽媽看後,回覆我說:“看了兒子寫的作文,我淚流滿面……”我能想像得到他們一家三口相處時,曾經是那樣的幸福快樂!
要知道這些作文都是他在七年級的時候寫的,可是上了八年級後,他變了……
只因,他的父母離異了,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支離破碎,就像他撕碎的那張試卷般,再也無法復原。這對李威同學的打擊實在太大了。
更為可惜的是,深受家庭變故影響的他,小聰明用錯了地方,他開始沉迷電腦網路遊戲,把網咖當成了家,並一發不可收拾。他週末和假期裡沒日沒夜地玩遊戲,沒有一點時間觀念,沒有一點節制,爺爺奶奶管也管不住。回校後,上課時他大多是打瞌睡或是伏桌子睡覺。他也曾多次逃學,曾經有一次夜裡,他一個人躲到那打水庫的一間廢棄的小黑屋裡,給老師和家人找得天翻地覆。他是我當老師以來碰到的最為可惜的一個學生,憑他的能力,只要他肯使三分的力,上重點高中是分分鐘的事。
那天上課後,過了兩三天,我在教學樓一樓的走廊上碰到他,我朝他叫道:“李威,你過來一下,我有話要跟你說。”
他站到我的面前後,我嚴肅且很正經地對他說:“那天你不交作業,我沒有點過你的名字,我很是給你面子的,而你的舉動,卻傷了老師的自尊心。你難道忘記了你寫的那篇《自尊在我心中永駐》的作文了嗎?你說你自尊心重,希望能得到別人的尊重;老師也是人,也渴望能得到學生的尊重的呀!”
他聽後,用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看著我,沒有吭聲。我接著說:“你如果知道錯了,你應該跟我道個歉。如果你現在沒意識到自己錯了,那我可以等……5年後,你知道自己錯了,5年後你再跟我道歉。10年後,你知道自己錯了,10年後你再跟我道歉。20年後,你才知道自己錯了,20年後你再跟我道歉。我給你最長20年的期限!”
他聽後,眉頭一皺,但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我叫他離開了,然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如今5年過去了,將進入10年的限期,我至今仍未等到他的一聲:老師,對不起!
我也不渴求20年後的他能給我說一句道歉的話。但是我隱約能感覺到,這個等待20年的道歉,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只要有合適的溫度,有適宜的陽光,有足夠的養分,有一天,這朵花終究會開放的,我期待著……
但是,男人嘛,永遠是長不大的動物,何況是學生,他當時也還只是個孩子。我不應該用成年人的眼光去苛求一個孩子用光十幾年來所積攢的一點點尊嚴,來向老師道個歉,這樣會很傷他的自尊心的。但是我給他20年的期限,到時他也該長熟了吧,時間也總該夠了吧!
幼稚,終究被風塵掩埋;任性,終究被時光遺忘;狂妄,終究被現實打敗。當孩子覺悟時,也許已經晚了;當孩子成長後,也許已經敗了;當孩子知錯時,也許再也找不到補過的機會。
一個等待20年的道歉,如果等不來,再等20年又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