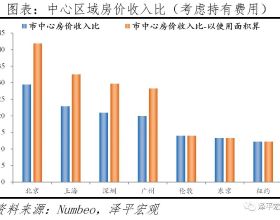老知青家園 2018-10-17
上海知青在北大荒一待就是30年
朱曉軍 楊麗萍
摘自《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
人物簡介:
韋建華,上海知青,1950年3月3日生人,1966年初中畢業,1968年8月26日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二十七團,在一連當過農工,1972年1月25日結婚嫁入赫哲族人家,婚後生有一對兒女,兒子留在身邊,女兒送回上海,恢復高考時,為婚姻而放棄返城。知青大返城後,調入勤得利郵政局。1993年退休,1977年攜夫與子返回到上海,貨款置房,憑著上海人的精明,北大荒人的艱苦奮鬥過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韋建華(右)
1
我在北大荒待了30年。
返城機會?機會倒是有的,1975年,我媽媽退休,我讓妹妹接了班。她是六八屆畢業的,去北大荒投奔我,下鄉到十三連。我讓她回了上海。
恢復高考頭一年,我們家付中義就叫我去考。
我是六六屆老初三的,我記性很好,(讀書時)學習一直不錯,畢業後才“文革”。
付忠義說:“你複習複習,肯定能考上。”
我說:“我不考。”
付忠義工資低,四十多塊不到五十,要養兩個孩子。老大在上海我母親那兒,月月寄錢,再供我上大學,一筆錢分四下,哪夠啊。1972年,我結婚那年,父親已經去世。母親退休了,也沒能力供我讀書。
怎麼下鄉到北大荒的?1966年初中畢業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在家待了兩年就開始上山下鄉了。我們家姐妹五個,五朵金花,我老大。父親是工廠的工人,母親以前是家庭婦女,家裡孩子多生活困難就工作了,在一家工廠的食堂。
我妹妹是六八屆的,老師嚇唬我們:“你們兩個得有一個去北大荒。”我想,我走遠一點,我妹妹就能離家近一點兒。我有五個閨蜜,兩個選擇去北大荒。我說我跟你們去北大荒吧,我不太喜歡南方的水田,也有到外邊闖蕩闖蕩的想法。
我是1968年下鄉的。剛下鄉的時候,我在農工班,本地小青年說我長得漂亮,又冷又傲。機務排的本地的多,他們看到城裡的姑娘想接觸又不敢,就調皮搗蛋地逗逗。我跟他們是不說話的,個別淘氣的來拉我的手一下。我拿出手絹擦擦手,把手絹扔了。
我在連隊很不得志,也很壓抑。珍寶島局勢緊張後,成立武裝連隊,我家庭出身比較清白,把我調了過去。武裝連隊說我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又把我弄下來,去了農工排。你心高氣傲,人家不拿你當個東西,你傲什麼傲呀?
收割時正好是雨季,麥子澇在水裡頭,連搶帶割一個多月,來例假都不讓你請假。立秋後,黑龍江邊已很冷了,腳得咬著牙往田裡踩,在水裡頭一浸浸一天,早上出去穿條幹淨褲子,回來時髒得都洗不出來,都是褐黃色的泥。下工回到宿舍洗完臉洗完腳,拎著脫下來的褲子到小水溝去洗,洗完晾到外面的曬衣繩上。第二天早上起來,褲子根本不幹。很多人身體就這樣弄壞了,造完了。我的腰椎間盤突出、腿疼就那時落下的。
從上海到東北,在劉英俊紀念碑前,韋建華(前排右一)與同校同學合影
8月草最肥美,荒草墊子裡面蚊子大著呢,就聽見蚊子在你跟前“嗡嗡”地飛,吃飯時張開嘴,弄不好就帶兩個蚊子進去了。東北打草你見過嗎? 男的拿大扇刀,長的80公分,短的也有50公分,靠著腰勁一扭“唰”的一片,一米來寬的草就割倒了。女的沒勁,用小鐮刀割。冬天牛羊馬吃的草料,苫屋頂、編蓋糧食用的草簾子,都靠割的草。
剛下鄉時的指導員很好,部隊營級轉業幹部,後來提為別的團的副團級了。他走前特意把我叫到家,他老婆也在。他說,新來的指導員生活作風不好,跟小姨子亂搞過,小姨子懷過孕,你長得太漂亮了,要提防點兒他。
新指導員上任後,總有意無意想接近我。我故意疏遠他,離他遠一點。跟我一起下鄉的“小辣椒”偷出我的信件給了指導員,他就借這個引子引誘我。父親上班路上認識了一個送牛奶的男孩。送牛奶有車,他就讓我父親搭一段路,兩個人就熟了。他是1946年生的,屬狗,我父親也屬狗,兩個人像有緣似的。我父親有意把我嫁給他,說得也不太明白。那小子上我家來過幾趟,可能有那個意思吧。後來,他參軍走了。他是上海郊區的,我下鄉時為什麼沒去郊區農場?我那樣不等於送上門了嗎?跟他又沒什麼感情,家裡來信跟我又說起這個事。指導員見我沒上他的當,他就告訴手下的人打擊我。
“小辣椒”為了保送上大學,跟指導員發生男女關係。結果沒走上,她就把指導員咬出來了。我說,他那時候那麼勾引我,我要想上大學,應該頭一個走。“小辣椒”還不是自己立場不堅定。
我怎麼認識老付家?老付家兩個小子跟我在一個連——一連,我老婆婆在一連的縫紉組,跟我挺熟。青年剛下鄉那會兒,男孩縫縫補補都不會嘛,我老婆婆手比較巧,一般衣服什麼的都會做,給小青年縫縫補補的,跟大家處得挺好。
付忠義的表妹,他大舅的二姑娘跟我睡一個炕。我倆挺說得來的,沒事領我去她姑家,離得都很近。他表妹總領我去老付家,就有給我們牽線的意思。當年小青年說我這個人很傲,一般人不敢接近。他弟弟付忠喜卻看中了我,他跟他媽說了。他媽說,你大哥還沒結婚,你倒先想結婚了,給你大哥吧。我老婆婆有這個意思,時間長了也就成了。
談戀愛?其實也沒談什麼戀愛,說不好聽的話,我們結婚前連手都沒拉過,我找付忠義,就是尋思找個當地的,有個靠山,不被指導員欺負。當時上海、北京的知青都找我,我不跟他們談。老付是黨員,不歸指導員管,只要跳出他這一塊,他奈何不了我。我有這個想法才找的付忠義。
我們家老付這個人別的好處一點沒有,就是一個老實。老付有過一個物件,赫哲族姑娘,沾著點親戚,是他二姨夫那邊的,屬於父母包辦的。老輩跟蘇聯通婚的也不少,以前赫哲族女人難產,蘇聯動用飛機接到那邊去生產。我老婆婆都準備給他們結婚了,領導就找他了。那時跟蘇聯關係緊張嘛,領導說你剛入黨,組織對你還在考驗中,不好跟“蘇修”扯上關係,這事兒就拉倒了。
我們家老付那時在八岔郵局上班,一米七四,不黑,他們哥們長得挺像的。他13歲就上郵局上班,掙錢養家了。那時,他只要回來了,兩個弟弟就偷偷告訴我:“我哥回來啦,叫你去呢。”我就上他家玩一會兒。他兩個弟弟都在跟前,我們也沒什麼好嘮。
指導員找我談話:“聽說你談物件了?”我也不敢承認啊,那時不允許知青談物件,承認不是找挨斥兒嗎?我說沒有啊。他說:“沒有?我都聽說了。”我來脾氣了,我說,說我有啥關係?說你指導員的都有。他說,怎麼個說法?我說,別人說你的話,我信,我也不信。我不相信你指導員能做那個缺德事。他說那你怎麼又相信呢?我說我相信呢,因為說這個事兒的人不是小老百姓,不是一般人,也不是空穴來風。
我實際上是告訴他別動我的腦筋了。他恨我恨得要命,處處想捏死我。
我爸比較開明的,知道我談物件,就問了一句:“民族政策你瞭解嗎?赫哲族風俗習慣你知道嗎?首先不能違反政策,別到時候一杯苦酒喝下去,你連哭的地方都沒有。”聽說我要結婚,我母親給我寄了兩床被面、兩套衣服。我婆婆給我做了兩床新被。老付要跟我結婚,調回了勤得利郵局。我們是1972年1月結的婚,我22歲,老付是25歲,他比我大3歲。
結婚生了小孩,我就調到農場物資科去了。老付是物資科的支部委員,郵局就他一個黨員,業務歸縣裡管,組織生活要在當地過。人家對我比較客氣,物資科有幾個上海知青也比較談得來,不像在一連,指導員偷偷摸摸總想弄你,我的日子就比較好一點了。
韋建華與付忠義結婚照
2
“你考吧,我供你。”
我們家付忠義說:“你考吧,我供你。”
他想讓我發揮更大的能力,覺得我這輩子幹啥都拿得起放得下。
我說:“一方面我如果考上了沒有經濟來源,另一方面我不想欠你的情。”
為什麼不想欠?我們文化差異本來就夠大的了,他才(讀)小學五年級,我初中畢業;他是鄉下的,我是城市的,見識比他強,處事比他果斷。雖說我比你高一點,距離還不算太遠,還可以平起平坐。如果我考上大學,我們文化上的差異拉得更大了。沒有了共同語言,硬捆綁在一起,對誰來說都不好,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我要瞧不起你嘛,人家說我沒良心,我也委屈我自己,我也不想這麼幹。我要上大學不可能再回來了,兩個孩子他帶一個,我帶一個,孩子缺爹少媽,這個家分成了兩半。人家會罵我是“女陳世美”,還有兩個“孽債”,我不想這麼幹,所以我就沒考大學。
遺憾肯定有的。我家姐妹五個學習都很好,我從小就被我爸當男孩養,他一心想培養我。我爸跟我商量過:“供五個女兒上大學,我是沒那個力量。你是老大,英語學得很好,長得也不錯。”父親想讓我初中畢業考外語學校,將來當翻譯。
我父親出生6個月過繼給了有錢人家,6歲上學讀書,讀的是1949年前的貴族學校,跳了好幾級,11歲就初中畢業了。他本來是苦出身,爺爺奶奶生了四個兒子,兩個女兒,父親是最小的一個。他畢業時那家破產了,養父死在監獄,父親只得到洋行做事。他的英語特別好,能說能寫。19歲時,他覺得老給人家聽差臉面上過不去,就不幹了。
沒考大學是個遺憾,我考上大學不是也圓我爸一個夢嗎?
知青大返城時,我想不想回來?也想回來,可是我知道家裡沒有實力,父親已經走了,母親沒有那個能力,另外回上海有份好活兒還行,沒有活兒誰養活我?我一個人回去了,假離婚要變成真離婚也不好,我對感情還是比較專一的。
我屬於哪一種?可以這麼說吧,真正的賢妻良母,找了一個男的,就不再有非分之想,死心塌地跟他過日子。
剛結婚的時候,總有一點互不相讓,也吵過鬧過。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他的大男子主義。
我老婆婆愛出去玩,我們家老付就不知道幫我幹活,老跟我急眼,覺得我幹多少活都是應該的。他們哥們家務活都不幹,這一輩子我也挺傷心的。就說洗衣服,老付根本不洗,都是我洗。我還是上海那個習慣,髒衣裳從來不過夜,今天換下來的衣裳今晚必須洗掉,內衣三四天就要換。
勤得利那時候窮,不少人都沒有內衣,冬天就是一件小棉襖,外面套一件大棉襖,進屋把大棉襖脫了。一件小棉襖穿一冬天,他們也不洗澡啊。我跟老付結婚的時候,給他買了兩套新衣服。那舊衣裳也不能不穿吧,我拿出來一看,我的天哪,他年輕時身上透油啊,棉毛衣褲穿在身上像紇帛似的,梆梆硬,穿在身上能貼身嗎?我就給他洗,搞熱水泡泡,打上肥皂溜滑,使勁搓,搓乾淨了,再打肥皂,再漚一會兒,漚好了再搓,搓完了在開水裡頭煮,來回洗幾遍,那件衣裳才洗出來了,軟和了。結婚後,他的衣服拿出來除了破的,沒有一件烏七八糟的,都清清爽爽的。
在東北,有些人家孩子的尿布子是不洗的,用完了往火牆上一搭,烤乾了再用。我們跟前有個老太太,孫女是8月份生的,比我家老大大一點,他們的家不能進,一進屋尿騷味兒打鼻子。我都是弄點水搓搓,搓乾淨了再拿開水燙一下,完了再擱火牆上晾開。用的時候拿手搓搓,搓軟和了再給孩子用。孩子的衣服不多,沒有一件穿得嘎巴嘎巴洗不出來的,薄的每天洗,絨的最多兩三天洗。
頭一個孩子9月生的,再冷的天兒,一週也要給孩子洗一兩次澡。連小叔子都服我,說這麼冷的天,你還敢給孩子洗澡?小蘇(桂蘭)就不行,給孩子洗一回澡,孩子感冒一次。我們兩孩子洗澡時,凍得嘴唇發紫,洗完澡餵飽他,包好了睡一覺,一出汗,啥事兒都沒有了。
我的兩個孩子身上奶腥味、尿騷味兒都沒有,都很乾淨。我是屬鴨子的,天天要洗的,洗臉洗腳洗屁股,一天不洗都不行。我們家老付叫我改過來了,他要不洗,我說你別碰我,你也別上床,你不講衛生我要得病的。我老婆婆不怎麼洗,她洗頭洗臉,夏天到江裡頭泡一泡,遊游泳,搓搓澡,冬天能不洗就不洗了,也算是乾淨了。
上海男人洗衣做飯都會,捨不得老婆幹活的。我爸可心疼我媽了,以前沒有洗衣機,我們家姑娘多嘛,小的衣服——背心褲衩、夏天的衣裳我媽洗,冬天的大厚衣裳、被單都是我爸洗,我媽從來不洗。上海女人也比較獨立,從新中國成立前到現在,女的一直是上班掙錢,不像東北男的出去掙錢,女的在家伺候老的小的。男的拿著大老爺們的架子,對老婆吆喝來吆喝去。
東北的男的,總是有一股大男子主義。老二9個月時,我在物資科食堂,冬天輪著到煤廠幫忙卸煤,到點沒去餵奶,孩子不鬧嘛。正好郵車也來了,老付要分信,分報紙,分包裹什麼的,等不來我就把孩子送過來。他把孩子往地下一扔就走了。孩子哇哇哭,我抱起來。這把我氣的,我說我要是出去玩也行,哪有你這麼樣的,你上班我也上班,你是治我呢,還是治孩子?
我是上海人嘛,比較會做飯,他舅舅在郵局,經常到我們家吃飯。他們的風俗是家裡來了客人,男的陪著喝酒吃飯,女的不能上桌。我婆婆屬於老一輩的,可以跟客人一起坐。等男的吃完了,女人再上桌撿點兒剩。家裡做點兒好吃的,兩個小叔子回家,大嘴一扒拉做多少吃多少,等我上桌什麼都沒有了,就剩點兒菜湯,饅頭蘸菜湯,菜湯泡點飯。
我懷孕了,你得想辦法叫我多吃點,對吧?人家根本不管,我跟我們家老付吵過好幾回。我說你太不像話了,太不知道心疼我了,我吃飯不是給我一個人吃,肚子裡還有孩子。你說你什麼都不給我留,生出來的孩子長得癟癟瞎瞎的怎麼整?
我父母拿我當掌上寶似的,到婆婆家拿我當根草似的,確實不能忍受。他舅舅比較開明,就說小韋一起來吃一點吧,別光顧著做了,就是允許我上桌了。我們家不是那種小炕桌,我們有地桌,有凳子,我說你們吃吧,我這邊做差不多再來吃。飯菜都弄好了,我也上了桌,擠著吃一口,我不管那些,該上桌就上桌。
赫哲族老輩人生孩子是不能在家生的,要去外面生,在外面搭個小草棚,生完孩子才能回家。我老婆婆的三個兒子都是這麼生的。我尋思怎麼這麼野蠻?本來女人生個孩子就一腳門裡一腳門外的,我回上海生孩子。後來沒等我回上海,我父親就去世了,不能回上海生了,最後是在家生的。坐月子的時候,我們家老付不會照顧,我婆婆伺候得挺好,一天幾頓飯做著。兩個孩子都是九十月份生的,那時候魚好釣,我婆婆做好飯伺候我吃完就說,我去釣魚去了,拿個小盆去釣魚了。一兩個小時就端著半盆子魚回來了,嘎牙子啊,鯽魚啊,給我熬一盆湯,全是野生的,沒什麼土腥味,我其實肉吃得不多,魚吃得多,下奶最好。
我老婆婆挺能耐,爬樹、游泳、打獵都會。她在赫哲族女人裡頭屬於漂亮的,比較聰明、開通的一個人。以前的老人跟現在的不能比,當婆婆的總端著個架子,但是她跟我還可以。我在東北呆了三十年,她有將近十五六年是跟我過的,跟小蘇過了七八年。
婚後生活了一段時間,基本上可以了。可以了也不行,那陣兒東北時興跳舞,我挺好動的,出去跳舞。八點半,不到九點,他上舞廳找我,說這麼晚了,回家吧。我就跟他回去了,路上我跟他說,我這次給你面子,明天你再這麼來叫我,第二天你就上民政局來找我,我能說到也能做到。我說沒有這麼管的,管得太狠了,我出去玩玩,也沒亂搭咕。亂搭咕你管可以,跳跳舞怎麼的?我還不到五十歲,就應該像老太婆似的守在家裡頭啊?我連上大學都沒去,沒離開你,你要這麼樣管我,我可受不了。從那以後,他就不管我了,我愛玩就玩吧。
你等著,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韋建華與付忠義夫婦合影
3
1993年兒子高中畢業,本來想叫他考大學,卻趕上郵局最後一批接班。我說,郵電局多熱啊,你不如接我的班呢。他想想也是,考大學也不外找個好單位,郵局不就是好單位麼,他就接了我的班,我也就退休了。這一步走錯了,應該叫他考大學,有文憑還是好的。
1997年,聽說上海有政策,知青退休後戶口可以遷回上海。郵局那時候也松,只要你提出來退休就給你辦。1997年6月給老付連同兒子一起辦了退休。9月,我和老付回到上海,11月戶口就辦了回去,一切都按照我想的,辦得挺利索。不過,兒子沒帶回來,那個時候他剛結婚。我說,你等著,我反正要把你弄回上海。
我本來沒想到退休以後還能回上海,在東北還蓋了一個房子,120平方米,花了6萬塊錢。
我們倆在赫哲族裡頭是老大,比我們小不少的都管我們叫大哥大嫂。我回東北,回同江,回勤得利,他們都搶著請我吃飯。我上八岔也好,街津口也好,到誰家都受歡迎,好比說今天沒打著魚,想辦法出去給我弄條魚回來。殺魚做魚丸子,拿魚油烙餅,拿熬好的猱頭油炸做窩窩頭,那個好難吃啊。
赫哲族比較純樸,我們倆結婚時,付忠喜花80多塊錢買一個紅燈牌收音機,那時候一個月工資才30多塊錢。我生兒子的時候,老三可高興了,說哎呀,我們老付家有根了,大嫂,這個月的工資都給你。兩個小叔子對我是沒什麼說的,大嫂長,大嫂短,對我都挺好。
我們家老付有個表弟,結婚比我們早,兩個孩子比我們的大。他說,嫂子你來。我去了他家,他用白麵、魚油給我烙了一張餅。那時候白麵很少,大都是大餷子、高粱米、小米。他那兩個孩子看著我吃,眼珠兒撲騰撲騰瞅著那個餅,我就咽不下去了,我就把那個餅分給他倆吃了。
赫哲族喜歡喝酒,老一輩沒有不喝的,一天一宿不落桌地喝,沒菜也喝,幹拉。打一斤酒,就個鹹菜疙瘩,弄兩棵蔥,兩瓣蒜,沾點大醬,就這麼喝。這是喝酒嘛?這不是作踐自己嗎?肝腎都損傷了。
按說上海人不喝白酒,我倒是喝白酒,我在家的時候,我父親一小就培養我像男孩子那樣,抽菸喝酒我都會。剛下鄉那會,過年過節他們打酒喝酒,我拿個缸子也去要酒了,他們說你還會喝酒?我說為什麼不會喝呢(笑)?他們跟我打賭,說你能喝多少?我說喝就喝,跟他們喝了。後來他們都知道我會喝酒。我們家付忠義不喝酒,他說我看那幫老的喝酒就沒個人樣,喝完就作妖,自己身價都掉了。
我老婆婆喝酒,我從來沒有限制過她。那時候打酒不像現在,哪個商店都有打的,我跟我老公不在郵局麼,哪個連隊都走,哪個連隊的酒好,我們上哪個連隊去打。那時,十四連燒的酒好,告訴他們送點兒酒過來。
我說喝酒就要吃點兒菜護肝保腎,對吧?酒精對肝損傷很大的,親戚朋友端我的飯碗,是瞧得起我,我招待他喝酒,拌個冷盤,再炒個菜,反正好的我沒有,春天搞點韭菜,炒兩個雞蛋;秋天弄兩個辣椒炒炒;冬天了,炒個土豆絲,白菜粉絲裡放點肉絲。不管喝好喝壞,待客之道嘛,怎麼也得給他們墊巴點。老的小的都願意上我們家來。
我們家肉從來不斷。我不像他們有肉的時候一燉燉一鍋,幹拉的肉。我沒有,我把肉切成一二兩一塊,炒菜了拿一小塊,切點肉絲就夠了,借個味兒嘛。我過日子始終是細水長流。付忠喜打獵打到野豬了,我們大傢伙都幫著往回抬,往回拉,弄回來大家再分著吃。打到魚,回來也給我們分點。小蘇做點好吃的就來叫我,我做點好吃的叫她,反正兩家人處得親。人家一說起來老付家,都挺羨慕,好像哥仨挺有本事的。你在上海看不到這些,這是一家人的親和力和凝聚力。
在勤得利的時候,小蘇他們生活比我們好一點,付忠喜上山打黃鼠狼和猱頭,一張差點的猱頭皮能賣到二十,打魚也能賣點兒錢,我們倆始終這點工資。我父親去世早,我有時候還得接濟一點給我母親。
剛回上海時,我們住在我老媽那兒,那種兩三家合租的公房,共用廚房和衛生間。我老媽有兩間房,我媽住一間17平方米的大屋,我住一個12平方米的小屋。妹妹都結婚搬出去了,我回去有地方住,也算很不錯了。
2000年3月,我花9萬在奉賢區買了一套86.55平方米的房子。我考慮到母親百年之後,這房子姐妹要爭,另外按當時的政策,一次性付款買80平方米的房子給解決藍印戶口,這樣就可以把兒子一家的戶口解決了。
哪有錢?1996年兒子結婚,1998年姑娘結婚,手裡沒有錢,全是借的,9萬元對我來說已是天文數字,我就敢借這筆錢買房。以前的房子?談戀愛時,婆婆江邊的房子拆了,一連給了間小草房,倆弟弟在連隊住宿舍。結婚後,我們住在郵局,靠著江邊。赫哲人離不開山水。有兩個房間,我們住大屋,婆婆住小屋。婆婆做飯給我們和兩個弟弟吃。二弟結婚時,我們已搬進銀行的空房子,有兩大間,他們跟我們住在一起。一年後,電廠分了房子,他們才搬走。
在老付家三兄弟中,我做事往往出乎他們意料。蓋房子時小蘇他們還議論,說就憑他們倆的工資,兩個孩子在外面讀書有錢蓋房子?她能蓋得起來嗎?結果我蓋起了,還給兒子娶了媳婦。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聽說我在上海買房,他們說這傢伙好厲害,人家又在上海買一套房子!現在上海那套房子值200來萬了,這在他們民族引起了轟動,不管勤得利的,還是同江的都說我有遠見。赫哲族對我比較信服。我的經濟頭腦可能遺傳了我爸爸。
4
1997年我回上海時,女兒已經二十七了。
女兒兩歲半時,我把她送回了上海。我在東北待30年,她基本上是在上海長大的,所以她跟我在心理上總像有點兒隔閡似的,不是十分親。
什麼原因把她送回去呢?這個就跟我老婆婆有一點關係了。我們結婚早,那邊又沒有幼兒園,沒人帶孩子,應該是老的幫忙帶吧,我老婆婆卻愛串門子,上她兄弟姊妹那兒去玩玩,一玩就十天半個月。她一走,這兩孩子我弄不過來呀。
我父親過世了,女兒回去後,我媽跟她好像有點相依為命似的,走哪兒帶哪兒,左右鄰居都說她是我媽的第六個女兒。我媽也給她撐腰,四個姨要管她,她就告訴外婆。外婆就說人家小孩爹媽不在跟前,由我管,不要你們管。她就很橫了,誰都敢頂,誰都敢吵。
孩子不在跟前,我在物質上能滿足就滿足她,她就覺得好像有人撐腰的,跟她幾個姨就明著幹仗了。我回去看家裡的杯子不多了,就買了2盒24個杯子,都叫她打了。幾個姨說你怎麼又打杯子了?她說你管得著嗎?那都是我媽媽買的。
小學四年級前,她都在上海讀的,寒暑假也不回來。長期跟我不在一起,心裡頭還是有陰影。上三年級的時候,我回上海無意中看到她寫的日記,說爹媽不要我了,把我自己扔在上海。開家長會,別的小孩都是爸爸媽媽去,我沒有爸爸媽媽替我開家長會,都是外婆去。上下學別的小孩有爸爸媽媽接,我沒有。她有點兒被拋棄的感覺。
我就跟她說,我原想把你帶在身邊,把你弟弟留在上海。你外婆生了五個姑娘,沒有男孩,讓她領著外孫子;你奶奶生三個兒子,沒姑娘,領著孫女。可是你精啊,知道上海條件比東北好,說啥不肯回去了。你弟弟比你小十四個月,哭著鬧著要跟我走。不是我們拋棄你,是你要留在上海的。
她說是這麼樣嗎?我說是的。
五年級她回到東北,沒有上海戶口,不讓考中學,升到初中後,1986年還是八幾年,黑龍江發大水,縣裡發了一個檔案,說有親的投親,沒親的靠友,我就拿著這張通知書,找到上海有關部門說,我們那邊學校都沒有了,發大水了,我的孩子只能回上海來。上海挺支援,二話不說都收了。兒子在上海讀到小學畢業,女兒初中畢業,沒有戶口升不了學,必須回來嘛,兩個孩子回到東北,女兒進了齊齊哈爾民中。
1986年高二學年結束時,政策下來了,知青子女可以有一個回上海,我就把她辦回去了。上海高中的教學程序比東北快,再說南方跟北方的教學質量也不一樣,她只考了個大專。填志願的時候,正好我妹妹在自來水廠,人總得喝水,自來水廠是不會倒閉的,她報了,畢業後就去了自來水公司,在控制室當排程。1997年廠裡培養後備幹部,她是少數民族,又是女的,就讓她去讀專升本,讀三年。
我們回去時,女兒還沒結婚,未來的女婿在攜程網站下邊的公司當土木工程師,透過校領導給我在通河高階中學找了個活兒,管理學生宿舍。那些學生也不太好管,結果最調皮搗蛋的學生都挺聽我的話,學校管不了的,我都給他們管好了。第一個月600元工資,第二個月就加到800元。
兩年後,那位校領導調到了吳淞中學,通河中學不要我了,我就回家了。他們找了一個宿管老師,根本壓不住那些孩子,學校又來找我,想叫我回去幹。我說我不幹,你們既然已經不要我,好馬不吃回頭草,我就沒去。
吳淞中學請我過去,也是管理學生宿舍。我去了,在吳淞中學幹了三年,月工資一千。
我們家老付?回到上海他沒做什麼,他就協助我,幫我看管學生,我一個人也幹不過來,對不對?我吃飯的時候他幫我四處看看,學校發一個人的工資,兩個人給他幹,不合算嘛。
學校給我一間房,中午管一頓飯。我有一頓飯,他沒有,一大葷,兩小葷,一個素菜,加一個湯,食堂阿姨也是臨時工,跟我關係搞得挺好,學生扔的鞋子、衣服我撿回來,誰能穿誰拿走;有時我開啟洗澡間的門,讓她們進去洗洗澡,打飯的時候總是手下留情,多打一點,別人給一小勺,給我可能是一大勺或兩大勺。我自己再做點,我和老付基本上以中午那頓飯為主,晚上買一些蔬菜,去學校飯堂打點湯。湯是不要錢的,早餐買兩個饅頭,很省很省的,一個月200塊錢生活費就夠了,那段時間我倆攢錢挺快的。
姑娘結婚時跟老婆婆住在一起,很小的兩間房子,沒有客廳。她買了一套跟她老婆婆一樣的房型。前年又買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她現在在一個企業當書記。過年給我拿點兒錢,拿點兒東西,感情交流不多,小時候不在身邊的緣故吧,這也是一件憾事。
到上海後,我就給我們家老付買重大疾病保險,體檢時發現他的腎一大一小,而且兩個比正常的小。我最小的妹妹是大夫,他們醫院讓做ECT。妹妹說:“大姐,做ECT要將近800塊錢,你捨得嗎?”那時候,我退休工資也就700多塊錢。我說,那也得做,不做咋整?這人沒了每月七八百不也就沒了嗎?做吧。結果出來了,腎功能不全,尿蛋白沒有,肌肝偏高,尿酸高。
醫生給開了一種藥,很貴,50來塊一盒,每月要吃四五盒,這就要200多塊吧,還要吃一些降壓藥,我都給他買。十五六年過去了,他的腎功能恢復正常了。他現在73歲了,頭髮白的少,老二付中喜基本全白了,老三60歲時就全白了,現在已經去世了。老三老婆也不知道珍惜,現在後悔了,什麼都晚了。
韋建華與付忠義夫婦合影
我們家老付在上海待不慣,說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老吵著要回去,後來我們買了新房,裝了空調,冬天不冷了,夏天不熱了。我還跟他說,“你要是在勤得利可能早就作古了。”
北大荒這30年怎麼看?這我倒沒想過。沒有上山下鄉也不可想象啊,怎麼想象?我現在當翻譯官,高高在上,住著高樓?這些好像很空洞,離我很遙遠。
現在的生活嘛,我感到也挺好的。我一喝酒就想起我爸,從小就培養我抽菸喝酒學外語。
北大荒?我們這些知青經常聚會呀。聚會就聊北大荒的事,在北大荒那些年收穫的確挺大。我們這批人吃的苦最多,遭的罪也最多,我現在腰椎間盤突出、腿疼,都跟那段生活有關係。
本文摘選自《大國糧倉: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實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來源:澎湃新聞 湃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