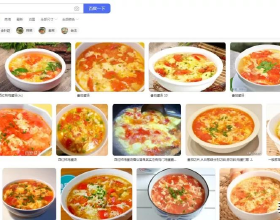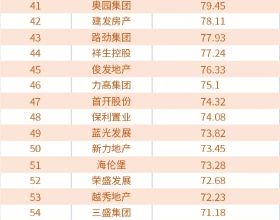對人機工效的忽視
今天的統計資料表明:坦克乘員如果長時間置身狹小、密閉的空間裡,受各種輻射、廢氣、電磁、熱能、噪聲、振動等影響,完成射擊的時間將增加35%,脫靶次數將會增加4%,如何改善坦克人機工程環境,提高人機功效已經成為現代坦克設計必須要考慮的頂層因素之一。
然而,在166工程啟動的那個年代,人-機工效問題還遠未成為一門值得專門討論的科學。再加上自T-34以來,蘇聯坦克設計界就形成了極為注重減少車體輪廓尺寸的傳統,這種傳統在T-54/55系列中型坦克上被貫徹的十分徹底,以今天的視角而言,其人機工程效能本身就糟糕的一塌糊塗。結果,當下塔吉爾的工程師們試圖以最為簡單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壓榨155工程潛力時,一個必然的苦果也就出現了——這是有史以來乘員工作環境最為惡劣的蘇聯坦克之一。事實上,U-5TS(2A20)115毫米滑膛炮炮身全長6090毫米、全炮重2382千克、身管長5740毫米、身管重1720千克、正常後坐長為340~410毫米、極限後坐長430毫米、高低射界為-4度30分~+17度。在如何這將門滑膛炮塞進原本為140工程設計的炮塔,並與稍作改進的155工程底盤進行合理匹配的問題上,可供列昂尼德·N·卡採耶夫能夠發揮的空間不多:140工程的炮塔比155工程的炮塔更為扁平,然而U-5TS(2A20)115毫米滑膛炮其起落部分尺寸又要大於被取代的D-10T 100毫米線膛炮,這意味著只能壓縮本就有限的乘員空間,導致全車的人機功效比155工程更為惡劣——駕駛艙總體設計空間不符合斯拉夫人體尺寸的需要,當閉窗駕駛時,平均身高1.75米左右的駕駛員其坐姿高與駕駛艙門結構在車內的高度不適應,駕駛員以正常姿態操縱坦克時,坦克帽頂與駕駛艙門間隙小於5毫米間隙,眼高也與潛望鏡高度不盡匹配,腿長度相對於操縱踏板位置偏大140毫米,迫使身材較為高大的駕駛員往往採取緊縮哈腰的非正常姿態操縱坦克;由於戰鬥室空間被進一步壓縮,車長和炮長只能一前一後坐在115毫米滑膛炮的左側,這種佈局實際上讓3名乘員坐在一條直線上(包括駕駛員),一旦坦克被穿甲彈命中左側,左側3名乘員都可能在劫難逃;火炮射擊後滯留在戰鬥室內的煙霧令人難以忍受,儘管火炮有抽菸裝置,可以用來吹除氣體,但戰鬥室內仍會很快充滿有毒氣體;炮塔內裝有自動拋殼裝置,由上架、下架和拋殼窗3部分組成,位於防危板活動部分上方,利用火炮的後坐能量將空彈殼從炮塔後部的小窗丟擲,但由於空間過於狹小,當坦克在顛簸不平的路面行駛或遭到非貫穿性打擊時,彈殼可能無法有效丟擲,空彈殼會撞到炮塔內壁並高速反彈到戰鬥室,對乘員造成傷害;同樣由於車內空間變得進一步狹小,為了不降低U-5TS(2A20)115毫米滑膛炮的備彈量,下塔吉爾的工程師們試圖創造性的在駕駛員身旁設定彈藥油箱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但這又使得發生彈藥殉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炮塔空間不足,U-5TS(2A20)115毫米滑膛炮發射後只有回到3度30分的仰角位置才能拋殼和裝彈……這些人機功效方面的問題,不但令乘員感到不適,過早地產生疲勞,減弱了戰鬥力,而且還暴露出了坦克設計本身存在的諸多不合理之處。
從經濟生活和軍事學說角度進行再解讀
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軍事學說特別強調戰爭初期的意義。“在未來的戰爭中,戰爭初期具有決定性意義”。據當時《軍事戰略》一書的估計,未來戰爭,在戰爭的頭半個月中,空軍的損失可達60~80%,陸軍的損失可達30~40%。武器的損失很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加5~7倍左右。因此,很難指望像過去那樣,在戰爭爆發後才大量組織新的軍事生產,而要在平時就要建立必需的儲備。第二,要準備相應的生產能力和動力以便在戰爭爆發後能夠迅速轉入戰時生產,某些特殊的軍事企業,應建立平時不動用的後備生產能力。第三,要注意保持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生命力,認為這是備戰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為此,必須分散配置,建立雙套生產,並採取對核武器的防護措施。最重要的工業目標要設在地下。第四,農業、交通運輸業等也都要做好適應核戰爭要求的準備。以上與準備核戰爭有關的各種措施,都意味著國民經濟在和平時期就要進行大量的備戰工作。這種備戰,同出現核武器以前的備戰相比,規模要大得多,技術要求也複雜得多。這種新要求,自然要使赫魯曉夫時期的經濟軍事化更為青睞於發展T-62這樣工藝簡單、適合大量生產,卻又在效能上有著較顯著提高,能夠滿足軍事鬥爭需求的常規武器——蘇聯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規律決定了這一點。
同時還需要看到的是,作為一種最終產量高達2萬輛的“過渡性應急”產品,T-62的出現從一個側面表明,即便是核武器的出現(併為蘇聯國家機器所迅速掌握),也並沒有改變“大縱深-諸兵種合同戰役法理論”在當時蘇聯軍事學說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縱深戰役法理論的廣延性與深度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大縱深戰役通常由一個方面軍或方面軍群實施,並得到大量空軍和海軍的支援。方面軍戰役已不是各集團軍戰役簡單的總和。集團軍戰役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獨立性,通常由集團軍在方面軍編成內與其他軍團協同實施。隨著戰爭的發展,方面軍戰役也逐漸喪失了獨立性,它通常由方面軍在方面軍群編成內與其他軍種的軍團協同實施。這樣就出現了全新的戰役樣式即方面軍群戰役——由最高統帥部直接指揮的戰略性戰役。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軍總共實施了50多次戰略性進攻戰役,說明大縱深戰役法理論已成為蘇軍戰略行動的基本樣式。大縱深戰役法理論,經過戰爭中蘇聯紅軍以鮮血為代價的不斷更新完善,至戰爭結束時已足以勝任作為一個國家武裝力量核心思想的任務。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起,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原子彈、氫彈和遠端火箭的裝備,人類戰爭全面進入了核時代。核時代的戰役理論同機器時代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但是,這種質變又不是一下子發生的。技術決定戰術,武器決定作戰理論,這是一條真理。但是,軍事技術對作戰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的影響不是直線性的。以戰役理論為例,由於它處於中間地位,上有戰略,下有戰術,它所接受的軍事技術的影響就可能來自三個途徑,其中,經過戰略和戰術來的影響是間接途徑,經過戰役兵器來的影響是直接途徑。這些影響是綜合起作用的,但不同時期總有一個途徑的影響為主,有時是間接影響為主,有時是直接影響和某一途徑的間接影響平分秋色。
事實上,在核武器裝備部隊初期,蘇聯軍方和軍事學術界只是普遍把它當作能“急劇增大軍隊火力威力”的手段。這是因為此時核彈的投擲手段是航空兵。由於受飛機航程的限制,加之投擲精度不高,核彈數量較少,熱核武器及遠端火箭的實用性尚且受到懷疑,所以核武器對戰役法理論的影響是有限的,其表現是蘇聯軍方竭力使核武器適應傳統的戰法。因此,戰後蘇聯陸軍的戰役法理論仍然徘徊在”大縱深-諸兵種合同戰役法理論”的道路上,連續的機動戰思想仍然佔據著蘇軍軍事理論的主導地位,大縱深連續突破和大規模的分割圍殲仍是達成戰役勝利的基本方法。更何況,恰恰是由於蘇聯軍方對如何利用核火力突擊效果進行縱深作戰的爭論與思索已經開始,這反而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裝甲機械化部隊在整個蘇聯軍事學說中的地位。在當時的蘇聯軍事學說中,認為核武器的應用是增加了大縱深坦克作戰的優勢,因為,突破敵人的防線不再需要周密的計劃,付出相當大的犧牲,一顆核彈就可解決問題。而且,坦克可以在核爆後幾分鐘就可向爆心發動衝擊——蘇聯在其第一次實用型原子彈試驗中,就迫切動用坦克部隊證實了這一點——這是其他武器所不具備的,對於進攻方極為有利。為此,蘇軍不但保留了戰時的6個大型坦克集團軍(改為機械化集團軍),在戰後相繼組建了另外4個機械化集團軍,使蘇軍這種方面的軍級別快速叢集數量增長到了10個,而且也註定了在極為成功的T-54/55系列投產10年後,作為這一系列中型坦克的重大升級版本,蘇聯軍方對T-62必然會保有“天然的興趣”。
結語
由於“珍寶島事件”的緣故,T-62成為了一個特別的歷史圖騰,在各種誇大其辭的演繹中,日漸走向神秘主義的虛無,以至失去了本來面目。但就其設計理念而言,真實的T-62卻是一個有些“尷尬”的存在——在戰後正式投入量產的蘇聯中型坦克(主戰坦克)中,它絕非是一個富有亮點的角色。“平庸”兩字是業界對其的普遍評價。不過作為一個承上啟下的設計,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T-62所扮演的角色又是恰如其分的,其整體設計思路有著非常清晰的邏輯性。也正因為如此,對其“平庸”的設計理念進行一番剖析和審視,仍舊有其思辨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