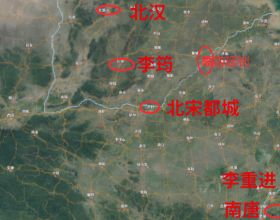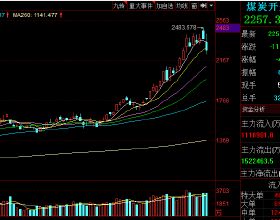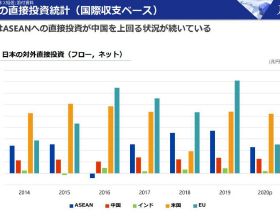“你今年‘紅美人’的銷售有沒有受影響?”我開門見山地問道。
“影響肯定是有的。”顧品說:“寧波的(新冠)疫情一爆發,我們這裡的快遞差不多減少了2/3,很多人不要了。疫情發生前每天是五六百箱地發出去,疫情發生後就只有一二百箱了。”
“你覺得主要是疫情的緣故嗎?”我求證道。這個因素洪增米也跟我強調過。
“一個是疫情,一個是經濟不景氣。”顧品補充道:“我有很多老客戶,以前每年都送很多‘紅美人’,今年就沒怎麼送。疫情造成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很多企業收入少了,人接觸也少了,送禮自然也少了。”
“你是什麼時候上市的?”我想到另一個原因。胡曉海(菜鳥公社)曾告訴我,今年由於天氣的原因,嘉興的“紅美人”降酸慢,一直到12月初才正式上市,比往年足足延後了一個月。
“我們還是11月17日上市的,象山柑橘文化節第一波發出去的量很大,後來量就減少了。”顧品說。
“口感不行,回購率不高?”我猜測道。
“對!”顧品實事求是地說:“主要還是去年凍害的原因,樹的營養供應不上,造成品質差異非常大。我也是後來才發現,同樣是老樹,沒受凍的樹品質不比往年差,但受凍的樹品質就很差。”
“你怎麼看以後的行情?他們都認為‘紅美人’的紅利期已經過了。”我指了指同行的萬邦斌,不僅是萬邦斌,先前走訪過的洪增米、鄭志國等一批最早種植“紅美人”的先驅者都持這個觀點。
“過是過了,但尾巴還是有的,還能玩幾年。”顧品笑著說:“今年好果到後期的價格又反彈回來了,行情最差的時候跌到10元/斤,後來又漲到16~18元/斤;差果每年都一樣的,價格很亂。”
說到差果,我忽然想起另一個問題:“這幾年‘紅美人’的外觀品質為什麼越來越差?”這個現象我最早是在2019年發現的,“紅美人”不美了,甚至想找個好看的果子拍張照片都很難,以至於春節前在洪增米那裡開啟精美的禮盒包裝時,心中的疑問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值這個錢嗎?
上午跟鄭志國也聊到這個問題,鄭志國的觀點和洪增米一樣,都認為是樹勢的原因,高接樹第一兩年結果都沒問題,後面幾年就每況愈下了。顧品依然把這個現象歸罪於去年的凍害:“凍害後第一批花沒掛住果,所以多是高把子、粗皮的晚花果,但好看的還是有的。”
我不由想起第一次描述“紅美人”的那一句:好的果實,就像秋風中的少女,柔弱,甜美,讓人心生愛憐……紅顏薄命,似乎也可以應驗到這個品種之中。
聊天間,幾位同行來訪,帶來了一盒種植在浙江金華的“甘平”。我嚐了一下,口感跟春節前四川眉山寄來的“甘平”類似,果肉肥厚多汁,有爆汁感,酸味不明顯,但糖度也低,風味明顯不足,與最初在顧品這裡嚐到的“甘平”有著雲泥之別。
“你今年的‘甘平’怎麼樣?”我問顧品。
這個品種也是他最早從日本帶回來的,2017年開始推廣,藉助“紅美人”的成功模式和“100元一個的橘子”的噱頭,在柑橘界掀起了一波追新熱潮。但好景不長,生產上的諸多問題尤其是高裂果率讓普通的種植者望而生畏,品種推廣止步於敢於嘗新的“先驅”們,只有顧品固執己見,認為有門檻的品種才是真正的好品種,並和韓東道等人合股興建了300多畝的基地,主栽“甘平”和“紅美人”。
“本來今年的產量很高了,去年1/3凍死了,後來補種了。”顧品長嘆了一口氣,言語間已經沒有往年那般堅定和自信,“今年也就10萬斤左右的產量,其中商品果只有50%。很奇怪,都是一兩瓣的枯水,我家裡的果就沒有這種現象,韓東道種在博覽園裡的果也沒有這種現象,可能是土壤有機質含量不夠造成的。”
與新基地小苗種植的方式不同,顧品家裡的“甘平”是大樹高接換種的,而象山柑橘博覽園裡的“甘平”雖然也是小苗種植,但因為面積小,韓東道在改土時放了大量的有機肥,並在地面鋪蓋了一層厚厚的有機物。這大概就是顧品分析得出土壤有機質含量不足的依據。
“賣什麼價格?”我詢問道。
“我自己賣出去的是298元/盒,將近50元/斤;給微商的價格是35元/斤,他們自己過來摘,我摘給他,他不放心。”顧品說。
“那效益比‘紅美人’好多了!”我笑了笑,也不知道心裡是讚賞還是嘲笑。
“如果全部賣到這個價的話,哪怕賣一半剩一半,產值也比‘紅美人’高。”顧品苦笑道:“像去年凍害後,我搶收了一批果子放在冷庫裡,最後基本上都扔掉了,沒用。水果要賣掉才算錢。”
“什麼原因?”我追問道。
“我這幾年經營下來,賣好果可以,賣差果不行。我的客戶只要好的,價格貴不是問題。”顧品順手拿起客人帶過來的“甘平”,“像這種果我就賣不掉,缺少這樣的客戶市場。”
在2020年的時候,我曾把“甘平”最後的希望寄託在四川眉山等晚熟柑橘適栽區,但當春節前品嚐到四川寄過來的“甘平”之後,我已經對這個被譽為“最甜最濃味的柑橘”徹底失去信心了。我問顧品:“後面有沒有看中什麼新品種?”
“我現在主推還是‘紅美人’和‘甘平’,接下去搞‘四大美人’,包括‘黃美人’‘愛媛50’‘愛媛46’和‘愛媛43’,做一個禮品組合。”說著,顧品話鋒一轉,補充道:“但這種方式我一個人少量搞搞還可以,大家都去弄也不行。”
“但是不可能你一個人弄啊!”我苦笑道。若不是跟風者如潮湧,象山“紅美人”何以淪落到今年這種窘境。
在顧品家最早的果園中,豎立著“中國第一棵‘紅美人’”的標誌。從2002年的嫁接時間算起,“紅美人”在中國已經經歷了20年的發展歷程。從3畝到300餘畝,從露地到設施,從家庭作坊到寬敞的包裝車間,顧品也從一個青春煥發的小夥子變成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伴隨著體重和體量的增長,還有已經無處張貼的榮譽牆。
“現在人比‘紅美人’紅。”我指著滿牆的榮譽證書調侃道。
“這些都是沒有用的。”顧品嘆息道:“不光是榮譽,‘紅美人’的錢我是掙到了,但都在地裡面。”
在來之前,我就有這份擔心。做農業就像炒股,開始小體量的時候順風順水,收益頗多,然後越做越大,等牛市轉到熊市,就套在裡面了。顧品收益最好的果園是和鄭志國等人合作經營的32畝“紅美人”,光2016年一年就創造了350萬元的產值。而後續投資的300多畝基地已陸續投入1000餘萬元,若不是非糧化政策政府收掉了150畝地,補償了200多萬元,他的資金壓力會更大。
“現在思路跟以前不一樣了,以前想把規模做大,現在覺得做精就可以了。像曉塘的農戶能做到90%以上的精品率,我做不到,精品率只能達到60%~70%。”顧品說。
“就你個人而言,多大規模合適?”我接著問道。
“也就50畝左右,最多不超過100畝。”顧品說:“搞大了肯定死路一條,除非套政府錢。”
“那不一定的。你套政府,政府也套你啊!”我提醒道:“政府專案一般都是投基礎設施,你還得保證建園之後能盈利。”
“基礎設施不投的話肯定能盈利的。”顧品似乎又恢復了先前那份信心:“如果政府把大棚都建好,我隨便種什麼,但不能全部種‘紅美人’‘甘平’這種難種的品種,全部種這些品種也是死路一條,要搭配一些容易管理的品種,比如‘黃美人’‘綠美人’‘象山青’……”
我笑了笑,未置可否,只是總結性地問了一句:“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怎麼評價‘紅美人’這個品種?”
“‘紅美人’確實是一個好品種。”顧品應道:“就我們象山而言,到目前為止,它仍然是最好的品種。所以只要把品質種好,我覺得‘紅美人’這兩年的銷售還是沒有問題的。”
2022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