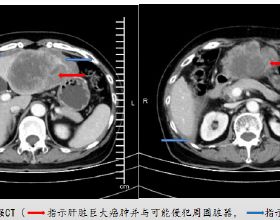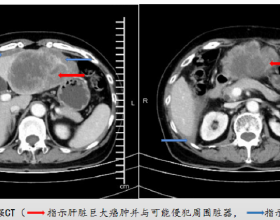往期連結:
《虞舜與九疑》第一章:三、大同夢想與聖賢崇拜(三)
第二章:舜帝南巡與南方文明(張京華)三、南方與文明
第三章 舜帝南巡與湘楚文化 一、“舜帝南巡”之歷史意義(一)
第三章 舜帝南巡與湘楚文化 一、“舜帝南巡”之歷史意義(二)
第三章 舜帝南巡與湘楚文化 一、“舜帝南巡”之歷史意義(三)
第三章 舜帝南巡與湘楚文化 二、舜歌《南風》之民本思想(三、四)
第三章 舜帝南巡與湘楚文化(陳仲庚)
三、湘楚文化之淵源流變
(一)火神祝融與楚文化之淵源
中華民族到春秋戰國之際基本實現了民族的大融合,文化則形成為南北兩大體系,北方以齊魯文化為代表,南方則以楚文化為代表。在其後的兩千多年曆史中,也基本上是這兩大文化體系的雙向並流和優勢互補。那麼,楚文化的特質是什麼?漢代王逸認為楚人“其俗信鬼而好祀”。這一評價一直影響著歷代的史書,如《漢書·地理志》認為楚之江南“信巫鬼,重淫祀”;《隋書·地理志》認為荊州之地“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通典·州郡典》載唐天寶年間事,說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荊州“風俗略同揚州”;《宋史·地理志》論風俗更為簡略,但對荊湖南路歸、峽之地的評價完全取自《漢書》:“信巫鬼,重淫祀”。元、明、清三代的《地理志》均不載風俗,但荊楚之地的巫風仍在盛行,人們對楚文化特質的看法也仍未改變。
楚人為什麼“信巫鬼,重淫祀”?這與楚人先祖祝融的世職大有關係。舜帝因為其家族“以音律省土風”的世職關係,因而對音樂和南風特別敏感,祝融家族因為“通天地”的世職關係,因而才特別“信巫鬼,重淫祀”。
先來看看祝融是誰。《山海經·海外南經》載:“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曰:“火神也。”《禮記·月令》亦云:“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張慮《月令解》雲:“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也。火性炎上,故曰炎融者,火之明盛也。神必有祝,遂稱祝融。”顯然,祝融是炎帝的助手,其職責是為祝禱“火之明盛”,所代表的是南方之“神”,屬南方文化體系。在《國語·楚語》中,火神祝融則落實到了具體的人:“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也。”郭璞注曰:“古者人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韋昭注亦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祝融司南屬火神,所以南正、火正均居南方並代指南方。學者們一般都認為,這重黎氏就是楚人的先祖,不管是合稱重黎或是分稱重、黎,都是祝融氏。這從楚人自己的認同中也可以得到證實,《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載,楚國的別封之君夔子不祀祝融和鬻熊,楚人認為大逆不道,於是舉兵攻滅夔國並俘其國君夔子。夔子卻辯解說:“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鬻熊是楚國的開國之君,祝融是楚人的遠祖,其地位還在鬻熊之上。夔子的辯解也恰好證明,只有在“失楚”即不承認自己是楚人的前提下,才可以不祀祝融和鬻熊,那麼,凡楚人就不能不祀,由此可見出祝融和鬻熊在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但是,重黎是“人”——火官,祝融是“神”——火神,“人”和“神”為什麼會有同樣的稱謂呢?《帝王世紀》解釋了其中的緣由:“祝誦氏,一曰祝和氏,是為祝融氏……以火施化,故後世火官因以為謂。”由此可知,火官的稱謂源於火神,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火施化”。火對於原始人類的生存來說本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而對於掌握他們命根子的火官,自然要尊為神聖的,故而火官和火神可以同一。
那麼,祝融“以火施化”的世職究竟是什麼呢?
首先,最初的職責是司“炊”。《說文》雲:“融,炊氣上出也,從鬲,蟲省聲。”作為義符的“鬲”是原始先民最重要的炊具,由此也可證明祝融的現實職責主要就是管炊事的官,一直到楚國的開國之君鬻熊,仍是管炊事的官。《國語·晉語》稱:“成王盟諸侯於歧陽,楚為荊蠻,置茆絕,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其實,倒不是因為鬻熊為“荊蠻”才沒資格“與盟”,而是因為鬻熊承先人之世職,司炊守燎乃為當然之責,故沒空與盟,鬻熊之“鬻”從鬲,亦可證明其司炊的職業。
其次,最主要的職責是司“祭”。虞翻《史記集解》雲:“祝,大;融,明也。”“祝”何以為“大”?《說文》雲:“祝,祭主讚詞者。”《唐韻》則雲:“贊主人饗神者。”祭主饗神為祝,神為大,祝自然也為大。“融”既可為“炊氣上出”,也可以為“明”,《左傳·昭公十八年》雲:“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有了“火”,才會有“炊氣上出”,同樣也就有了“明”。
當然,最為關鍵的是“祝”:“祭主饗神”,亦即“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也”。這裡需要分析一下顓頊“絕地天通”而命重、黎各司天地分屬神民的問題。《尚書·呂刑》提到了此事: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在《國語·楚語》中,觀射父對此事進行解釋說: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能齊肅衷正,其智慧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徵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位次。……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世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古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屬國家大事。這裡的要害問題就是祭祀權的爭奪:祭祀在當時乃是一種特權,如果家家都可祭祀,便不能顯示統治者的權威,因而從禮法上講是決不能容許民間濫祀現象的存在的。顓頊“興禮法”,命重黎氏斷絕民眾與天地鬼神的溝通,這是對濫用巫術的一種糾正措施,其目的是為了整肅“神治”,將祭祀的權力收歸中央,然後置官員統一祭祀。這就是“絕地天通”。
顓頊整肅“神治”,楚之先民重黎氏斷絕了百姓溝通天地的權力,而他們自己卻又獲得了“通地天”的特權,而且這一特權經堯、舜延至夏、商,至周宣王時“失其官守”,重黎氏一直在“世敘天地”。正因為“通天地”、“祭鬼神”是楚人先祖的特權和世職,所以才形成了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風俗。
再次,後來的職責還包括“觀火授時”。《國語·鄭語》記鄭國史伯之言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其功大在何處?史伯曰:“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亦即祝融具有雙重的任務:“昭顯天地之光明”。其一是管“地火”,主要是管“炊”;其二是管“天火”,主要是管“火星”與農事的關係。這裡的火星是指被稱為“大火”和“鶉火”的恆星。《左傳·襄公九年》雲:“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即火正的一項重要職責是觀象授時,也就是觀察“心星”(大火)或“咮星”(鶉火)在天空中出現的位置以確定農時,如果“心星”或“咮星”恰好在黃昏時從東方升起亦即“昏見”,便“出內火”——將儲存了一冬的火種引出來,點燃春耕燒荒的第一把火。作為火正的祝融,他所點燃的第一把火關涉到一年是否誤農時、是否有收成,這一把火也就具有了特別神聖的意義。這一把火點燃的時候,既要祭地神也要祭天神,以祈求一年的五穀豐登,這就將天地、人神的關係全都統一了起來。
無獨有偶,祝融氏家族“觀火授時”的這一職責,與有虞氏家族“聽風授時”的世職也是一種優勢互補的關係。作為天象恆星——“火星”出現的時間應該是“恆常”的,但作為地上氣候——“南風”初現的時間則具有“無常”性,因為“南風”不僅與太陽的直射有關,也與大氣環流有關,而大氣環流總是有變化的;春耕生產必須有南風的吹拂亦即氣候轉暖才能進行,所以“聽風”決不可少。這種“恆常”與“無常”的結合,也就是“不變”與“變”的結合,這種優勢互補的特點,對後世湘楚文化精神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楚文化在祝融火神精神照耀下形成了特有的內在特質。這種內在特質,並非體現在“信巫鬼,重淫祀”的風俗上,而是體現在“火”的特性上。那麼,火的特性是什麼呢?陳仲庚認為:“從火的自然本性來看,其外在特徵為柔為弱:體無固形而望風披靡,因對他物(燃料)的依賴性太強而極難保持自我的靜態存在,故而其生命力可以說是脆弱的;但是,“火性炎上”,無論火勢強弱,也不管遷移何處,寧可絕滅也不可改其“炎上”的本性,這種始終如一不可移易的內在本質,恰好又於柔中顯現出其特有的剛性。因此可以說,火的自然本性是剛柔相濟的,其形為柔,其性則為剛,或者說,它是以柔為用以剛為性的。火雖柔,但一切堅硬之物都可被它燒為灰燼或熔為流質,這是最為典型的以柔克剛。其次,火能包容一切,任何異質異體的東西經它的焚化和消熔,均可化為同質或同體的東西。其三,火是動態的,正是在動態中保持自我、在流動中發展自我,決不會自我封閉,更不願老死一隅。其四,火又有著頑強的韌性和充分的自信,不管處於何種劣勢,也不管面臨何種困境,均不可墮其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恰好是“火”的特性凝練了楚文化的精神核心,這種精神核心本就影響了同屬楚地的湖南,再加上屈原被流放到湖南,更加強化了這種精神的影響,從而使得湘楚文化在其發展演變的過程中,也就具有了鮮明的“火”的特性。
(二)屈原流放與“美人美政”之理想
楚文化本是“火性”文化,火的特性是剛柔相濟、以柔克剛。但到了老子的時代,已經轉向了“水性”崇拜:“上善若水”。《老子》一書又稱之為《道德經》,其實也就是對“水德”的闡釋及其利用問題。之所以會有這一轉換,大致是因為農耕文明的發展。楚人的原始農耕,與北方的“刀耕火種”有所不同,採用的是“火耕水耨”,其方法據裴駰《集解》引應劭的介紹為:“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隨著農耕文明的發展,水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人們對水也越來越重視,於是對“水德”也越來越崇尚。這反映在老子的哲學裡,就是對“柔弱”的強調,認為“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六章》)。因為水性為柔,而且是“潤下”,乘虛而入且無孔不入,其特性對莊子的啟示就是《養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技巧:“批隙導窾”,也就是避實就虛。這一技巧,在屈原和莊子的時代被很多人運用到了做人方面,而且形成為一種“時俗”,這就是屈原在《離騷》中所指斥的:“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規矩”和“繩墨”均為木匠之工具,其作用就是裁“曲”為“直”;而當時的楚人厭棄了“直”,所以背離“規矩”和“繩墨”去追求“曲”,而以“周容”(圓規)為標準。這似乎意味著,楚人在崇尚水性之“柔”的過程中一味地追求“曲”,最後導向了“圓滑”,並形成為一種時俗。這是屈原所深惡痛絕的。
“以柔克剛”本是水性和火性的共同特性,因而強調“柔”也是楚文化的一貫特性;但火與水畢竟還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火性炎上”而“水性潤下”。“炎上”與“潤下”的差別也就是“剛性”強弱的差別。在老莊哲學中,明顯地帶有“柔性”有餘而“剛性”不足的缺陷。老莊哲學在當時的盛行,可以說也正是時俗尚“柔”尚“曲”的結果;反過來,又推動時俗更加“尚柔”、“追曲”。屈原要與時俗相抗爭,既是為了挽救楚國當時的頹勢,更是為了拯救楚文化中原有的剛性,因為這種剛性關涉到楚國和楚文化的興亡成敗,所以屈原才如此堅定而沉迷,最後的以死抗爭,亦是為了喚醒楚人保持那點應有的剛性。
屈原的懷沙自沉,在當時似乎並未喚醒楚人應有的那點剛性。但他的遺體留在了湖南,湖南人在追慕、紀念屈原的同時,也將屈原所踐行的那份剛性繼承了下來,使之成為湘楚文化中精神核心的一份重要基因。
學術界普遍認為,屈原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開山之祖,其緣由就在於屈原對時俗的抗爭和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他的理想,也就是對堯舜的追慕:“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時俗“背繩墨以追曲”與先聖“遵道而得路”是這樣地相背相離,使得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屈原,專以抗斥時俗為已任。而就在這種抗斥的同時,詩人慕遠古之聖賢,上下求索“美人美政”以慰平生之理想,浪漫之本質也就寄寓其中了。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對遠古聖賢的追慕中,屈原尤其推崇舜帝,在他的詩作中多處單獨提到舜帝,而其他聖賢則無此殊榮。如“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離騷》), “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涉江》)。如此高遠美妙的理想之境,只有與重華亦即舜帝同遊時才會有,或者說,詩人只有藉助於舜帝之光輝,才能達到美妙的理想境界。這恐怕是屈原對舜帝情有獨鍾的主要緣由。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緣由,那就是屈原被流放到沅湘,這裡正是舜帝的陵墓所在,屈原來此正好可以與舜帝進行精神對話和精神交遊。
那麼,屈原所仰慕於舜帝的,究竟什麼呢?這似乎可以屈原自己的一句詩作概括:“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這裡的關鍵詞是“耿介”,考屈原之騷賦,“耿介”可以說是屈原所標舉的最高道德原則。然則“耿介”一詞該如何解釋?王逸注曰:“耿,光也;介,大也。”“耿介”即“光大”之意;對整句詩的意思,王逸釋為:“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王逸《楚辭章句》)今天的解釋則有點不一樣,如《辭海》的解釋為:“光大;正直”。《現代漢語詞典》則釋為:“正直,不同於流俗”。耿介的原意為“光大”,何以又引申出了“正直”之義?對此,今人姜亮夫先生有很好的解釋:“耿介者,光大之義,即《堯典》‘光明俊德’之說也。……言有明如天日之德,即儒家‘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謂”;“人之純德無逾於正大光明,而其非德無過於陰謀詭詐,三代以來惟楚人能堅持此德,漢承秦統,不發揚此義而以孝為治,獨承周家宗法之統,遂使吾民衰敝柔靡”<<。能正大光明者,自然堪稱正直。姜先生的闡釋還給我們指出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耿介”之德來自於《堯典》之“光明俊德”;二是惟楚人能堅持此德。
《堯典》中的“光明俊德”,也就是王逸所解釋的“循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天地之道”自然是正大光明的,因為有日月可鑑。“選賢任能”則更能切中屈原之心思。屈原被放逐,就因為楚懷王和頃襄王偏聽偏信讒言,不能選賢任能之故。比之於《堯典》,則堯舜之禪讓,確乎是中國選賢任能最為典型的史例,以後的歷史便不再有這樣的例子。也正因為不再有,堯舜才成為千古聖君,才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永不隕落的聖明完人。
當然,更讓屈原心醉神迷的,恐怕還是舜帝為斷絕讒言所採取的措施:“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堯典》)為防止讒說殄行蠱惑民眾,特設納言官,既傳達舜帝的命令,又轉告下面的意見,並要保證下傳上達的真實性,這確實是確保“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的有效途徑。同時,舜帝還要求大臣們對自己的缺點也要當面指出,不允許當面順從而背後又議論:“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尚書·益稷》)對於那些愛說讒言的人則要進行懲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尚書·益稷》)即是說,既要嚴厲懲罰那些庶頑讒說的人,又要給人以生路,讓人能改過自新。這種舉措,確實可以說是光明磊落,德被四海的,這也就是舜帝之“耿介”的精髓所在。而作為被讒言所害的屈原,越是感到時俗的幽昧可怕,就越會仰慕舜帝之光大可貴,從而也就更堅定了自己與時俗抗爭的決心、對舜帝之“美人美政”的不懈追求。
姜亮夫認為正大光明之德“惟楚人能堅持”,確切地說,則主要是屈原能堅持。如果所有的楚人都能堅持此德,也就不會有屈原的遭讒受逐了,屈原也就用不著以死來與時俗抗爭了。屈原的死,恰好說明楚人中少有人能堅持此德。屈原的抗爭應該說並沒有白費,他的死雖然對挽救楚國國運無補,但對沅湘一帶民眾的影響則是至為深遠的,這隻要看看湖湘人民至今仍然存在的對屈原的紀念和崇敬,便可知道屈原在湖湘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三)知行合一的湘楚文化精神核心
“湘楚文化”與“湖湘文化”基本上可視為同義語。這裡之所以用“湘楚”而不用“湖湘”一詞,乃是為了突出湖湘文化與楚文化的聯絡與區別。從聯絡方面說,湖南本屬楚地,又深受屈原影響,因而湖湘文化可是視為楚文化的分支或餘緒;從區別方面說,湖南人深受舜帝的影響,舜帝來自東夷,與齊魯文化有著天然的淵源關係,這也就意味著湘楚文化與齊魯文化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絡。因此,可以這樣說:真正能集南北文化之精華的就是湘楚文化,這種優勢是楚文化所缺少的。
那麼,湘楚文化的精神核心究竟是什麼?前文提到祝融氏家族“觀火授時”之“恆常”與有虞氏家族“聽風授時”之“無常”的結合,也就是“不變”與“變”的結合,影響到湘楚文化的精神核心,也就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信念與行動的結合——理想與信念是堅守不變的,現實與行動則要適時、適宜而變。體現在具體的思想和行動上,就是多數學者所認同的“知行合一”。筆者要補充的是:“知”是明德之“知”,“行”是用德之“行”;二者的合一,既體現了德治理念和德服天下的社會理想,也體現了道德修煉和道德教化的社會實踐。而對道德及其理想和信念的堅守並始終不渝地身體力行,乃是湘楚文化精神最為突出的特點。下面,我們可以選取幾位不同歷史時期的代表人物,看看他們身上所體現的湘楚文化精神特徵。
在屈原之後直至兩宋這漫長的一千多年時間內,似乎很難找到能夠體現湘楚文化特徵的代表人物。究其原因,恐怕是基於兩點:一是從秦漢到唐代,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轉移到西北長安,南方文化相對落後,沒有出現很有影響的文化人,唐朝末年,長沙人劉蛻中進士,時人稱為“破天荒”,可見當時湖南文化的落後程度和文化人的稀少;二是湖南沒有形成為一個完整的行政區劃,楚文化以楚國的行政區劃為依託,湘楚文化當然也要以湖南的行政區劃為依託,但這一段時間湖南被分割成不同的郡或州,直至唐代的廣德二年(764年),始設“湖南觀察使”,史書上才有“湖南”這個地名,宋代設荊湖北路、荊湖南路,當時即簡稱湖北、湖南,到此時才算是有一個比較確定的行政區域,湘楚文化或者說湖湘文化的意識也是從此時才開始建立起來。因此,湘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到宋代才重新出現。
宋代的代表人物是誰?《宋元學案》的作者之一全祖望說:“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為過於《正蒙》,卒開湖湘學統。”(《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五峰”就是胡宏,全祖望認為他是湖湘學派的開山之祖,這個評論無疑是公允的。胡宏的學生,也是南宋大理學家之一的張栻曾指出:“《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龜也”(張栻《知言序》)。張栻把胡宏的學說看作是道學之樞要,治理社會之根據,這個評論大體上符合實際。爾後出現的理學名人張栻、朱熹都從胡宏的著作中得到了教益,張栻更是繼承和發揚了胡宏的學說,形成了頗具影響的湖湘學派。
尤為重要的是,胡宏不僅開創了湖湘學派,還以自己的身體力行,詮釋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胡宏一生矢志於道,以振興道學為己任,他說:“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這種決心,足可與舜帝、屈原相媲美。
在知行合一的問題上,他特別強調“立志以定其本”:“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五峰集》卷3,《復齋記》)所謂“立志以定其本”,就是要求在認識事物之前,必須堅持一個認識事物的指導思想。在胡宏的認識論中,還提出了“循道而行”即按規律辦事的思想。他說:“失事有緩急,勢有輕重,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循道而行,則危可安,亂可治;悖道而行,則危遂傾,亂遂亡。”(《五峰集》卷2,《與吳元忠》)此處所講的“道”,主要是指規律而言,如果按規律辦事則安,違背規律則危。胡宏還指出:“道可述,不可作”。這是說:作為客觀規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可以認識它,但不可以製作它,這就肯定了事物之規律的客觀性。有了認識事物客觀規律之“知”,再採取遵循客觀規律之“行”,就能達到“危可安,亂可治”社會效果。
胡宏的一生不求名利,嚴格以道德自律,當時的權臣秦檜請他到朝廷做官,他不屑於與貪官汙吏為伍,去信嚴辭謝絕:“稽請數千年間,士大夫顛名於富貴,醉生而夢死者無世無之,何啻百億,雖當時足以快胸臆,耀妻子,曾不旋踵而身名俱滅。某志學以來,所不願也。至於傑然自立志氣,充塞乎天地,臨大事而不可奪,有道德足以替時,有事業足以撥亂,進退自得,風不能靡,波不能流,身雖死矣,而凜凜然長有生氣如在人間者,是真可謂大丈夫”(《五峰集》卷2,《與秦檜書》)。這就是他的人生宣言,他用自己的一生實踐了這一宣言。但是,他雖然不願做官,但對政治的熱情仍然絲毫不減,對社會理想的追求仍然孜孜不倦,在《上光堯皇帝書》中,詳盡地表達了自己的治國理想:“臣聞二帝三王,心周無窮,志利慮天下而己不與焉,故能求賢如不及,當是時,公卿大夫體君心,孜孜盡下,以進賢為先務。是時,上無乏才,而山林無遺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歡而無纖芥,形跡存乎其間”。其意也就是希望宋高宗能夠效法堯舜等二帝三王之為政要領:志利天下,選賢授能,以成就不朽之功業。宋高宗當然不可能成為再世之堯舜,胡宏的上言,只能看作是他自己對道德和理想的堅守與執著。
在宋代的代表人物中,更有一位土生土長的湖湘學人值得一提,這就是出生於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的周敦頤。清代學者黃百家曾這樣評價周敦頤:“孔孟而後,漢儒止有經傳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宋元學案·濂溪學案》)。周敦頤死後,宋徽宗賜諡號“元”,後世因而稱之為“元公”。黃百家對周敦頤在理論上的貢獻其評價是十分公允的,周敦頤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的確有“破暗”之功:使中國哲學從認識論層次上升到了本體論層次。從學術貢獻上講,他可與孔孟比肩;從道德修養上講,他同樣可與孔孟比肩。周敦頤自幼“信古好義,以名節砥礪”,一生淡泊名利,不求聞達,任職期間盡心竭力,深得民心,“政事精絕”,宦業“過人”,而又胸懷灑脫,有仙風道骨。他的人品和思想在當時就得到了廣泛的尊崇,因而死後不僅諡號為“元”,其靈位還從祀於孔廟,與孔孟並列為“三聖”,在孔孟之後的兩千多年曆史中,僅他一人能獲此殊榮。他死後千百年來,仍一直為人們所敬仰,清末民初的湖湘大才子王闓運更是語出驚人:“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話雖然說得狂了些,但也確實點出了周敦頤的影響以及湘學在宋代以後的地位。
明代的代表人物無疑是王夫之。王夫之生活於明末清初,雖然大半生是在清代度過的,但他從不承認自己是“清臣”。71歲時,清廷官員來拜訪這位大學者,想贈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雖在病中,但認為自己是明朝遺臣,拒不接見清廷官員,也不接受禮物,並寫了一副對聯,以表明自己的情操:“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清”指清廷,“明”指明朝,王夫之借這副對聯,堅守自己作為明朝遺臣的信念,而且不懼清廷“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嚴律,終生未剃髮,從思想到行為均保持了自己作為明朝遺臣的晚節。
王夫之同樣是以堯舜之世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從“循天下之公”出發,他猛烈抨擊“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歷代帝王把天下當作私產的做法。為了總結明王朝覆亡的教訓,尋找復興民族之路的政治動力,他繼承和發揚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優良傳統,以“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創新和求實精神,從哲學上和政治危害上全面清算了宋明理學唯心主義,以科學方法剖析了宋明理學的理論根源,並以其在批判中建立的“別開生面”的樸素唯物辯證法體系,為統治中國思想界數百年的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古典哲學做了總結和終結。對此,譚嗣同曾給予了高度評價:“萬物招蘇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論六藝絕句》),認為他是五百年來真正通天人之故者。
在知行關係問題上,他力圖全面清算“離行以為知”的認識路線,注意總結程朱學派與陸王學派長期爭鳴的思想成果,在理論上強調“行”在認識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得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重要結論。他以知源於行、力行而後有真知為根據,論證行是知的基礎和動力,行包括知,統率知。同時,他仍強調“知行相資以為用”。王夫之還進一步提出了“知之盡,則實踐之”的命題,認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人可以在改造自然、社會和自我的實踐中,發揮重大作用。這種富於進取精神的樸素實踐觀,是王夫之認識論的精華。
為了堅守自己的理想與信念,為了保持自己的氣節與情操,王夫之不避艱險、超越生死,他的高風亮節光耀千古,也是湘楚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
清代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曾國藩。有的評論者說:如果以人物斷代的話,曾國藩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最後一人,近代歷史上的第一人。這句話從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國藩的個人作用和影響。他一生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為“同治中興”之第一名臣;同時,他又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拓者。而這一切,都是以他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實踐為主導的。
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從一開始就以捍衛傳統道德相號召,他發表了《討粵匪檄》,檄文中特別強調:“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奇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接著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他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所以能動員當時廣大的知識分子參與到對太平軍的鬥爭中來,為日後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用人治軍方面,他注重“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處此亂世,愈窮愈好”,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他從培養將官的清正廉潔出發,來培養將士的“合氣”;正因為將士同心,他的湘軍才有了“扎硬寨,打死仗”的頑強作風。
在人格修煉方面,他嚴格按照“五字法”修煉自己:其一是誠,為人表裡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於世;其二是敬,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其三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於安寧放鬆的狀態;其四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其五是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則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地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謙對、仁恕、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可以說,這是他獲得成功的首要保證。天平天國傾亡之後,他的朋友、幕僚及手下將士幾乎全都勸他“問鼎”,他全都決然而然地回絕,很多人都認為他是“愚忠”,其實是一種誤解。他的信念就是做一個道德聖賢,他不願“問鼎”當皇帝,也就是對道德信念的堅守。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對曾國藩曾有過高度評價:“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現藏韶山紀念館的光緒年間版《曾國藩家書》中,數卷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之珍藏”。毛澤東認為:曾國藩建立的功業和文章思想都可以為後世所取法;曾國藩治軍最重視精神教育, 並以“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毛澤東建立紅軍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蔣介石對曾國藩更是頂禮膜拜,認為他的為人之道,“足為吾人之師資”;他創辦黃浦軍校,也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這不僅體現了曾國藩作為道德聖賢的個人魅力,也體現了他作為道德實踐者的實際功效。因此,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功業中,他不愧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
現在,我們不妨藉助陳獨秀的一段話,對湘楚文化的精神核心做一個總結。上個世紀20 年代,陳獨秀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讚揚說: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作證明的。二百幾十年前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黃興)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蔡鍔)帶著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毅不拔的軍人!
需要指出的是,“堅毅不拔”是行為表現,“奮鬥精神”也只是精神“外殼”,真正的精神“核心”乃是“明德”之“知”在引領著道德實踐之“行”;正是這種“知行合一”的精神核心鑄造了湖南人的靈魂,才使他們有了這種奮鬥精神和堅毅不拔的毅力,同時也使湖南人具備了勇於擔當、敢為人先的勇氣和決心。(作者:陳仲庚)
供稿:九疑山舜文化研究會
注:歡迎閱讀,如轉載請註明作者和出處。
編輯:尹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