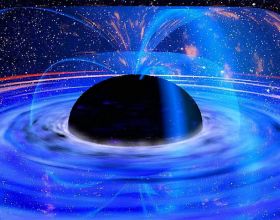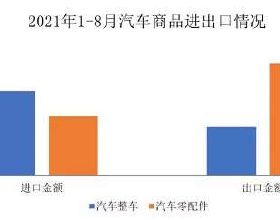金庸先生於1981年6月22日為《鹿鼎記》寫了一篇“後記”,其中說道:“這部小說在報上刊載時,不斷有讀者寫信來間:‘《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因為他們發覺,這與我過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實這當然完全是我自己寫的。很感謝讀者們對我的寵愛和縱容,當他們不喜歡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段落時,就斷定:“這是別人代寫的。”將好評保留給我自己,將不滿推給某一位心目中“代筆人”。《鹿鼎記》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與形式,要儘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造。
這部《鹿鼎記》的小說形式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創新。說它是“四不像”,那是指它非武、非俠、非史、非奇,又亦武、亦俠、亦史、亦奇。
“無武無俠”的武俠小說,乍聽起來只怕有人要斥為荒誕不經胡說八道。然而《鹿鼎記》中的主人公韋小寶卻恰恰如是,此人不會什麼武功,更談不上有多少俠義。而其他一干人物雖或有武,卻連康熙皇帝也是個“會家子”;抑或有俠,如天地會群雄,在書中只不過是一些相對次要的文學形象。
當然,書中的主人公韋小寶也不是完全不會武功,相反,他所接觸到的人中,就有許多超一流的高手:太監海大富、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獨臂神尼,這幾個人韋小寶都是正式拜了師的;而神龍教的洪安通教主及其夫人方荃也各教韋小寶“英雄三招”與“美人三招”;少林寺的方丈晦聰、長老澄觀大師等也都與韋小寶(時為少林寺弟子晦明)切磋過功夫。然而說來令人難以相信,韋小寶的武功,始終都只停留在“入門以前”的階段。學得最好的只不過是一套“神行百變”的輕功的三四層,神行是談不上的,百變抑或“百逃”倒是懂那麼一點。此人天性不喜武功,最拿手的功夫還是撒石灰鑽桌底、抱腿打滾及乘機抓人家下陰。說是無武也不為過,說是有武,那就只能說在似與不似之間了。
韋小寶其人的特點不但是不武,更主要的只怕還是非俠。他的政治觀點是非明又非清,既在宮廷中做他的忠心耿耿的小太監進而做大臣,卻又在以“反清復明”為目標的天地會中任他的逍遙自在的青木堂的韋香主。他的道德只能說是亦正亦邪,對皇帝講忠心卻也不免時時玩些花樣,而對天地會講義氣當然要看看情況並打打折扣。不說假話固然不行,而貪生怕死、溜鬚拍馬、見風使舵則更是他的拿手功夫,所以與俠是完全談不到一處,卻又似乎沾了那麼一點義氣的邊,而這些還都是從戲文中聽來的。
《鹿鼎記》寫的就是這麼一個人物的人生故事。所以說它無武無俠。若要更準確,就只能說是似武非武,似俠非俠,整個兒似是而非。
金庸自己在其“後記”中也有這麼一句話,即“然而《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毋寧說它是歷史小說”。作者的話,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金庸說這《鹿鼎記》“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這是可信的。而“毋寧說是歷史小說”就不見得是那麼回事了,至少,是不可全信。準確地說,這部小說也像歷史也像傳奇,似是歷史的傳奇而更是傳奇的歷史。若要說它是全然的歷史小說,這肯定是有些不妥的。小說中主人公匪夷所思的經歷與功業簡直是奇而又奇,令人聞所未聞,比如他與俄羅斯攝政女王索菲亞小姐之間的戀情及他主持簽訂了中俄第一個邊界條約—也是中外關係史上的第一個正式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云云,只怕是在史書縫中也找不到證據的。而如順治之出家當和尚,皇太后原來是毛文龍的女兒毛東珠假冒的以及康熙皇帝是一個會家子等,當然即使在野史中恐怕也找不到依據,而僅僅是武俠小說是作者虛構的傳奇。
但是,若說它是傳奇呢,則小說的第一章有關清初“文字獄”的內容卻又基本上是有史可查的。而至於康熙平定臺灣,平定吳三桂的叛亂,以及《中俄尼布楚條約》等亦都實實在在是那麼回事兒。康熙捕殺先皇順治的奉命大臣鰲拜,雖未必有韋小寶參與其間,但確為有據可依。更重要的,透過這些叫人匪夷所思的故事情節,我們往往會歎服歷史,確實是那麼回事。”而這歷史是否是實事或史實則已經不那麼重要了。如此,我們就只好折衷地說,這部《鹿鼎記》亦史亦奇,似史似奇,似非而是。不同於其武俠小說性質的似是而非。
有點武,有點俠,像是史,像是奇,是謂“四不像”,正是《鹿鼎記》的獨創,亦正是《鹿鼎記》的精妙之訣。
金庸筆下的大俠大致可分為三類 :儒俠,道俠 ,佛俠。所謂"儒俠",即是能夠為國為民犧牲自我,顧全民族大義,文武雙全且儒雅風流者。其中最典型的要數郭靖,他以一介平民之身,"鐵肩擔道義",死守襄陽十數載 ,最後以身殉國。從郭靖到楊過,出現了一種本質上的變化。如果說郭靖是正而不邪 ,楊過就是亦正亦邪。少年的楊過言語粗陋汙穢,行為放蕩不羈 ,形似無賴 。這一形象的出現標誌著金庸筆下的主人公從儒俠到道俠的轉變。儒家倡導 "仁 ",道 家倡導"智";儒家倡導為國為民 ,犧牲自我 ,道家倡導至性至情,實現自我,而這一點在楊過身上體現的尤為突出,與郭靖相比,楊過的形象顯得更真實,更有人味。到了《天龍八部》,金庸筆下的主人公開始成為佛家的代表。蕭峰一生都在尋找自己的仇人"帶頭大哥",卻沒想到找的竟是自己的父親,當最後真相大白,他剋制住嗔念,不再復仇;當他處在宋遼對峙的夾縫中,面對契丹、大宋百姓的災難 ,義字當先 、以死弭兵 ,實現了為人世的和平而甘願獻身的大慈悲 ,真乃佛家大俠也。
而金庸寫到《鹿鼎記》這裡 ,俠的概念開始趨於平凡 ,俠的光環也越來越黯淡 ,到了韋小寶身上則很難尋覓到一絲半點俠的影子。金庸筆下的主人公正慢慢從正義之俠發展成為"無俠"或者說 "反俠",而韋小寶正是一位成功且獨特,又不乏深刻的反俠典範。因為以前無論是儒俠、道俠或者是佛俠都只存在於人們的幻想之中,是人們理想的產物 ,而韋小寶則更具有現實性,他的一舉一動對於現實生活都是非常貼切的。這也是金庸在塑造了眾多的傳統意義上的俠之後,在現實生活中逐漸產生對俠的困惑與懷疑,有意與俠告別,讓傳統意義上的俠發展為無俠,去探討人性的本真問題。因為只有將俠打破了之後,人們才會迴歸於文化反思 ,進而去推動對於現實的改造。而這是歷史進步、文明發展的真正推動力,也可視為金庸塑造韋小寶這個形象的創作思想的一個深層挖掘。
後武俠時代,是現實衝破理想的時代,也是睡夢驚醒的時代。多麼美好的武俠世界,不過是過眼雲煙,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俠義的,但卻並不像武俠世界那樣的俠義。
就好像韋小寶,他的義,是利己主義的義,更是一種左右逢源,而尋求發展的義,他忠誠於多方勢力,同時又不忠誠於任何一方,因此,他可以去害歸辛樹一家,也可以去救茅十八。他敏銳的感受到風聲到底來自何處,然後提前像牆頭草一樣的導向哪方。
而這種左右逢源,在最終,還會變成一種站隊,這是現實最終擊潰武俠世界的訊號。當他最終在多方勢力相繼凋零,最終勝利者康熙皇帝浮出水面之後,韋小寶終於明白了,武俠世界不過是當權者的木偶,當戲演完了,謝幕了,最終的贏家不是任何一方,而是看戲的康熙皇帝。
其實,這種情況,才是真實的武俠世界,就好像荊軻為太子丹服務,展昭為包拯服務,盛英為康熙服務,李元芳為狄仁傑服務。真正的武俠,不是遊離於時代的獨立世界,終究只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從理想到現實,即使是快意恩仇的俠客,最終也難免被招安的命運,這種思想,不只是金庸一個人的思想,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思想。我們一直在罵宋江等人的招安,事實上,宋江走的路,才是一條最真實,最正確的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