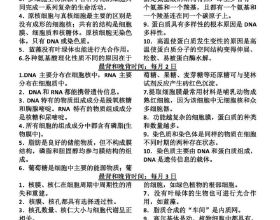清幽的風景背後,是另一個由詩文和傳說構成的奇觀。
宋人郭熙在《林泉高致》裡曾提出在山水畫中當遵循人能在其中“可行”“可望”“可居”“可遊”的畫理。畫者在山水畫的佈景中會考慮人的因素,而一旦踏入現實中的山水,這樣的思慮便會面臨有心和無力之間的彷徨——人們常常願意記錄自己的 “到此一遊”,但自然的無限乃至冷漠,總是顯出人的渺小。只是人們又總愛耽溺在這樣的彷徨之中——在征服的快感和茫然的無助之間,世人在天地間的位置漸漸明晰。
蘇州城郊的花山,並不廣為人知,但獨得清幽之色,因此倒顯出世人在山水間自處的一番典型姿態。山並不高,不過四百餘丈,卻玄機四布——本來,抵達終點並非向上的唯一動力,沿途的景緻才是決定此行意趣的機杼。入得山門,便見“華山鳥道”的摩崖石刻,一路往上,“隔凡”“洞天”“除塵崖”“宿墜”“雲屏”……歷代各色人等到此,總是樂於留下手跡。而為後世熟悉的康熙、乾隆,也多次遊覽,多次題詩。
這不僅是出於記錄此行的意念吧——卡爾維諾曾經談到,有旅人愛收藏自己在世界各地得來的沙子,而所有的收藏都是一部日記,“記錄自己轉瞬即逝的狂熱”,也“將自己的存在之流變成不易消散的客觀存在,將連續的意識之流凝結成書面文字的晶體”。而這些在山石上留下痕跡的前人,是將自己鑲嵌在了山水之間,他們瞬間的意識與山石同化,記錄的是他們與自然的對話。他們縱情於與自然的交流,並邀請後人的加入。於是,面對這些自然景緻以及前人遺蹟,後人會陷入“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的恍惚。並且,在那樣的山水之間、沉靜之地,這種陷落不可抵擋,足以誘惑人調動自我的潛能靠近前人所感知到的詩意、美感和慨嘆。這種靠近不只是還原,更是重建。因此,當見到“布袋石”、見到山石上“且坐坐”的字樣,會有自然的親近之感——人生實多負擔,背上的包袱不如就卸在此地,暫且一坐一歇吧。儘管這包袱裡裝的貨色一定古今有別,但無疑同源於人之根器。
再往上,有接引佛,有翠巖寺,有怡泉……諸景靜默以待。而山頂的蓮花峰,近觀其石上寬下窄,遠觀凌空,似傾非傾,就此巍然獨立了千百年。每及此類奇景,民間傳說便更添其異彩:“相傳觀音菩薩由南海普渡來花山修道,足踏千葉蓮花,留峰頂成蓮花峰。登蓮花頂,可許願祈福。”自然景緻,又被引向了世間的實用法則,許願祈福,最實在卻也最虛妄。登頂途中可見“御碑亭”——將康熙的詩二首和乾隆的詩一首刻於碑上,供於亭內。即便如此殊待,身處其時其境,會頓覺帝王與那些留下痕跡的先人並無二致——同樣有血有肉,面對的是如出一轍的景緻和現實。人跡與自然間所形成的對壘和悖論,在登頂遠眺的那一刻,泛出通達的靈光。
登頂後總不願原路返還,於是便可路遇“支公洞”,據傳東晉高僧支遁曾在此開闢道場,修煉成道。於是難奈好奇,偏要進到這狹促的山洞裡,留下的卻是這樣侷促陰冷的山洞如何棲身的疑惑。這當是支公身上傳奇色彩的一處支點。據說,花山曾是明末遺老的聚居之處,有著“就隱山”的別稱。這樣的傳統,在現在山下修建的“花山隱居”之所可覓遺蹤。只是,那是精緻可人的旅人居所,不復山野凜冽的粗獷。
旅行是為了逃避現在、體驗別處的生活吧,而因為有著預知可以歸來的底線,也就失卻了未知所蹤的驚險,這險中有喜有怖。但隱居,則需要一份與現世斷然隔絕的氣度和毅力,要接受山水的可親,也要意識到它的崇高和冷漠,像里爾克說的:人在不理解自然的時候,才開始理解它——“當人覺得,它是另外的、漠不相關的、也無意容納我們的時候,人才從自然中走出,寂寞地、從一個寂寞的世界”。所以,支公的隱居洞並不曾要融入這沁人心脾的山水之間,反而顯出艱澀、相隔的意味,這當是因他懷著敬畏之心參透了真正的自然之中遍佈著人力的不可控。這個渺小而寂寞的山洞,是人生的巨大隱喻。
歸來翻看資料,發現自白居易起便有著大量吟誦花山的詩文;黃公望等名家也曾以之入畫,而清代歸莊更是言明:“花山固吳中第一名山,蓋地僻於虎丘,石奇於天平,登眺之勝,不減鄧尉諸山。”想想,自己去往蘇州那麼多次,視線確實被天平、虎丘、靈巖所遮蔽了,若非友人相邀,居然不知此處勝景。而在景緻之外,耐人細品的還有這些前人留下的痕跡,不管是山間的石刻,還是尺幅之間的詩畫。帕斯捷爾納克說:“詩人的傳記,存在於讀他詩作的人接下來的日子裡。” 同樣,花山上的這些前人遺蹟,是他們人生經歷的別傳。後人每每與之邂逅、對視,都會催發出它們新的意蘊,延續它們的生命。它們猶如底片,等待時間的一次次沖洗,隨後,不同個體、不同時代的身形在其上慢慢顯影。
就這樣,在野趣和人文氣的渾然中,花山擁有了自己不同的景深——清幽的花山背後,是另一個由詩文和傳說構成的花山。它濃縮了時間,延續起“一時之性情,萬古之性情”的廣泛人性,更漸漸化成一面稜鏡,照見古今的歲月。(來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