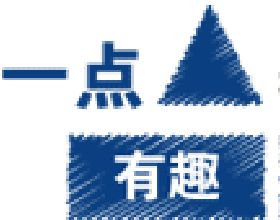今晚大家都在舉頭望月,中秋的月亮。
“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就像一首歌唱的,天上的月亮讓地上的人浮想聯翩起來,全世界看到的會是同一個月亮吧?
全世界都在欣賞同一個月亮的美,這點早已不容置疑。而且在世界各種語境裡,還都普遍地把月亮想象成一個女神。
在拉丁文裡,月亮一詞“luna”也就是月女神的名字:盧娜。盧娜和中國的月女神嫦娥一樣,也有個愛情故事:有一夜,盧娜駕著一對白駒拉的銀車巡天,看見俊美的牧羊少年在山坡上熟睡,不由春心蕩漾,情不自禁地給他深深一吻。她貪戀這個美少年的美,為了使少年的美永不凋謝,她便使他長眠不醒。每個夜晚,她駕車經過,都下凡來給少年一個夢中的吻。
這麼絕對霸道的愛,簡直是完完全全地佔有,雖然如此羅曼蒂克。
濟慈的長詩《恩底妳翁》寫的就是這個故事。只是詩人的心腸柔軟,他讓那個牧羊少年似睡非睡,與月亮女神夜夜纏綿。
不同於盧娜的天神血統,中國的嫦娥是從凡間升入月空的,與人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關聯。可是她既沒有探親的往返機票,也沒有攜手相伴“仙界”的男友,她追求自由,想掙脫人間的束縛(這一點,讓人嚴重懷疑她和后羿琴瑟不和),反而被卡住了,卡在一個叫“月宮”的地方,孤零零一個人,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等於是被判了無期徒刑。
所以李商隱的推理就很合理了:“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和李商隱一樣,蘇軾也設身處地,替嫦娥感受了“高處不勝寒”的寂寞。但嫦娥偉大在這裡,她雖然安慰不了自己的寂寞,她卻安慰了天下人的寂寞。不知她是被詩人昇華了,還是中國民間的普遍好意?反正這個寂寞女子,一下成了中國人思鄉和嚮往團聚的象徵。
以前望月亮,雖然阿波羅早登月了,人家早告訴我了月亮上沒有桂花樹,但人家是美國人,到底隔了一層。我還是一到中秋,就會含情脈脈地、優雅地望著那個月亮,因為李白這樣望著,杜甫這樣望著,中國人歷來這麼看著。如果不帶著這種情感,天上這輪月明月還是明月嗎?
現在,不大望了。一是近視,讀書讀的;二是霧霾,清朗的夜空少有;三是地下的燈火太亮太擠了,月亮是那麼侷促地,掛在樹的一角,樓的一邊。
當“嫦娥”化身為探測器,為我們一次又一次,實實在在地傳回月亮的寫真時,我突然如釋重負:哦!終於可以理性地望著月亮了,再不用浮想聯翩,心潮起伏。
只是,某些夜晚,我會醒來,想起兒時,想起那棟老房子。一抬頭:哎!朗朗夜空,月亮就安在那。風好似村子裡的好夥伴,揪著綠樹的枝條,在月亮一旁盪漾,搖過來又搖過去,撩撥著我一顆蠢蠢欲動的心。果真,有人在窗外叫了:“出來哦——,好圓的月亮粑粑!”
來了來了,我趕緊丟下手中的碗,一溜煙地閃出門來。月亮真亮啊,亮得刺眼。
作者:甘草子,不小資,不文藝,不妖嬈,不風情,恬淡自守,性如草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