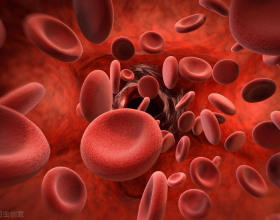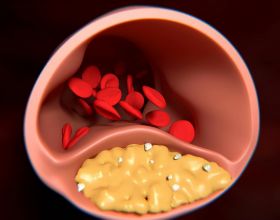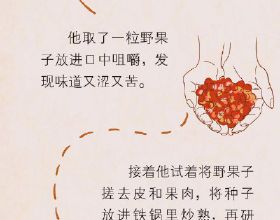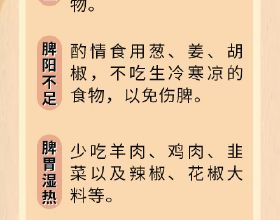□王瑞起
老奶奶快一百歲了,一個人住我的樓上。風燭殘年,她的一切美好都留在了記憶當中。她像深山裡久經狂風暴雨的一棵枯樹,已經枯槁,但憑依鑽進深土裡根鬚儲備的回喂和浸透青春汁液的糙厚樹皮的護衛,依然頑強地活著。
老奶奶平時足不出戶,所以我很少見到她,更沒有交流。據說她退休前是一個國營大廠的會計。她有一個孫女,是某三甲醫院的腫瘤科醫生。那個醫院距我們小區只有一站地遠,所以孫女經常來探望老奶奶。有一次我們在電梯裡相遇,孫女說,她的奶奶一生好強,死活不願意搬到他們家去一起住,怕給他們添麻煩,所以只好經常來看看老奶奶。這兩年奶奶越來越懷舊,想把她年輕時的一切美好都寫出來,出一本書。可是她眼睛近乎失明,又不會使用電腦,就用筆寫,孫女幫她打印出來。已經兩年多,差不多快截稿了。
去年夏天的一個傍晚,通明的陽光已被晚霞所代替。我從外面回來,剛走到單元門口,就看見老奶奶手提一個塑膠袋,站在門前。我打招呼說:老奶奶好啊!
老奶奶上前一步,拉著我的衣襟,顫顫巍巍地說:“王先生,聽說你以前是出版社的社長,能不能麻煩您幫我個忙啊?”
“什麼事?老奶奶,您只管說,別客氣。”
老奶奶開啟塑膠袋,從中拿出一沓A4紙列印的稿子,說:“王先生,我寫了一部書,您幫我找家出版社看看,能不能出版?”
我接過稿子,封面頁上的書名是“我的美好人生”。隨手翻了翻,大約有三百多頁,幾乎全是用日記和書信按時序連綴起來的,還有一些難以接續的殘篇斷章,大概是資料丟失的緣故吧。心想,這遠遠達不到出版的要求啊。但面對老奶奶那蓄滿渴望與求助的怯懦的眼神,我說出來的是:“奶奶,我先拿回去看看,一定幫您這個忙。不過您別太著急,一旦有了信兒我就第一時間告訴您。”奶奶臉上呆呆的,似乎沒聽見我說話,我便俯在奶奶的耳朵上,又大聲說了一遍。
老奶奶拉著我的手,頻頻點頭,千恩萬謝。我扶著老奶奶進了電梯,一直送她到十一層的家門口。老奶奶慢慢開啟房門,然後回頭向我彎下身來,鞠了一個躬。
回家後,我隨便翻開了一篇日記。老奶奶寫道:“那天因為我把一塊雞蛋皮掉進他的粥碗裡,劃了他的嗓子,他和我吵起來,一賭氣我回了孃家。這是我倆結婚二十一年來的唯一一次。第二天我就後悔了。他的襯衣要兩天換一次,我走了誰給他洗?他有胃病,不能吃涼東西,我走了,早晨誰給他熬小米粥?那豈不是要天天吃麵包喝開水湊合了嘛。他的中國胃不習慣啊!我多希望他來接我回去,給我個臺階下就行。可他就是個倔驢,怎麼也不肯來接我。我也死要面子,在孃家一住就是十八天。這件事都怨我,是我們愛情中唯一的一個汙點,讓我後悔一輩子,腸子都悔青了,想想我就流淚。今天我實在挺不住內心的懊悔,自己回家了。還好,他也給我道了歉。”
過了一個星期,我給老奶奶送去一份出版合同。我對她說:“出版社的編輯看了您的稿子,說您寫得很好,決定出版。正在送二審和三審。這是出版合同,請您籤個字。”奶奶突然睜大了眼睛,滿臉縱橫的皺紋也在這一瞬間綻開了。她顫抖著右手,戴上老花鏡,又拿起一柄放大鏡重疊上,一邊看著合同文字,一邊嗤嗤地笑出聲來。有一滴口水流下來,滴在合同上,她立馬從紙巾盒裡抽出一張紙巾,小心翼翼地擦乾淨。工工整整地簽上名字以後,她抬起頭,小女孩一樣看著我,問:“什麼時候能出書?”
我說:“三四個月吧。”
“好,好,我有盼頭了。”
那天以後,老奶奶僱了一個保姆。有好幾次我看見她由保姆攙扶著,在院子裡曬太陽。每次她都穿得整整齊齊,雪白稀疏的頭髮一絲不苟,瘦瘦的臉龐被曬得光亮而矍鑠。
老奶奶百歲生日後的一個月,我在樓道里遇見她的孫女,說是奶奶病倒了。我趕緊隨她上樓。
老奶奶臥在病榻上,臉色灰暗了許多,兩眼空洞恍惚。保姆正在擦拭奶奶嘴角的涎水。對於我的到來,奶奶沒有任何反應。孫女將我拉到床邊,伏在奶奶的耳邊,說:“奶奶,王叔叔來看您了。”
奶奶努力睜了一下眼睛,嘴角動了動,像是要說什麼,沒說出來。然後將枯枝一般的手伸出來,我把我的手遞給她。
奶奶又一次翕動嘴角,“書,書。”
我聽懂了,忙說:“您的書印好了,正在裝訂。明天我就給您拿樣本來。”
奶奶憑著意志維繫著她那遊絲般的殘生。我知道,那本書是她生命之燈的最後一滴油花。
第二天中午,我從文化書社打印出一本樣書。送到奶奶手上的時候,她的神志已經模糊不清了。那是一部很厚的書,書名和奶奶的名字都是凹字燙金的。她雖然看不清楚書的樣子,但可以用手摸。她的手放在書的封面上,久久不肯拿開,熱淚盈眶,很驕傲的樣子。嘴裡喃喃說道:“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兩個小時以後,奶奶安靜地走了,手還按在那本書上。
在安頓奶奶身體的時候,孫女拿起那本書,驚愕地發現書芯全都是白紙。
我趕緊請求原諒。
孫女怔了一會兒,微微一笑,說:“謝謝叔叔,您費盡心思滿足了奶奶最後的心願,讓她走得滿足、安然、舒心,是您圓滿了她的美好人生。”
【來源:瀋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