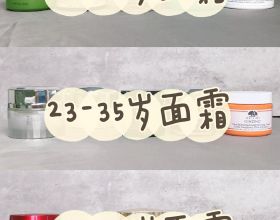【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康令】
1971年7月中旬,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做形勢報告,在談到第31屆世乒賽時,他問在場的莊則棟和乒乓球隊隊員:“這次美國乒乓球隊第一次來中國訪問,小莊,讓你和乒乓球隊的同志們去美國訪問,你們敢不敢去?”“我們敢去!”乒乓健兒齊聲回答。周恩來笑著說:“好嘛,應當是禮尚往來嘛!”
中方用“禮尚往來”的思維和手段來處理極為複雜的中美關係,“乒乓外交”是個經典例子,但並非孤例。新中國建立初期,在中美兩國敵對的情況下,曾經出現過美國駐丹麥武官主動走過來要和中方武官握手,但遭到當場拒絕,使得主人和美方非常尷尬。此事後來經外交部領導研究請示了總理後規定:今後我外交人員在公共場合不要這樣生硬。第一,我們不主動和美國人握手;第二,如果他們主動來握手,禮尚往來,我們不要拒絕。
莊則棟與美國兵乓球運動員科恩(資料圖)
50年後,中美選手將組隊出戰休斯敦世乒賽混雙比賽,延續“小球推動大球”的外交佳話。這也被解讀為是繼中美領導人影片會晤後,中美關係向好的一個標誌。
《禮記·曲禮上》有云:“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近年來,中國外交話語中頻頻出現的“禮尚往來”引發了國內外越來越多的關注。有些觀點認為,中國在國際關係往來中進行“禮尚往來”就是軟弱和退縮,這顯然是誤解了概念或是忽視了歷史。相反,我們恰恰看到了中國外交自信的一種迴歸乃至躍遷。不妨先看看這幾年外交部對中美關係的表態中,分別在什麼情境中提到“禮尚往來”,背後又體現了中國人怎樣的經典智慧、力量和氣度:
2017年,中美領導進行了友好互訪,外交部發言人在11月9日對美國領導人即將訪華的說明是:“今年4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海湖莊園時,特朗普總統夫婦對習近平主席夫婦予以熱情周到的接待,各方面都作了高規格的精心安排。中國是禮儀之邦,講究禮尚往來。中方高度重視特朗普總統本次對中國的國事訪問,我們當然要盡地主之誼,予以熱情周到的接待。”
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甚至對你更好,這種“以德報德”和“投桃報李”是“禮尚往來”當中的“示好”,可以翻譯成“return favors”。
2018年,特朗普簽署備忘錄,基於301調查報告指令有關部門對中國採取限制措施,美國魯莽和危險地對華挑起貿易戰。中方在3月23日對此明確表態並做出相應回擊:“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會奉陪到底。希望美方認真嚴肅對待中方立場,理性慎重決策,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既損人更害己。”
對於“畏威而不懷德”的情況,那就要使出“以直報怨”和“先禮後兵”,是“禮尚往來”當中的“示威”,可以翻譯成“reciprocate”。
2019年,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前夕的12月13日,路透社記者提問:“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方面今天發表的相對‘帶有進攻性’的講話?”外交部發言人並沒有掉入“話語圈套”,而是繼續從“以我為主”的角度進行闡發:“中國人是講究禮尚往來的,我們願意跟各國,包括美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但同時,對於損害我們主權安全利益的行為,我們必須要做出堅決有力的回應。”
“禮尚往來”並不是一味忍讓
將“示好”和“示威”合起來講,就是“禮尚往來”當中的“示範”,典型的辯證思維,也可以在更高層面上看出中國努力將中美關係引向平等互尊、包容互鑑、合作互信、良性互動、共贏互利的新境界。
近些年來,中國的“抗疫外交”“反制外交”“民心外交”還有“乒乓外交2.0”等外交新形式著實令世人眼前一亮,其實都蘊含了“禮尚往來”的理念、話語和實踐,我們可以進一步歸納為“過程式對弈”“領域間互惠”“文明型共生”等運用方式,顯示出的是“三位一體”的複合邏輯:利益上“示好”,力量上“示威”,理念上“示範”。
“禮尚往來”本身是個很有趣的詞。“禮”蘊含的是價值和規範,“往來”強調的是交流和互動,兩者結合起來便產生了積極的化學反應:“禮”的施行離不開“往來”的複雜過程,“往來”的持續則要將“禮”貫徹始終。
中國人從小到大都會接觸“禮尚往來”這個詞,以至於我們常常習慣從“送禮”或者“人情”這些極為日常瑣碎的視角來理解。於是,“他者”的觀察反而可以幫助我們切換視角。
例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中國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中國的立法者們主要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人民能夠平靜地過生活。他們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感到對他人負有許多義務;要每個公民在某個方面都依賴其他公民。”
根據彭林、陳來、楊向奎等學者的總結,禮之精神和要義之中的“禮尚往來”,其實主要包含這麼三層古典含義:一是主張來往雙方保持相互尊重,二是要求自我和他人之間交往平等,三是講求公平合理的施報平衡原則,最終指向的是普遍、持久、和諧的理想化人類秩序。中國傳統外交中的“禮尚往來”具體表現為“以敬為重”的理念和“禮和天下”的實踐。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一方面努力堅守“禮尚往來”的經典意涵,一方面創新發展了“禮尚往來”的外交意義。在“同等尊重”“平等互利”“對等鬥爭”這三種外交觀念及其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禮尚往來”的濃厚印跡。比如,1952年4月30日,周恩來在駐外使節會議上這樣闡述“禮尚往來”外交方針:
“‘禮尚往來’。資本主義國家,你對我好,我也對你好;你對我不好,我也對你不好。針鋒相對,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總是採取後發制人的辦法,你來一手我也來一手。不怕它先動手,實際上它一先動手就馬上陷於被動。開國後我們用‘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這兩手,在整個戰略上處於主動地位。至於在具體事情上,是可以後發制人的。”
從毛澤東1945年在黨的七大會議上講“禮尚往來”的鬥爭方針和自衛原則開始,黨和國家領導人將中國傳統文化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相融合,實現了認識論上的守正創新,用“禮尚往來”的認知豐富了“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鬥爭思想。要讓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在形勢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站穩腳跟”甚至“突出重圍”,我們外交的“禮尚往來”既體現原則堅定性又顯示策略靈活性,透過時間空間的適度轉圜來換取更多應對的餘地,從而在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實現“平衡”與“對等”:
一方面是在戰略層面“主動出擊”和樹立底線思維,充分表明新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是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之內,代表和堅持的是公平正義的大勢。同時強調中國保持獨立自主的堅定愛國立場,絕不會像曾經的北洋政府或國民黨政府那樣卑躬屈膝地賣國求榮、挾洋自重。
一方面是在戰術層面“以靜制動”和講究“轉守為攻”等鬥爭藝術,在較大程度上儲存自身實力的同時,要有長期打算和足夠耐心,集中力量孤立最頑固的敵人,給搖擺不定的國家留有一定觀察空間,使我們可以主動根據對手的態度和政策變化來進行具體的分析研判和做出妥善應對,最終目的是保證核心利益不受損失。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禮尚往來正規化”的整體發展脈絡愈發清晰,是以追求包容、開放和進步為主旨,體現在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等對外關係的許多方面,在繼承和發展中逐步實現了思維方式、表達形式、行為模式的有機結合,體現出以下三大特徵:
一是“重溝通”,就外交的形式而言,中國外交倡導的“禮尚往來”不是“一廂情願”也不是“一意孤行”,國家之間的良性互動應在彼此尊重、平等聯絡的基礎上,保持穩定交流、密切溝通,以實現互通有無、加強互信。透過運用好“關係”和“過程”等國際體系中的社會要素和鏈結樞紐可以孕育國際規範、培養國家情感、催生集體認同,並且積極促進國家的身份向好的方向轉化。
二是“保增量”,就外交的內容而言,中國外交倡導的“禮尚往來”不是“等價交換”或者“我贏你輸”,對鬥爭既要堅決出擊又要留有空間,對合作既有各取所需又有積極援助。這種互動形式並不是西方衝突秩序觀所指向的“自助”與“爭奪”,而是中國和諧秩序觀所指向的“互助”與“禮遇”。增加國際交往中的“餘地”就是增添世界進步和各國發展的資源,可以更好實現國家之間的互利共贏與全球治理的增量改進。
三是“促大同”,就外交的目標而言,中國外交倡導的“禮尚往來”不是“同而不和”也不是“拉幫結派”,國家和文明之間應堅持開放包容、更多地成人之美而非成人之惡,大國尤其帶頭應求同存異,並引領各國積極公正地捍衛人類共同利益、應對全球共有挑戰,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50年後,再度續寫“乒乓外交”。圖片來源:WTT世界乒聯
中國外交的“禮尚往來正規化”是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有效途徑,能給更好走出國家之間交往的新路提供示範意義。同時,作為中華經典國際關係概念的“禮尚往來”,既能與當今國際政治主流概念和實踐的普遍意義相對接,也基於中華文明特色實現了對西方相近概念的價值超越。在此試舉幾個西方國際關係與外交理論的相近概念進行比較:
1)“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
人們傳統行為模式中的“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也是經過複雜的計算機模擬而篩選出的最佳合作策略,雙方如果具備對於關係長期穩定性的預期,那麼採取積極正反饋式的合作就會進一步增加雙方的信任。
這基本與“禮尚往來”的邏輯一致,但“禮尚往來”還要突出自身主動做出利他的舉動,從而等待他者的回應。新中國建立初期就有“退避三舍”“友好當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承襲中國“敬人”傳統的外交品格,並且傳承至今,這就是典型的“示好”態度和“示範”舉措。
2)“人情交易”(quid pro quo)
福山在政治學分析中提到的“人情交易”(quid pro quo)概念,倒像一種遊走在法律和道德邊緣的精明政治手段,在美國政治中往往被包裝成禮物授受的人情往來,因為可以避開“禁止市場交易”的懲罰而成為美國遊說業的核心,近年來頻頻出現在美國與烏克蘭的幕後交易等國際事件中。顯然,這種虛假偽善的做法與彰顯道義和擔當的“禮尚往來”的本意格格不入,是很不值得提倡和推廣的。
3)“對等/互惠”(reciprocity)
國際法和國際貿易中的“對等/互惠”(reciprocity)本質上是規定國家之間權利義務要互相對應,以及適當對現有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改進。儘管可以確認國家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互惠,但仍可能傷害一些實力較弱的國家,比如發達國家有動機和能力去設計和實施保護自己的有效制裁發展中國家的手段。中國認為的“禮尚往來”則不僅僅注重“形式對等”和“形式互惠”,也要盡力推動和實現“實質對等”和“實質互惠”,講求持續地互動與回報的良性迴圈,指向的正是各國一道實現長遠利益。
4)“交往”(communication)
全球史和文明史視角下的“交往”(communication)概念源於拉丁語中單詞“分享”(communis)。西方世界從殖民時代起就盛行的“文明優越論”如今只是略有淡化,而沒發生本質轉變,指出與其他文明的“多元交往”更多是為了加強西方文明的自我認同,以及強調全球化的實現是由於西方的主導。
相比之下,中華文明從古至今都保持著更為謙和內斂的姿態,具有“富而不驕,強而好禮”的文明觀,透過“禮尚往來”式的文明互鑑推動形成了“懷柔遠人”“協和萬邦”“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等寬廣的世界觀,這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依據。
“禮尚往來”作為“中華經典國際關係概念”,反映了中國人的戰略思維,在當代仍然具有鮮活生命力,對理解當代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具有重要指導價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有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缺失的國際關係概念。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