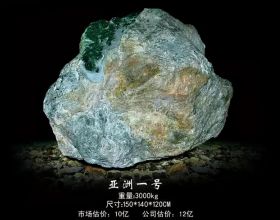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楊靖
1768年3月底,倫敦發生暴亂。美洲殖民地駐倫敦代表富蘭克林在致友人書信中描述道:“暴民們……在每條街上吼叫,來往馬車中的紳士淑女也呼喊‘威爾克斯與自由’……甚至城外十五英里之內每座房子的門窗上,差不多都畫上了No.45(第45 期《北不列顛人》[The North Briton])。”
這次暴亂的起因,是英國政壇“明星”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1725-1797)結束流放生活返回首都後,執意報名參加當年的議會選舉,結果卻“遭遇不公”——不僅勝利果實被他人掠走,他本人也因屢次“藐視法庭”而遭逮捕。4月,王座法庭(The King's Bench)判處他兩年監禁。5月10日,數萬群眾聚集要求釋放威爾克斯。政府下令開槍,造成震驚全國的“聖喬治廣場屠殺”事件。
這不是威爾克斯和法律的第一次“硬槓”。早在五年前,這位著名報人便因公開毀謗政府領導人位元伯爵(Earl of Bute)和權臣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而被送入倫敦塔。位元伯爵最初的身份是“帝師”,喬治三世登基後不久受命組閣。為了加強輿論宣傳,他聘請蘇格蘭同鄉、著名作家斯摩萊特(1721-1771)出任《不列顛人》(The Briton)主編。位元伯爵秉承國王喬治三世意旨,致力於重振王權,威爾克斯則固守輝格黨信念,希望國王像他的兩位先輩一樣垂拱而治,或“統(reign)而不治(rule)”。雙方立場迥異,論戰很快進入白熱化狀態。
在位元伯爵尚未來得及下達查封令之前,威爾克斯將新近重印的一部劇作《莫蒂默的垮臺》(The Fall of Mortimer,1731)題獻給首相大人——劇中主角羅傑·莫蒂默是昏君愛德華二世王后的情夫,一度執掌國柄,後被英明神武的愛德華三世當眾誅殺。位元伯爵與王太后的緋聞早已傳遍宮廷內外,威爾克斯此舉無異於火上澆油,令位元伯爵怒不可遏。然而苦於對方只是藉助歷史事件含沙射影,並未實名指證,從維護大局穩定出發,當權不久的首相選擇了隱忍。
但並非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肚量,比如海軍大臣桑威奇。年輕時代,威爾克斯及桑威奇同為臭名昭著的“地獄之火俱樂部”(Hellfire Club)成員,花天酒地、胡作非為,日後由於志趣不投而分道揚鑣。威爾克斯曾在報紙上點名批評桑威奇賣官鬻爵,言之鑿鑿,令後者顏面大損,發誓要報仇雪恥。威爾克斯聞訊毫不在意,緊接著又刊印詩集《女人論》(An Essay on Woman),對桑威奇的作風問題大加撻伐。詩集戲仿蒲柏名作《人論》(An Essay on Man)——其中一首蒲柏原文是:“醒醒吧,我的聖約翰!”威爾克斯將其篡改成:“醒醒吧,我的桑威奇!”臨到出版,威爾克斯覺得不過癮,又改成“醒醒吧,我的小范尼!”——範尼·默裡(Fanny Murray)是當時倫敦最有名的妓女,據說和桑威奇有染。作為報復,桑威奇先是暗中指使屬下與之決鬥,後來更是親自披掛上陣,聲稱“不將他(威爾克斯)送入牢獄決不罷休”。
威爾克斯自己送上門來。1763年《北不列顛人》第45期(暗指詹姆斯黨黨人1745年反叛)刊載威爾克斯針對國王近期演講的評論——國王在新議員任命儀式上發表講話本來也就是走個形式,照威爾克斯的看法,它堪稱是“英國政制中最空洞、最造作的發明”:國王照本宣科(講稿由大臣起草),新老議員鼓掌如儀。或許因為宣告“七年戰爭”結束的《巴黎和約》剛剛簽訂,國王意氣風發,忍不住自誇幾句(事實上國王一向謙遜持重,曾對面諛他的宮廷牧師說:“我到教堂是聆聽讚美上帝,而非讚美我自己”),不料招致猛烈批評。威爾克斯直言不諱地指出,“英國就和約條款同法國進行了既不體面又不正當的談判,而國王是當事人之一”,並宣稱國王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在執行君主權力(比如簽訂條約)時必須要對人民負責,甚至警告國王不得效法斯圖亞特王朝專制君主,與人民離心離德。在評論結尾,威爾克斯再度重申“自由是英國人民的特權”,而非王公大臣的專利。
在國王授意之下,桑威奇向議會上院控告威爾克斯“品行不端”“誹謗君主”“褻瀆上帝”,並高聲朗讀《女人論》部分露骨的“色情”描寫作為證據,結果上院以絕對多數透過決議,宣佈第45 期《北不列顛人》是“對國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無禮和侮辱咒罵,是對議會最嚴重的誣衊誹謗……並肆無忌憚地企圖離間人民對國王陛下的感情,煽動人民不服從王國法律,進行反對國王陛下政府的叛亂”。
在上院“定性”後,如何處置深孚人望的威爾克斯這一難題便轉交給下院。作為下院議員(早在1757年,威爾克斯便透過花費三千英鎊收買選民而成功當選),他在議會發表演講,宣稱“新聞自由是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與政治自由,人身財產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共同構成最基本的公民權。而在上述自由中,“新聞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堅強的堡壘……批評政府乃是每一位報人的神聖天職……而英國的自由將達到何種程度,這正是我要努力尋找的”。同時,他還提出申訴,強烈譴責上院“非法”搜查他的住所和印刷工廠(近五十名印刷從業人員受牽連,被無端羈押),因為根據英國法律傳統,“家庭就是一個人的城堡”(his house is his castle)。最後,他還重申其議員身份,要求享受司法豁免權。
下院對威爾克斯的遭遇抱持同情態度,因為他們對於國王試圖恢復君主專制的舉措憂心忡忡,擔心自“光榮革命”以來的英國君主立憲制會毀於一旦。透過表決,下院最初的裁決認定對威爾克斯的搜查和拘押屬於“非法”行為,應當立即予以糾正,當事人因此“獲賠一千英鎊作為補償”。這一結果令國王大為光火,好幾位議員被“請”進漢普頓(Hampton)宮,當面接受訓飭。隨後,國王又採取慣用的脅迫和收買方法對議會反對派進行分化瓦解,迫使下院違心作出與上院“一致”的裁決。威爾克斯被判罪名成立,其作品被責令公開銷燬。
精通律法的威爾克斯(曾在荷蘭萊頓大學研習法律)以民事訴訟(誹謗罪)不應由議會裁定為由再次提出抗辯,要求本案改由民事訴訟法庭(Court of Common Pleas)進行審理。開庭之前,威爾克斯面對法官和聲援的群眾發表演講:“我認為在所有的自由中,中下層人民的自由最需要保護;今天在我的案件中將得到最後的判決:馬上就要決定的是如此重要的一個問題——英國的自由到底是現實還是幻影。”法官阿什伯頓男爵(Baron Ashburton)同情威爾克斯的境遇,尤其反對政府憑藉“通用逮捕令”(general warrant)侵犯公民人身權益:“為獲取證據,憑無名的逮捕令就闖入他人居所,這比西班牙宗教法庭還要糟糕……這是對人民自由的公然殘害,破壞了《大憲章》(Magna Carta)第二十九條——而這一條針對的正是專制權力。”
很顯然,威爾克斯一案不僅是他(及其所代表的中下層民眾)和統治階級(王權)之間的鬥爭,也是英國統治階級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正如歷史學家蘭福德(Paul Langford)在《十八世紀英國》(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一書中所說,“十八世紀六十年代政治性質的改變將永遠與新國王喬治三世及其最不安分的臣民之一——約翰·威爾克斯——聯絡在一起”。照另一位歷史學家戈登·伍德的看法:威爾克斯審判案中體現出的英國式自由,既是“一種民族特性,也是一種精神狀態”,這與一個世紀前彌爾頓在《論出版自由》中表現出的精神氣質一脈相承。與威爾克斯同時代的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中也不無驕傲地宣稱,“黃金時代首先是自由時代”——這是英國人古老的政治信念。
最終,由於國王的強力干預,大法官決定對威爾克斯進行缺席審判(此前他已“畏罪”潛逃法國巴黎):各項罪名成立,判處入獄監禁,並剝奪其公民權(outlaw)。流亡巴黎期間,威爾克斯失去經濟來源,靠預支稿費度日,負債累累,情急之下,乃以年近半百的“高齡”重回萊頓註冊入學(根據當地法令,大學在校生不得因債務而被捕)。1768年,經過四年蟄伏,聽聞國內政局有所鬆動,威爾克斯即刻潛返倫敦,並迅速在英國政壇再次掀起狂飆突進式(Sturm und Drang)的一場風暴。
威爾克斯的競選令政府和國王大傷腦筋。這位異見分子(trouble-maker)在第一時間婉言謝絕了老友坦普爾勳爵的美意:後者建議他在自己掌控的口袋選區(pocket borough)參選,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重返議會。但很顯然,威爾克斯的目標是要搞出一個“大動作”——他中意的選區是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在英國政治傳統中,金融城面積不大,但地位獨特:經濟實力超群,擁有自成一體的司法系統,等同於“獨立王國”(內戰前夕,議會反對派首領約翰·皮姆藏身於此,查理一世親自帶人追捕,也未能如願)——據說在城區範圍內,即便國王駕臨,其御駕也要排列於金融城市長(Lord Mayor of London)之後。這一次選舉,儘管威爾克斯信心滿滿,但卻出人意料地以失敗告終。政府在選舉之前釋出公告,要求選民在選票上填寫本人姓名——金融城多富商大賈,害怕當局秋後算賬,只好轉投他人。
隨後,威爾克斯將目光轉向金融城所在的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郡。該郡面積狹小,但上繳的土地稅佔據英國的七分之一,足見其經濟地位之重要;與之相應的則是其政治地位:該郡在議會擁有八個席位(金融城有三個)。不僅如此,威爾克斯選中此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此地富商圖克(Horne Tooke)是他堅定的政治盟友,也是“權利法案支持者協會”的建立者。協會短時間內募集資金兩萬英鎊,不但幫助威爾克斯清償了債務,也為他的競選提供了有力保障。與此同時,為滿足候選人的“有產者”資質,坦普爾勳爵主動提出將自己名下價值六百英磅的土地轉讓給威爾克斯——如此一來,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1769年2月,眾望所歸的威爾克斯在米德爾塞克斯郡選舉中大獲全勝,“獲得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當局提出的候選人只得二百九十六票。倫敦人燃起篝火以示慶賀”。但這一選舉結果上報議會時卻被判定“無效”,因為這不是國王想要的結果。議會責令米德爾塞克斯郡3月重新組織選舉。這一次,由於其競選對手是一名壞脾氣的律師,且患有嚴重口吃(很可能是該郡的刻意安排),威爾克斯再度成功當選;議會害怕國王發怒,再一次宣佈本次選舉無效。4月大選之前,政府方面可謂做足了功課。首先,官方媒體大肆散佈謠言,威爾克斯“私生活糜爛”,與妻子分居多年(事實),幷包養多名情婦(部分事實)。其次,威爾克斯的對外聯絡受到干擾:他的居所被監視,書信被攔截,有時只能化裝出行。最後,正式投票前,他有權有勢的政治盟友統統被“勸退”,理由是,選舉應當“真實反映普通民眾的意願”。最為下作的是,眼看威爾克斯人氣高漲,官方居然下令提前關閉他的投票箱。
饒是如此,實力強勁的威爾克斯第三次取得碾壓性勝利。此時,國王的惱火升級為震怒:他痛斥議會顢頇無能,並下令不惜一切代價罷黜威爾克斯——“我的王冠幾乎決定於此”。惶恐的議會裁定威爾克斯候選人資質不符(之前被剝奪公民權),轉而宣佈其競選對手勒特雷爾(Henry Luttrell)“合法當選”——這位仁兄雖貴為王室姻親,但品行卑劣,連他的老父親都要公開“與之決鬥”。這一“逆轉”雖令國王稍感慰藉,但在議會內部卻激起強烈反彈。前首相老皮特(William Pitt)怒斥其為“砍向自由之樹根部的利斧”,伯克也譴責這一行徑“動搖了憲法”之根本,並且預言這必將引發嚴重的政治危機。
果不其然。王座法庭宣判後,數萬民眾湧上街頭。根據歷史學家的記載,“自1750年初大地震預報以來,倫敦街頭從未見過如此多人”。遊行隊伍一路橫衝直撞,沿街商鋪玻璃全被砸碎,勒雷特爾及其同黨受到驚嚇,數日不敢出門。入夜時分,街道燈火通明——據富蘭克林估算,在暴亂最嚴重的兩晚,倫敦燃燒蠟燭費用高達五萬英鎊。更為恐怖的是,在威爾克斯被押解王座監獄途中,暴民竟然打翻看守,劫下囚車。威爾克斯處驚不變,迅速擺脫其“拯救者”,逃入一家酒館,一番喬裝打扮後乘著暮色悄然抵達監獄——歷史著作一般是囚犯化裝潛逃出獄,像他這樣改頭換面自投羅網可謂絕無僅有。史載他在入獄之前有一句名言:“議會不守法度,我卻要做表率。”
或許是被他的大無畏精神所感動,王座監獄給予威爾克斯極為特殊的待遇:他獨享豪華單間,看書寫稿,接待訪客,一切與常人無異(他自稱是享受了友人伏爾泰在巴士底獄的禮遇)。前來探望的人絡繹不絕,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半是好奇半是仰慕。為表達愛意,她們大量贈送禮物,出手闊綽,且相互攀比,甚至不惜傾家蕩產——堪稱是古早的“追星族”,其中最有名的當數社交名媛昆斯伯裡公爵夫人(Duchess of Queensberry)。此外,美洲殖民地人民對這位“自由之友”可謂推崇備至——威爾克斯和伯克是議會最同情美國革命的兩位傑出代表——連美國革命元勳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也以一睹其風采為榮。在1769年一封信中,拉什寫道:“數日前,我有幸與身處王座法庭監獄的威爾克斯先生共同進餐,席間有一些來自美洲和英格蘭其他地方的紳士們作陪……他是一位美利堅自由事業的熱心人。”
1770年4月,威爾克斯出獄。之前在議會的“不良記錄”一筆勾銷,他終於如願以償,再度進入議會下院——名作家沃波爾(Horace Walpole)對此曾不無調侃地評價:威爾克斯被關押,英國人選他當議員;如果他被送上絞架,英國人可能選他當國王。事實上,時刻關注大選結果的國王確實感受到壓力山大:威爾克斯入獄後,他的支持者紛紛走上街頭,甚至打出“要威爾克斯,不要國王”的反動旗號(小冊子作者則模仿蒲柏英雄雙行體,譏諷“惡毒的法官和大臣聯手,限制威爾克斯和英國的自由”),與此同時,六萬民眾在陳情書上簽名,要求立刻釋放這位英國自由的“保護神”。馬克思日後曾指出,威爾克斯事件一度有動搖喬治三世王權之勢——其聲勢之浩大可想而知。
國王對這幫“不明真相的民眾”(ignorant multitude)受到矇蔽與挑唆而痛心不已,對“煽動群眾”的威爾克斯(約翰遜博士稱之為“當代的西塞羅”)更是恨之入骨。但國王也心知肚明,威爾克斯背後支持者的力量不容小覷(尤其在美國革命爆發以後,國王幾乎被視為這一場帝國“內戰”的罪魁禍首)。老牌反對派伯克曾當面駁斥國王:“問題不是你有沒有權力讓人民處境悲慘,而是你有沒有責任讓他們生活幸福。”曾任印度總督的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預言:“當他(國王喬治)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鳴得意之時,他應該記得,這頂王冠取之於一場(光榮)革命,但也會失之於一場(美國)革命。”擔任議員長達三十餘年的劇作家謝里丹在演講中力挺因言獲罪的威爾克斯,並宣稱:“腐敗的上院、專制的暴君、諂媚的宮廷……只要有一份不被查封的報紙,我就能將他們統統打敗。”在這位資深輝格黨政治家看來,威爾克斯事件的實質在於:人民有權選舉代表,不受任何脅迫(國王)和限制(政府)。茲事體大,關乎國運昌隆,因此來不得半點含糊。
威爾克斯當然也沒有辜負國王對他的殷殷“關切”。據說他重返下院後首個重要提案,便是倡議將每年1月30日的齋戒節改為狂歡節。這一天是查理一世斬首日,威爾克斯認為英國民眾當天不應該齋戒,而應該狂歡縱飲,以此慶祝暴君的滅亡和自由的勝利。此外,每當議會審批王室開支,威爾克斯必定仔細稽核每一筆款項,凡有疑處則力主裁減——其理由是納稅人的錢必須節約,否則有負人民重託。對於如此堂而皇之的政治“話術”,國王儘管氣惱,但也莫奈之何。更令國王惱恨的是,金融城的一幫烏合之眾(rabble)似乎故意與國王作對,居然在威爾克斯在押期間缺席選舉他為市政官,後改任司法官和財政官,並於1774年選舉他擔任金融城市長。在任十餘年間,威爾克斯厲行改革,主張以人道主義精神對待欠債人及其他罪犯,去除其腳鐐枷鎖,並著力改善監獄環境。同時,他嚴禁法庭參與當事人財產拍賣,規定法庭不得收取額外費用,違者嚴懲不貸(對罪犯家屬實施敲詐勒索的一名法官被判處死刑)。1771年,政府派人抓捕報道議會辯論的記者,威爾克斯利用金融城的司法特權加以阻攔。在議會下達通緝令後,威爾克斯認為這是對新聞自由的公然侵犯,拒不執行。他下令扣押議會來人,理由是:“你們表現出專制意識,人民就要表現出反抗精神。”
在他的晚年,威爾克斯的政治主張日趨保守。在1780年“戈登暴亂”(Gordon Riots)中,他負責守衛英格蘭銀行,居然下令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其中絕大部分是他當年的擁躉),此舉令他民望盡失。此後,儘管他在下院提出司法改革、宗教寬容以及重新劃分選區等議案,但與他之前聲稱的“中下層人民權益”關係不大,也沒有產生太大影響。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逐步走向血腥屠殺,令他益發心灰意冷。照歷史學家的看法,這位當年敢於透過報刊和選舉向王權和“舊制度”發起挑戰的勇士,此時已成為一座“熄滅的火山(extinct volcano)”。1790年,威爾克斯在米德爾塞克斯郡競選失利,黯然退出議會。他的一生,似乎也印證了羅伯特·弗羅斯特詩作《十磨坊》(“Ten Mills”,1936)中的名言:“年輕時我不敢過於激進,害怕年老時過於保守。”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