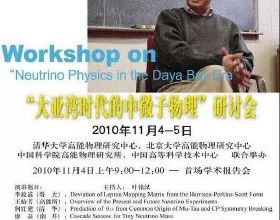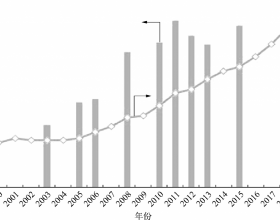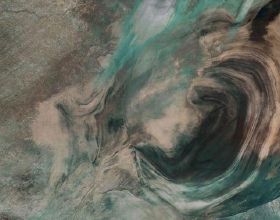1938年,在莊嚴的瑞典皇家科學院,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正式頒發,上臺領獎的是一位西方女性,但在場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中國人”,她寫的作品主角也是中國人。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公佈了對她的評語:“對中國農民生活進行了豐富與真實的史詩般描述,且在傳記方面有傑出作品。”
隨後瑞典國王親自將獎牌和證書頒授給她,隨後上臺發表獲獎演講,她說的每一句話都沒有離開過中國,面對日本在中華大地上的肆虐,她堅定的說道:“我對中國的敬仰勝似以往任何時候,因為我看見她空前團結,與威脅她自由的敵人進行鬥爭。由於有著這種為自由而奮鬥的決心,而這在一種極其深刻的意義上又是她的天性中的根本性質,因而我知道她是不可征服的。”
這位獲獎者名叫賽珍珠,她此時並不關心自己有沒有得獎,她期盼的是,全世界都能支援中國抗戰,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
賽珍珠之所以如此牽掛中國,還和她曾經的過往有關。
一、對徐志摩一往情深
賽珍珠的父親是一位美國傳教士,1892年父親前往中國傳教,四個月大的賽珍珠也隨著父親的工作來到中國,居住在江蘇鎮江,這一住,便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年。
1924年,中國學術界迎來一場聲勢浩大的迎接活動,亞洲首位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要訪問中國,陪同訪問的皆是文化名流,包括蔡元培、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等人。
其中徐志摩擔任泰戈爾出訪中國的翻譯,徐志摩作為新月派詩人,同時還是位出色的作家,在進行翻譯時妙語連珠,文采盎然,博得臺下陣陣掌聲。
其中擔任金陵大學外語系教師的賽珍珠就在臺下,賽珍珠從小受中華文化薰陶,接觸的第一門語言便是中文,在面對徐志摩精準且雅緻的翻譯時,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她從內心深處感受到了共鳴,甚至產生了崇拜,她意識到,他對臺上的這位文壇翹楚產生了莫名的情愫。
可此時的賽珍珠已經和一位美國農學家結婚七年了,兩人一起在金陵大學教書,賽珍珠生過孩子之後在32歲的年紀也逐漸發福,賽珍珠知道,自己的這份情應該埋在內心深處。
可能從古至今,國內國外,文理科的差異總是存在。文學系的賽珍珠和農學系的丈夫根本談不到一起,她內心的苦悶無法排解。終於她鼓起勇氣找到徐志摩,兩人促膝長談,從哲學聊到文學,又從文學聊到新聞報紙,從詩詞到歌賦,兩人仿若遇到了人生知己。
之後徐志摩陪同泰戈爾訪問日本,長久的歲月裡,賽珍珠再也埋藏不住自己的情感,給徐志摩寫信,她寫道:
“我的心掩藏在語言的背後,但從你眼裡頻頻擲來的刺激,使我痛苦不安。”
可信還沒寄出去,她便得知徐志摩已經準備和陸小曼成婚了,這訊息,猶如落入冰河。
婚後的徐志摩並不幸福,作為女人的賽珍珠很快就發現了徐志摩的情緒,她認為,此時徐志摩正是需要關愛的時候,她拾起自己的勇氣,給徐志摩寫下了:
“我不想憑此得到你的愛,只希望你能從中找到力量。狂亂如你,沉靜如我,其實大家都一樣,在痛苦的婚姻中,更加期待真愛的到來。”
徐志摩呢,他喜歡的向來是具有東方氣韻的女子,面對一位西方女子的示愛,他淡淡回道:
“我跌倒在生命的荊棘裡,只有康河的水能為我療傷。”
隨即便前往劍橋大學。
賽珍珠真的不敢奢望了,情之一字最為傷人,它不是尖刀,卻有著遠比尖刀的鋒利,而且直插人心。
賽珍珠也準備前往美國,兩人這一別,沒了再見之日,徐志摩飛機失事,人生也在青春謝幕。從此賽珍珠便把心中的徐志摩寫在書中,讓他永存。
二、走進諾獎殿堂
賽珍珠就屬於那種起點很低,可一旦起飛,便能一飛沖天的人。
論才華、學識,她無法與徐志摩相提並論,當徐志摩得知賽珍珠想要透過寫作來貼補家用時,他這樣鼓勵賽珍珠:
“不要為金錢去寫作,只有真正發自內心的熱愛,才能像泰戈爾那樣,做夏夜雨林中的鵑鳥,吐出無雙的情趣。”
那時的徐志摩或許還不知道,不,是永遠也不會知道,他曾經鼓勵的那位女士,會走上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臺,成為第一位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作家,也是美國第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賽珍珠的代表作是《大地》,也是她的創作巔峰,出版之後成為美國銷售量最大的書籍,緊接著賽珍珠又寫作了《兒子們》、《分家》,合稱《大地三部曲》,這一套書籍成功讓一家負債累累的出版公司一夜之間起死回生。
賽珍珠秉持文化相對主義,在她看來,文化並無高低優越之分,所以文化差異性是十分必要的,但各個文化群體應該在擁有文化差異的基礎上超越文化差異,在中國這叫“和而不同”。
三、“我一生只屬於中國”
賽珍珠原名珀爾·巴克,之所以給自己起這個名字,是因為她對中國的賽金花十分崇拜,賽金花會說德語,在八國聯軍侵華中和統帥瓦德西進行過交流,勸說瓦德西在北京莫要濫殺無辜,為保護北京市民做出了十足的努力。北京人民對賽金花十分感激,將其稱為“議和人臣賽二爺”。
賽珍珠也想成為賽金花這樣的人,能夠為生養自己的國家做貢獻,能夠在中間調理好中美之間的關係。
她是第一位將中國的四大名著《水滸傳》翻譯為英文的人,她翻譯的名稱為《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精巧度被徐志摩連連讚賞。
1934年賽珍珠離開中國,可她的心從未放下,新中國成立之後,她在中美夾縫中生存,內心無比痛苦,當時他對菲律賓外長這樣說美國:
“美國政府想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衡量和要求新中國的一舉一動,這樣就產生了矛盾,這些代表美國式的價值觀和標準均起源於西方文化、歷史背景,與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相距甚遠。”
作為一名深知中華文化的學者,同時作為一名美國人,她對美國的想法瞭如指掌,也知道問題所在。
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開始破冰,已經80歲的賽珍珠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開闢了專欄“重新看中國”,希望中美關係正常化,而且還積極準備訪華。
可回應她的是一封回絕信,信的結尾是:
我們無法答應您訪問中國的請求。
第二年,賽珍珠便與世長辭了,懷揣著她對中國鎮江的思念,對曾經那位讓自己魂牽夢繞的詩人的念想,她想如果當時那人沒出意外,現在他們會是怎樣呢?她也不知道。
遵照賽珍珠的遺願,她必須穿中國旗袍下葬,墓碑上要用篆書刻字。尼克松評價她:“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一位敏感而富於同情心的人。”
可在自傳中,她只寫下了:
“我一生到老,從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屬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