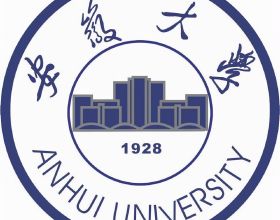老電影《小兵張嘎》中的張嘎子,是難以超越的經典形象。嘎子的扮演者名叫安吉斯,安吉斯的母親,是著名的剿匪英雄烏蘭。
烏蘭1922年出生在內蒙古卓索圖盟土黷特右旗(遼寧朝陽市)的嘎岔村,原名寶力格(意為泉水)。
九一八事變後,寶力格隨父母流落到北平,讀中學時,寶力格參加過“一二.九”愛國運動。盧溝橋事變後,年僅15歲的寶力格,成立了女子爆破隊,先後炸燬了多處日軍軍事設施,因此日軍還下達了對寶力格的通緝令。
為了躲避日軍的搜捕,寶力格離開北平,去了延安。
在延安,寶力格改名烏蘭(意為紅色)。
1946年1月16日,烏蘭被任命為哲盟騎兵武工隊的政委。負責訓練300多名剛入伍的新兵。
新兵們清晰地記得,在深邃碧藍的天空下,英俊瀟灑的女政委,頭戴紅色頭巾,腳蹬黑色長靴。身背一條馬槍,腰上還插了兩把駁殼槍,站在青色戰馬旁,突然揮動馬鞭,戰馬長嘶一聲向前奔去,烏蘭猛跑幾步,飛身上馬。動作乾淨利索。贏得新兵們一片喝彩聲。
疾馳的駿馬上,烏蘭摘下長槍,幾聲槍響,子彈都精確的命中靶標,新兵們看得目瞪口呆,甚至忘記了喝彩。
在烏蘭的訓練下,騎兵武工隊的軍事素質飛速提高。
幾個月後,武工隊改稱12支隊,屬熱遼軍分割槽直接指揮。
這一天,有人給烏蘭送來一封信,寫信人是當地著名的悍匪“打一面”。
“打一面”是土匪的報號,形容他槍法好,一個人可以獨當一面,有人見過他騎在飛奔的馬上,開槍打死百米外正在奔跑的狍子。
“打一面”心狠手辣,當地百姓提起他來都心有餘悸。
“打一面”的來信說:他打算帶領手下弟兄,參加烏蘭的騎兵支隊。
“打一面”的來信,讓烏蘭很為難,這股土匪的名聲太差,另外這些土匪還有抽大煙的毛病。
但如果拒絕“打一面”投誠,他很可能就去投靠國民黨軍。斟酌再三,最後烏蘭決定,接受“打一面”帶人投誠。
1946年3月,烏蘭和北票縣支隊政委王雲,帶領十幾名騎兵戰士,來到指定地點,接受“打一面”的投誠。
“打一面”說了幾句恭維話,然後請烏蘭為他100多名屬下講話。
23歲的烏蘭不卑不亢,朗聲對大家說:你們能棄惡從善,痛改前非,來參加我們的隊伍,我和我的戰友們表示歡迎……
這時一個叫陳海龍的土匪陰陽怪氣地說:“咱們一群大老爺們,讓個女人管著,不露兩手讓弟兄們看看,咱們心裡不服”。
烏蘭掏出駁殼槍,問陳海龍:“打什麼”。
陳海龍想難為一下烏蘭,指著空中飛過的雁群說:打下只鳥來,給弟兄們做下酒菜。
他話音未落,烏蘭左右開弓,兩聲槍響,兩隻大雁應聲落地。陳海龍嚇得再也不敢多說話了。
新投誠的戰士,紀律渙散,不服從指揮,另外他們都有抽大煙的毛病,烏蘭對這些戰士苦口婆心,跟他們講正規軍和土匪的區別,對他們噓寒問暖,那些生病的戰士,也能得到及時精心的治療。
很快,烏蘭就在戰士們中間樹立起很高的威望,大家都親切地稱呼她:“我們的烏蘭政委”。
然後烏蘭又跟大家說抽大煙的危害,並動員新戰士們戒掉抽大煙的習慣。
1946年5月12日,我熱遼軍區17旅主力部隊,對土匪盤踞的北票縣城發起猛烈進攻。
烏蘭的第十二騎兵支隊,因剛組建不久,所以執行外圍打援任務。
這也是第十二騎兵支隊第一次走上戰場,大家既興奮又緊張。
第二天拂曉,500多名騎匪,瘋狂地嚎叫著衝向12支隊的陣地。
本來戰士們以為,烏蘭會下達反衝鋒的命令,和敵人來一場騎兵對騎兵的對決。
沒想到烏蘭按兵不動,等敵人的騎兵靠近了,烏蘭下令開火,頓時槍聲大作,密集的彈雨中,敵人成片地被打死在陣地前,後面的敵人見勢不妙,丟下滿地的屍體倉皇撤退。
過了半個多小時,敵人又發起第二次攻擊,烏蘭還是以靜制動,將敵人打了回去。
緊接著敵人又發起第三、第四次攻擊,依舊沒能突破12支隊的陣地。
眼看敵人就要發起第五次攻擊,烏蘭卻命令戰士們離開陣地,準備好戰馬,隱蔽在一片樹林中。
敵人的騎兵衝過來,烏蘭一聲令下,以逸待勞的戰士們,揮舞著雪亮的戰刀殺入敵群。
經過連續幾次的攻擊,敵人已經是人困馬乏,面對呼嘯而至的我軍騎兵,匪徒們毫無還手之力。
在戰場上,戰士們又見證了女政委的神威,她手持雙槍,在戰場上縱馬馳騁,槍響處,敵人紛紛墜馬。
敵人的援兵潰敗,烏蘭率領騎兵部隊緊追不捨,最後土匪們撤到南山下一個叫宅舍的村子裡,負隅頑抗。
烏蘭派遣那些槍法比較好的老兵,單人獨騎在村子周圍遊弋,獵殺敢於露頭的敵人。其中“打一面”表現得最為出色,他換了三次戰馬,打死了至少20名匪徒。
到了第2天中午,敵人的彈藥將要告罄,天空飛來三架運輸機,把彈藥以及食品,空投在一片山窪中。
戰士們打算把這些空投物資搶過來,烏蘭卻不同意,她讓戰士們在山窪周圍埋伏下來。
果然,敵人組織了一百多騎兵衝出村子,打算將空投物資搶走。
敵人剛下馬,周圍就響起猛烈的槍聲,敵人100多騎兵,就這麼稀裡糊塗地被“包了餃子”。
戰士們抬著繳獲的戰利品,喜笑顏開,烏蘭卻意猶未盡地說:“其實還能打兩次伏擊,敵人再多送些槍支來就好了”。
戰鬥結束後,第一次參戰的12支隊大獲全勝。他們卓越的戰鬥力,得到上級的表彰。最得意的應該是“打一面”,他被直接任命為中隊長。
可“打一面”覺得官太小了,另外我軍紀律嚴明,這也讓做慣了土匪的“打一面”很不適應。他暗中給另一名匪首寫了一封信,準備拖槍叛變。
“打一面”將寫好的信交給一個親信,讓他把信送走,沒想到這名親信受了烏蘭的感化,早就沒有了重做土匪的心思,他甚至沒有猶豫,就把這封信交給了烏蘭。
第2天中午,通訊員騎馬來到“打一面”的駐地,對“打一面”說:今天下午五點半,烏蘭政委在指揮部請中隊長喝酒。
“打一面”不知道陰謀已經敗露,當天下午五點,他悠哉悠哉地騎著馬到了指揮部。
見到烏蘭,“打一面”問道:“這慶功酒是不是喝得有些晚了”。
烏蘭說:“喝酒先不急,這裡有封信,你先看看上面寫的啥,然後才有酒喝”。
然後烏蘭把“打一面”寫的信丟在地上。
“打一面”彎下腰去撿信,就聽烏蘭厲聲喝道:“捆起來”。幾名警衛戰士一擁而上,將“打一面”五花大綁起來。
經過審訊,“打一面”對自己所做的事追悔莫及,並說他這樣做,全是受了陳海龍的挑唆。
烏蘭帶人將陳海龍也抓了起來,這傢伙自知難逃一死,癱坐在院子裡邊哭邊說:“老子轉了半輩子,沒想到倒在你這個黑心女人手中”。
按規定,“打一面”和陳海龍都該被執行戰場紀律。
可烏蘭建議,“打一面”是難得的人才,抗戰時期,他在沙陀子消滅了日軍一個小隊。最近又立了大功,況且他這次陰謀叛變,也確實是受了別有用心的人的挑唆,所以應該給“打一面”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就這樣,“打一面”撿回一條命,調去了兄弟部隊,後來成為著名的戰鬥英雄。
但是除了烏蘭,很少有人知道,這位戰鬥英雄,就是當年惡名昭彰的“打一面”。
1946年7月中旬,烏蘭率領的12支隊,奉命到老哈河以北沙漠地區剿匪。
老哈河北岸,土匪盤踞的納什罕、照格吐、六家子,查干套海等地都處於沙漠腹地。當時屬敖漢旗管轄。
位於翁鰲沙漠中部的納爾村烏拉山,山上長滿了雜草灌木。沙漠中是一片片廣袤的窪地,比較有名的有柏樹窪、杏樹窪、樺樹窪。這些大窪面積都有幾十平方公里,中間長滿了沙柳、駱駝刺、雪裡窪等植物,在這樣的環境裡,土匪藏在這些地方,很難被人發現。
第12支隊進沙漠剿匪,正趕上一年中酷熱時節。頭頂炎炎烈日,腳下是陷腳的黃沙。有時幾十甚至上百里才能碰到水泡子,水面上浮著黃沫和蛆蟲,水又苦又澀,馬都不肯喝,更不要說是人了。
白天已經夠苦了,晚上也不得安寧,那些土匪都是當地人,熟悉地形,白天他們躲在陰涼處休息,到了晚上就跑出來,襲擊剿匪部隊。
等我們準備好去追擊時,他們騎著馬翻過沙梁,早就逃得無影無蹤了。
幾天過去了,沒有看到土匪的影子,卻把戰士們搞得疲憊不堪。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準備等天涼快了再進沙漠剿匪。
烏蘭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她堅定地認為,現在如此被動,主要原因還是當地百姓還沒有發動起來。當地百姓受土匪蠱惑太深,不瞭解我們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
從此戰士們每到一個村子,都會幫助村民們煮奶茶、撿牛糞、修理棚圈、整理院子,哪怕是村子裡的人都逃難去了,空無一人,戰士們還是嚴格執行紀律。
在一個叫高爾廟的村子裡,有個老人病重,烏蘭讓衛生員給老人治病,有人說這個老人的兒子是土匪。
烏蘭說:不要說他兒子是土匪,就算他是土匪,我們也不能見死不救。
衛生員治好了老人的病,老人第2天就騎馬到山裡,把他兒子以及另外十幾個同僚,帶回村裡,交給烏蘭處理。
烏蘭非常慷慨地把這些土匪都放了。這些被釋放的土匪,都成為烏蘭的義務宣傳員,12支隊仁義之師美名,在大漠中傳頌開來。
還有一位老人的牛病了,他把牛送到部隊,說要請烏蘭政委殺了吃肉。
烏蘭沒有殺牛吃肉,她找來隨軍的獸醫,把牛治好了,又給老人送了回去。
在烏蘭的努力下,當地百姓開始廣泛地向剿匪部隊靠攏,控訴土匪們的罪行。
這一日,剿匪部隊來到一個叫小回子地的村莊,這裡是當地有名悍匪“小德字”的家鄉。
當地群眾來報告說:“小德字”就躲在附近山溝的一個山洞裡。
當天晚上,烏蘭帶人乘著月色進了山溝,在當地人的指導下,戰士們發現了那個極為隱秘的洞口。
同時烏蘭還發現,土匪們的馬,沒有和土匪們在一起,山溝裡有一塊平整的草地,土匪們把馬都放養在草地上。
烏蘭首先派人把土匪們的戰馬都繳獲了,然後才勒令山洞裡的土匪繳槍投降。
可是山洞裡的土匪非常頑固,非但不投降,還一直向洞外發射子彈。
無奈之下,烏蘭釋出進攻命令,兩挺機槍形成的交叉火力,將洞口牢牢的封鎖住,幾名戰士趁機從兩側迂迴過去,把幾顆手榴彈丟進洞中。
幾聲悶響,山洞裡再也沒有了動靜。戰士們小心翼翼的進了山洞,才發現躲在山洞裡的20多名匪徒,都一命嗚呼了。其中就包括匪首“小德字”。
從此剿匪部隊連戰連捷,先後殲滅了“小德字”、“小白龍”、“韓老三”等股匪。
截止到1946年10月,大漠上的12股土匪,只剩下““七十六”、”吳老廣”和敖特根白音三夥土匪了。
1946年11月10日,國民黨軍第93軍第22師侵戰赤峰後,把“七十六”“吳老廣”和敖特根白音三夥土匪捏合在一起,讓敖特根白音做了國民黨軍的“熱北蒙旗保安司令”,吳老廣是副司令。
敖特根白音終於成為大漠中最大的土匪,他有些得意忘形,自稱是“大漠之王”。
這位“大漠之王”有點坐井觀天的意思,他活動的勢力範圍,只有東翁敖以及西拉木倫河沿岸的沙漠地帶。
敖特根白音手下的匪徒挺多,與剿匪部隊相比,無論是人數,還是武器裝備,都絲毫不落下風。
再加上他們熟悉當地的地形、風土人情,還有國民黨軍的空中支援,所以剿匪部隊一時半會兒,拿敖特根白音股匪沒什麼辦法。
很久沒有遭到打擊的敖特根白音,變得越來越狂妄。到了春節期間,他竟然給手下的土匪們放了假,每人發了20塊大洋回家過年去了。
敖特根白音也帶著300多人,回到位於翁敖沙漠中那什罕廟的老家。
烏蘭苦苦等待的,各個擊破的時機終於到了。
1947年1月21日,這天是大年三十,烏蘭集結部隊,於傍晚時分,奇襲六家子村。
敖特根白音最得力的爪牙根登,就在六家子村過年。
40多名土匪,根本沒料到剿匪部隊會在大年三十晚上發起攻擊,他們正湊在一起喝酒賭錢,突然發現我軍戰士神兵天降,黑洞洞的槍口,瞄準了他們的腦袋。
就這樣,剿匪部隊幾乎兵不血刃,捕獲匪首根登以下匪徒43人。
肅清根登股匪後,剿匪部隊馬不停蹄的奔襲照格圖,並於拂曉前抵達指定位置。
70多名匪徒宿醉未醒,就成了剿匪部隊的俘虜,其中包括敖特根白音手下,另一名得力爪牙曹德納木扎蘇。
狡兔三窟,六家子和照格圖,還有那什罕廟是敖特根白音的三個落腳點,根登和曹德納木扎蘇被剿匪部隊清除後,居住在那什罕廟的敖特根白音,就成了孤家寡人。他被圍攻時,不會有人來增援,即使他突出重圍,也是無處可逃。
剿匪部隊經過整整一夜的奔波,到達那什罕廟時,天已經亮了。
括敖特根白音居住的院子不是普通的蒙古包,而是土木結構的房子,牆壁非常厚實堅固,牆壁上還預留了射擊孔。
此刻括敖特根白音已經發現自己被包圍了,他躲在房子裡,開始向外射擊。
槍聲驚醒了其他土匪,頓時槍聲大作,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土匪,也爬起來向剿匪部隊開槍。
剿匪部隊穩紮穩打,把300多名土匪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到中午時分,只剩下括敖特根白音所在的院落還沒有被攻破。
烏蘭估計敖特根白音還在等待援兵,便把根登和曹德納木扎蘇送到前線,讓敖特根白音放棄幻想,繳槍投降。
敖特根白音果然沉不住氣了,他把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擋在身前做掩護,跨上一匹白馬衝出院門。
烏蘭眼疾手快,抬手一槍,敖特根白音滾鞍落馬,那匹白馬當場斃命。
敖特根白音又抓過那孩子,狼狽不堪的逃了回去。
下午1點多,土匪們的火力明顯減弱,烏蘭判斷,土匪們已經沒有子彈了,果斷下令,吹響衝鋒號。
戰士們衝進院子,一個叫任六的土匪,躲在水缸裡,向戰士們開了一槍,戰士們果斷還擊,將任六擊斃。
在炕沿下,有個傢伙把頭埋在雙臂間,渾身顫抖個不停。
戰士們把他拉起來,原來這傢伙就是“大漠之王”敖特根白音。
凱旋而歸的路上,騎在馬上被五花大綁的敖特根白音,終於遇到了一股援兵。
這些援兵是匪首吳老廣的人,不過他們是來給敖特根白音拜年的。
這些援兵腦筋有些不太靈光,沒頭沒腦的問烏蘭:“這是怎麼回事”。
烏蘭幽默的回答:“給你們拜年來啦”。
土匪們這才反應過來,轉身想跑,卻再也沒有機會了。戰士們又捎帶腳,把三十幾個拜年的土匪生擒活捉了。
烏蘭感覺這些拜年的土匪有用處,讓他們頭前帶路,奇襲吳老廣的匪巢黑水,經過激戰,匪首吳老廣被剿匪部隊生擒活捉。
駐紮在高爾蘇附近的“七十六”股匪,得知敖特根白音被剿匪部隊俘虜以後,嚇得夠嗆,竟然放棄高爾蘇,向阿拉格烏拉方向逃竄。
只不過他們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了,烏蘭派出一支騎兵部隊,在半路上攔截“七十六”股匪,將這股土匪徹底殲滅。
烏蘭大年夜殲滅“大漠之王”的訊息,在當地迅速傳播開來。
大家一起湧向剿匪部隊駐地,試圖一睹這個能文能武的女政委的風采。
但此刻的烏蘭又接到新的任務,趕赴阜新一帶,剿滅一股報號“老梁隊”的股匪,匪首梁省三。
“老梁隊”雖然是土匪武裝,但裝備精良,每個土匪都跨有一長兩短三支槍,常年藏匿在蓮花山上,做事陰損毒辣。
當地老百姓對“老梁隊”又恨又怕,已經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
為了徹底殲滅“老梁隊”,烏蘭親自率領偵察排,到蓮花山進行偵察。
發現“老梁隊”的匪巢倚山布寨,進可攻、退可守,而且還有四通八達的山路,能溜能跑的路線太多。
經過幾次偵察,烏蘭繪製出一張蓮花山的地形圖。由於蓮花山的地形太複雜,採用傳統的剿匪方式,很難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
為了確保全殲敵人,烏蘭派十幾名精明強幹的偵察員,打入敵人內部,裡應外合,最後將土匪們包圍在蓮花山的一條山谷中。
槍聲四起,土匪們無處可逃,屍體鋪滿了整條峽谷。從此猖獗一時的“老梁隊”,瓦解冰消了。
1947年12月,烏蘭所在的部隊,被改編為東北野戰軍第騎兵31團,團政委烏蘭。
遼瀋戰役中,烏蘭率領騎兵團衝鋒陷陣,立下赫赫戰功。
在慶功大會上,東北野戰軍政委羅榮桓,親自將一支衝鋒槍作為獎品,交到烏蘭手中。
輪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女英雄發言時,她不慌不忙的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沒等念出聲來,臉卻紅了。
後來有人把被烏蘭丟在地上的紙片撿起來,原來上面是一首詩:
春秋別君去,陣地度寒冬。
春來東風舞,帶來嗚雁聲。
這首詩字裡行間飽含相思之意,難怪拿錯了發言稿的烏蘭,會當眾臉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