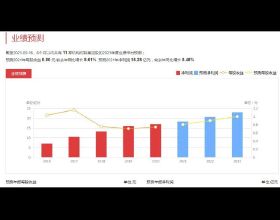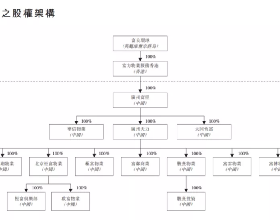我一直喜歡電影《柳堡的故事》。喜歡這部電影,是喜歡電影中出現的蘇北鄉間的風情,特別是兩個主角,一個村姑和一個年青英俊的軍人,騰騰的鄉土氣,躍躍的青春。這種好感一直延續到現在,成為我喜歡蘇北的一大原因。幾十年過去,至今我還是喜歡蘇北的風光,蘇北的吃,蘇北的人。每有假日,總想去蘇北,還去了兩次蘇北寶應,尋找拍攝電影時的外景場地,體驗電影中的蘇北風情。
電影叫《柳堡的故事》,外景場地真的是在一個叫柳堡的地方,在寶應治下。兩次去柳堡都是在十多年前,前次是春天,後次是秋天。
第一次去寶應,是開車從高郵沿著大運河237省道一直朝北,過了界首鎮,就一路問過去,終於看到通往柳堡的路標。柳堡在237省道東面,通往柳堡的道路是鄉道,當時還是石子路。已是四月天,沿路春柳拂風,白楊綻芽,兩旁河塘已有荷尖出水——柳堡原來地處藕鄉。
終於到了柳堡。這是一個小集鎮,和大多數蘇北小鎮一樣,一條新街,兩旁是各種小店。看此情景,我有點意外,更多的是失望。問鄉人,都說這裡是柳堡,沒有第二個柳堡。再問電影《柳堡的故事》,不是不知就是說不出所以然。講起“二妹子”,似乎還有印象。我們吃了一碗蘇北面,算是到此一遊。
過了兩三年,我又遊蘇北,又從高郵沿大運河走,又過了界首,看到去柳堡的路標,把車右轉,再找“柳堡的故事”。已是九月,路柳已成衰柳,只見裝滿白生生藕的車輛往外駛,時見路旁成堆的藕在過秤裝車——已是豐收的時季。
到了柳堡,一干部模樣的老人聽說我們要找電影的拍攝現場,一臉喜悅,說:“你們真有心。現場不在這裡,在鄉下,現在可以開車過去,那裡還有當年的場景。”
那是繼續向東的路,雖然已是村道,但仍很好走,兩旁盡是無際的稻田和大小的池河,稻已泛黃,柳仍成行,果然是“種滿柳樹的村堡”,一派水鄉風光。路過橋邊的油坊和抽水機房,走出一箇中年人,指著腳下的河道說,當年拍電影的人就是在這裡起岸的。這是一條通外的河道,想必當年電影攝製組人員一定是經大運河,從寶應或高郵縣城,經水路乘船到這裡的。
過了橋,又過一程,見村頭一家農舍敞著門,正在宰雞殺鴨。見不速之客,主人很是開心,說今天家有客來,正在準備中飯。“你們問的當年拍電影的地方就在那邊,看到有風車的地方就是。”他說著走出宅屋圍牆門,用手指方向。
我們下車,沿著田埂走去,到了橋頭,又沿著河岸,河的兩旁盡是黃燦燦的水稻,一架風車就在河岸,風中微動。風車是否舊物已不重要,看著風車,我眼前浮起的只是春風中的二妹子和十八歲的哥哥,電影中的許多印記都已褪去,只留蘇北的美好。
回到停車的地方,我們去那家人家道謝。這家人家和村落不相連,四五間平房,紅磚黑平瓦,外面打著圍牆,全屋籠在綠樹中。未進牆門只聞雞犬聲,進門只見地上雜花,架上滿是藤蔓,掛著絲瓜和扁豆。主人家已開桌,人滿桌。見我們,主人喜出望外,留我們一起吃飯。見我們推辭,女主人出屋,“嗤嗤”幾聲,從瓜藤上扯了五六隻絲瓜給我們。那是下部膨大、只只有二三斤重的秋絲瓜。我們不知所措:這麼大這麼老的絲瓜能不能吃?見我們遲疑,女主人連說“好吃奈,好吃奈”。我還以之前在柳堡集鎮買的一包滷菜和一包油氽花生米,大家作別。屋裡的客人都出牆門來,像是在送別親眷。
至今記得,那絲瓜遠比上海的絲瓜好吃,肉乳白而嫩,不知是蘇北地方種還是新品種。後來在上海也見到過類似形狀的絲瓜,買來吃過,只是那麼大那麼好吃的再也未見過。
最近,老友傳來有關電影演員廖有梁的影片。廖有梁在電影《柳堡的故事》裡扮演“十八歲的哥哥”,我一直以為他是北方人,沒想到他是上海嘉定人。廖姓在嘉定是大姓,不知他和中國高等師範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嘉定人廖世承是否同宗。看了影片,還想起了扮演二妹子的陶玉玲。作為老觀眾,除了常想到他們當年給我們的“美的享受”外,我還想再去一次柳堡,看看那架風車,再去看看那家善良的蘇北人家。
欄目主編:孔令君 文字編輯:孔令君 題圖來源:圖蟲 圖片編輯:徐佳敏
來源:作者:王孝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