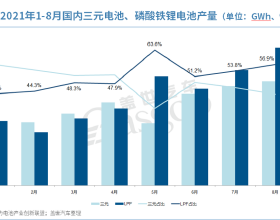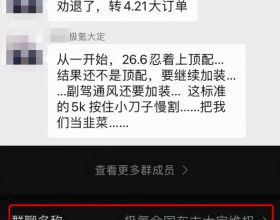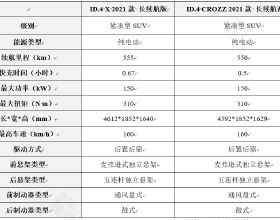虎年初九,以虎虎生威之勢,閒散於正定古城。過南城門,北行至陽和樓,在新磚老城之中感受著曾經的正定古城。
環陽和樓環道至西南角,一間靜雅的古民居躍入眼中,正門上方黑底金字的牌匾,上書四個大字“滋溪書院”。
進前院,到後院,入北廂房,一張長5米,寬1.5的書畫臺,散落著學生們的筆墨,陣陣墨香撥動著到訪者記憶深處的心絃,彷彿看到了自己孩提時代隨父筆墨的時光,眼神中點燃了一份慈祥。四塊梅花映雪絹布從屋頂垂下,將書院院長的茶臺與書畫操作檯分開。庭涇分明,將生活與雅趣孑然一室又難以割捨。
恰遇非遺拓片展示,進南廂房。。。。。。
“永和三年,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在起……”,一套12年蘭亭序拓片稿,將我拉到了曾經詩書禮樂的年代。輕撫漢磚,感受上邊斑駁的紋絡,歷經千年的傳承雖然沒有語言,但是一代代的的寄託,一朝朝的沉澱,透過你的掌心,慢慢的傳遞到大腦。拉近了歷史的年代,輕閉雙眼。歷史的厚重在你的內心慢慢的勾勒出一個雛形。漢磚上的每一個圖形,每個凸起和凹陷都刻畫在你的腦海,曾經的它們在大門邊,在牆上,在井邊,在牌坊。但是每一塊歷史的磚石都承載了一段或喜或悲,或平淡的故事。
以安徽宣紙覆蓋。輕噴水霧,讓紙面慢慢貼近磚體。再以經紗覆面,用麻刷輕輕錘擊。這是一個期盼空氣靜止的世界。不是手臂的力量,而是全身貫注把握心性的過程。你的呼吸。你的力量,你的眼睛的每次變化。都需要你在撫觸的時候在內心勾勒出的圖案的打磨。不驕、不躁、不徐、不急。大腦勾勒的圖案和拓片上宣紙的貼融必須一致。心到極致,彷彿給漢朝的美人穿衣,一定要那麼的貼切,一定要那麼的完美。漢磚上的宣紙,融合進磚體,變成了吹彈可破的面板。變成了自己可以看到的心性。
再用硃砂徽墨輕錘磚體宣紙,一幅美妙的印記凹凸著呈現於世,從畫匠到石匠、從石匠到拓片師,他們透過一次次的擊打和輕錘,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著不同年代不同的美。
我勸你要做一次拓片。因為我看到了我心臟的跳動,看到了我的呼吸。看到了我穿越到過去的那個年代,去感受漢朝子民的文化心性。
出院門,再回首牌匾“滋溪書院“,敬佩於元代正定大儒蘇天爵老先生以正定滋河寄託於書滿天下的壯志。中華五千年的文化,是以黃河長江為源頭的雋永文化,以水為魂,以文為血,以千萬文人為骨,才造就了這璀璨的文明。滋溪就是環繞著正定古城邊,被黃河長江孕育出的小龍。
我想,滋溪書院,就是孕育這一方水土的文化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