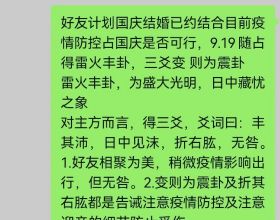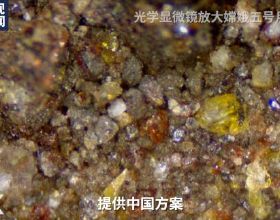我爸爸一生都執迷於自己的審美,他相信我家始終走在時代風貌的前列,尤其是在小鎮和縣城裡,我父母的朋友都認為我家是豪華的代名詞。多年後有次我去西安,聽到一個人形容他朋友家的裝修,用了一個詞:“金碧輝煌”。我立即想起我爸,他幾乎用了一輩子在追逐這個詞。
我爸出生在一個距離長江幾十公里的山村,據他說家裡屋頂是破的,只要下大雨,瓦片就往下掉。他的大哥,也就是我從未見過面的大伯,就是被村裡的大水沖走的。
他還說,家裡窮得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他初中沒畢業就參了軍,部隊改變了他一生(但沒有改變他的審美)。我出生的時候,他還在河南的部隊待了一年,一直做到連長。他應該是1978年退伍的,後來回到鄉政府當了幹部。
我不記得是哪一年,應該是在我出生前,村裡山洪暴發,山上滾下來一塊巨石,剛好砸到了那個破敗的老房子,砸到了我爺爺奶奶的床上,砸在了我爺爺的下半身,他當場去世,但我奶奶活了下來。我後來覺得,房子這事對我爸很重要,也許跟這個有點關係。
我出生在小鎮唯一一所小學的教職工宿舍。我媽是語文老師和班主任,因此有一個獨立的房間。我對那個屋子沒什麼印象,只記得廁所很遠,是學校的公共廁所,而這個廁所又在學校背後的山上。我媽後來說,家裡很簡陋。
到了小學三年級,我爸升了官,從鄉里升到了區裡,在區政府繼續做幹部。我們得到了兩間屋子,我住外屋,床就在窗戶底下,半夜總覺得玻璃上有張人臉。他們住裡屋,有一臺9寸的黑白電視(豪華)。
屋外有一塊空地,我爸養了很多花,每天花大量時間鬆土和澆水,多年後我在電視上看到各種退休老人都喜歡養花,他們總讓我想起我爸在盆栽之間來回移動的樣子,這種對植物的愛好和審美,也許是一種領導風範。
類似的愛好還包括一座假山。只不過我爸的假山座落在一個紅色的大腳盆,盆裡還養了幾隻蚌。我那時每天放學回家都先去扳一下蚌,希望能翻出珍珠來。後來他開始養鴿子,製作了四五個大籠子,籠子裡還有小屋,橫著木棍,到處都灑著玉米粒和穀子。鴿子的聲音是從喉嚨裡開始的,像幾百個人同時在小聲嘀咕。
幾年後,當我們再次搬家去縣城時,我爸找了一輛卡車運送這些鴿子。卡車盤山而下,半路上一顛簸,籠門全都抖開了,我爸說,等他反應過來,鴿子已經飛得一乾二淨,而他還以為那是山背後飛來的一群大鳥。
區裡的這個政府大院,我們也叫區公所,整個大院只有一個廁所,你得穿過幾條逼仄的巷子,沿著牆根走到非常偏遠的角落,一路陰風陣陣的。有天夜裡我爸從廁所回來,路上踩到了一條蛇,他說腳下一軟,腿肚子一陣刺痛。那是條毒蛇,他的小腿腫了三個月,包紮著各種草藥,他一瘸一拐地去給植物澆水,給鴿子喂玉米,渾身都是草藥味。
也是在那套房子裡,我媽有一天突然眼前一黑,瞎了。為了方便,她只好住在外屋我那張床上,鎮上的醫生全都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我爸找來了一個算命的,說是走江湖的,不知道用了什麼藥,我媽躺了三個月,竟然逐漸恢復了視力。
還是那套房子裡,我有次突發高燒,始終降不下溫,我爸在小飯館跟同事聊到我的病,隔壁一個吃飯的人聽見了,走過來對我爸說,你家小孩碰到事了,但他有辦法。他讓我爸去農村找一個年輕人,從他身上捉幾隻跳蚤,拿來燒成灰,灑在一碗水裡,給我灌下去。我媽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退了燒。
這些都是那套房子給我留下的最深記憶。那是八十年代末期,隨後我們搬到了縣城,我爸離開了政府,去了一家壟斷企業。我們在縣城的那套房子在當時真是有點金碧輝煌。
現在來看,我們在縣城的那套房子屬於一棟危樓,搬進去的第一天我就覺得這棟樓要垮。這棟六層小樓是本地人的自建房,沒有一個線條是直的,樓道狹窄,越往上爬越覺得傾斜,好像爬向了地面。搖搖欲墜了三十幾年,我最近一次回到那裡,發現它居然還在,我爸違章搭建的那個木質小陽臺也還在,幾乎是這個小城的歷史建築了。
在那套寬敞的房子裡,我父母開始了他們人生中第一次裝修。這個工程是如此複雜,在當時幾乎沒什麼經驗可循,連裝修這個詞都是新鮮的。他們決定一間一間來,於是所有傢俱在各個屋子來回挪移,而他們自己白天在廚房做飯,晚上依然住在擠滿了傢俱的臥室。我那時正讀初中,開始住校生活,每個週末回家時都會遇到一個全新的房間。
我還記得第一次踏入獨屬於我的房間,地板磚冰冷,牆面凹凸不平,因為他們用了一種名叫多彩的塗料,摸上去彷彿野外岩石一般刺手。陽臺被打通,包了一層厚厚的木框,窗戶是茶色的,窗簾是深紅色,紅到快要變成黑了,像往常一樣,我爸已經拉上了窗簾,屋裡漆黑一片。
當天晚上我幾乎整夜沒睡,因為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味道,我用手摳著牆上的塗料,張開大嘴呼吸,彷彿沉入水下,如今回頭看,難以想象我父母在充滿了甲醛的房子裡生活了那麼久,而我們所有人都毫無感覺。
那次裝修展現了我父母統一的審美,在任何細節上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比如在臥室打造了一箇中國園林式的月洞門,門上掛著粉紅色的珠簾,也許是從西遊記或紅樓夢的電視劇裡得來的靈感。但整體而言,那是一套舒適的房子,因為大多數傢俱都是他們年輕時結婚購買的,保留了一種蘇式復古的辦公室風格。
我意識到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爸愛上了打掃衛生,日復一日的用拖把擦地,因為地板是白色的,而他忍受不了一丁點黑色的顆粒。
全部完工是在夏天。那年暑假的一天夜裡,我被一種撞擊的聲音驚醒,彷彿有人在隔壁捶牆。我開啟燈,看見一隻巨大的飛蛾從空中掠過,它幾乎是求死一樣撞向天花板,我被它的尺度嚇到了,從沒見過那麼大的蛾子,翅膀像我的手掌那麼大。我在陽臺找到晾衣杆,試圖去觸碰,或者只是僅僅想把它趕向窗外。
這時我爸過來了,他站在窗邊盯著這隻飛蛾,沉默地盯了很久,然後他對我說,別動,這是你奶奶。我好奇地問,你怎麼知道?我爸彷彿沒聽見似的,他說她只是來看看你。他關了燈,然後我們站在黑暗中一聲不吭,聽見空氣裡傳來沉悶的碰擊,大約半個小時後,“我奶奶”飛走了。第二天我爸就託人去老家的墳前燒了一堆紙。
我們在這套房子住了快十八年。我升高中,考大學,隨後去外地讀書,畢業後偶爾才回來。隨著三峽水位的上升,新的縣城建起來了,人們開始往新城移動。2007年我爸媽賣了這套房子,在新建的長江大橋附近買了一套公寓。
那年我給我爸買了一個佳能的小數碼相機,春節期間他們跟著我旅行,他的相機記錄了一些看起來毫無意義的場景,比如旅館裡的一張床,街頭的一棵樹,更多是模糊不清的車窗即景。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回了一趟縣城,那是我第一次住進他們的新家。我爸得意的帶我參觀了所有房間,仔細解說每一樣傢俱和功能,我一邊走一邊附和,驚訝於看到的每一個細節——居然真的有人會買這樣的傢俱,這樣的顏色。
幾年後我們搬到了重慶。我爸在重慶的第二套房子實現了他的終極審美,全套金碧輝煌的歐式風格。我聽說老年人喜歡待在陰暗的屋子,我爸喜歡拉窗簾,我媽怕曬太陽,因此那套歐式公寓終日黯淡無光。但這是我的看法,我常看見我爸坐在鑲滿紐扣的棕色皮沙發上,心滿意足地看著這間屋子,你會好奇他們這輩子到底經歷了什麼啊。
就在上個月,我在一個資料夾裡翻到了我爸的數碼相機留存的照片,其中就包括下面這些圖片,那是他剛剛搬到縣城那套新房子拍下的。我簡直可以想象出他拍攝時的心情,由於自豪而希望所有物件永遠流傳,所有生活變成永恆。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孤獨圖書館(ID:aranya_library),作者:謝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