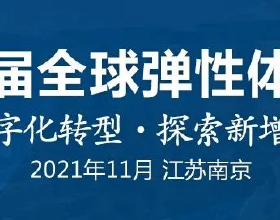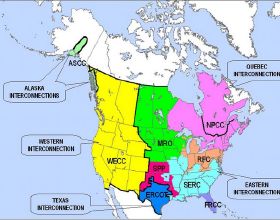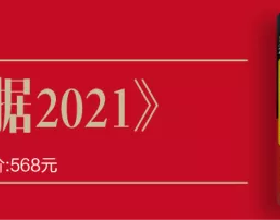紹興魯迅紀念館曾有這麼一號人物,他是“少年閏土”的孫子,曾擔任副館長一職。
他叫章貴,以魯迅研究專家的身份為世人所知。每當他回顧自己這大半生,永遠忘不了1954年魯迅紀念館成立時,工作人員找到他的情景。
當時,村長帶工作人員來到他家,希望他能去館裡工作,這個沒上過一天學的放牛娃誠惶誠恐,受寵若驚:“可是我不識字,能行嗎?”
工作人員笑著說:“能行!識字的人多的是,但像你這樣和魯迅先生有深厚淵源的,天底下怕是沒有幾個呢。”
章貴是章運水的孫子。提到章運水,人們可能有些陌生,但如果說“閏土”兩個字,人們定然十分熟悉。章運水就是閏土的原型。
章貴和爺爺章運水一樣,同樣是農民出身,同樣沒上過學讀過書。但不同的是,章貴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因為一個偶然的契機,又透過自己的勤奮努力,終於改寫了家族的命運。
1.少年閏土,是魯迅兒時快樂的源泉與心頭永遠的白月光
少年閏土是魯迅短篇小說《故鄉》中的人物,更是以同名標題入選小學六年級課本,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
提起少年閏土,我們腦海中就會浮現出這樣的畫面:月光下海邊碧綠的瓜田裡,一個少年手捏鋼叉,盡力向猹剌去。
魯迅寫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但對閏土傾注了特別的感情。因為閏土不僅真實存在,還是魯迅兒時最要好的玩伴。
閏土的原型叫章運水,紹興市上虞區道墟鎮杜浦村人。他父親名叫章福慶,在海邊種幾畝沙地為生,同時編得一手好竹器。算命先生說閏土五行缺水,因而父親給他取名“運水”;而魯迅在小說中改為“閏土”,寓意五行缺土,在紹興方言中“閏”與“運”同音,有異曲同工之意。
魯迅本名周樹人,在他的少年時代,周家還是遠近聞名的大戶人家,家裡有四五十畝水田。每逢農忙或過年時,閏土的父親就到魯迅家裡幹雜活幫忙,他手藝好,人又勤快,深受周家信任。
1893年春節,周家要舉辦一個重要的祭祀活動,事務繁多,人手不夠,閏土便跟著父親來周家幫忙看管祭器,因此和魯迅相識,併成了最要好的玩伴。
魯迅這樣描寫初見閏土的情景:他正在廚房裡,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
兩個年齡相仿的少年不到半天就混熟了,彼此以哥弟相稱,階層鴻溝在他們那裡似乎是不存在的。
地主少爺迅哥兒在高牆深院裡長大,少年閏土的世界對他來說是無窮無盡的新鮮與稀奇:下雪天捕鳥,海邊撿貝殼,潮水來時捉跳魚。
最厲害的要數月亮底下在西瓜田裡刺猹,那畫面如臨其境,讓年少的魯迅心馳神往,那時的閏土在他心裡簡直就是個少年英雄,無所不知,無所不會,朝氣蓬勃又充滿靈氣。
而迅哥兒則帶閏土在紹興城裡走走逛逛,看看城裡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兩個出身截然不同的少年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也結下深厚的友誼。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過了正月,閏土就被父親帶走了,臨別時,兩個玩伴都哭天抹淚難捨難分,彼此都沒意識到:多年以後,他們各自的境遇將是天壤之別。
2.漸行漸遠,出身和教育的不同讓兩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小說裡,魯迅寫的是他和閏土分別後,除了閏土讓父親帶給他一包貝殼和幾支很好看的鳥毛外,二十年裡再沒見過面。
但實際上,據魯迅的弟弟周作人回憶,從1900年到1912年期間,魯迅和“閏土”至少還見過兩次面。
那時魯迅十七八歲,在南京礦業學堂讀書,放寒假期間,閏土曾陪伴魯迅一起在紹興城遊逛,他們一起聊天、品嚐小吃。
閏土喜歡聽魯迅講學堂的新奇事,魯迅則很懷念小時候的無憂無慮,雖然彼此有著身份的隔閡,但起初他們還是保持著親密的友誼。
魯迅讀的是新式學堂,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崇尚自由平等,閏土則因為家庭環境所限,能夠吃飽穿暖就已經不錯了,家裡根本就沒有錢供他讀書,加上後來父親重病早逝,他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擔,子承父業,成為家裡的頂樑柱。
對於魯迅口裡說出的新名詞,閏土壓根就聽不明白。漸漸地,再見面時,兩人已經找不到什麼共同話題。
在此期間,周家也經歷了一系列變故,先是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行賄案入獄,然後父親周伯宜又一病不起,被革除功名後整日借酒澆愁,很快就與世長辭,周家就此家道中落,再也僱不起短工。
魯迅與閏土的生活從此沒有交集的可能,再見面時彼此都已人到中年。
魯迅一直在外求學,發憤苦讀,希望能夠學有所成,報效國家。1902年礦路學堂畢業後,又公費留學日本學醫,不斷追求更廣闊的世界。
而閏土自從父親去世後就過著一成不變的生活,每日下地幹活,搖船、做工,到了一定的年齡娶妻生子,最大的願望不過是有個好收成,官老爺少收點租,家人的日子能好過一點。
兩個原本就出身懸殊的年輕人漸行漸遠,從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3.中年重逢,被殘酷現實築起的隔膜與辛酸
1921年冬天,魯迅再回到故鄉時,懷著美好期待再次見到閏土,他早已不復少年時純真健壯的模樣,儼然一副窮困潦倒的底層農民形象:
“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穿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縮著,那手也不再是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這些年,他到底經歷了什麼?
閏土有六個孩子,一家人就靠那幾畝沙地和打打零工討生活,然而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饑荒,苛捐雜稅,加上土匪和官兵的巧取豪奪,一年到頭辛苦勞作,連填飽肚子都難。
眼前的閏土臉上刻著深重的皺紋,像石像一樣沉默,他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只能默默地吸菸。在他身上,已經找不到一丁點少年時的靈氣與生機。
與外表的愁苦相比,更讓魯迅心寒的是閏土精神的麻木,和對現實的逆來順受。闊別多年,當魯迅滿懷歡喜說:閏土哥,你來了?
閏土卻只是嘴唇動了動,半天才怯生生叫了聲:老爺!……還要拉著藏在身後的兒子水生給魯迅磕頭。
水生已經十七歲,儼然又是二十年前閏土的翻版,唯一的是脖子上沒戴銀項圈,更黃瘦些。
從這個細節也可看出,由於饑荒、兵、匪、官、紳,苛稅的存在,二十年來農民的生存境況不僅沒有絲毫的改善,反而更艱難了。
這一聲老爺徹底擊碎了魯迅童年的美好回憶,也在兩人間築起深重的藩籬和無形的隔膜。
雖然多年未見,兩人再也沒有什麼話說,只能聊些無關緊要的閒天。
閏土又何嘗不覺得尷尬和辛酸呢,他第二天領著水生回去,明明水生和宏兒已經混熟了。
到魯迅啟程那天,他去送行,順便把挑揀的東西運回去,帶的卻不是水生,而是5歲的女兒章阿花,說是幫著看管船隻。
雖然閏土已經被世道逼成了木偶人,但心底多少還殘留些自尊吧,他不想讓自己的兒子水生和魯迅的侄子宏兒重蹈上一代的悲劇,那樣太殘忍了。
閏土沒上過一天學,沒見過新世界是什麼樣,更不懂得什麼大道理,他只知道對有權有勢的人要畢恭畢敬,吃官家飯的人都是得罪不起的。
雖然和迅哥兒是小時候的玩伴,但那個時候少不更事,哪裡知道人是分貴賤的呢。成人的世界只有生存的艱難,談友誼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對閏土來說,對魯迅稱呼“老爺”幾乎是本能的選擇。
說到底,這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雖然當時已經是民國了,但是紹興農村依舊是封建宗法制社會,農民的思想普遍處於矇昧狀態。
1921年的魯迅已經在教育部任職,他此次回鄉本是為了告別老屋,接母親到北平,和閏土的見面讓故鄉殘存的最後一絲念想也破滅了。
故鄉從此不再值得留戀,西瓜地上銀項圈小英雄的影像也從清楚變得模糊,離開故鄉的途中心緒也因此格外沉重。
魯迅從中年閏土的身上看到故鄉衰敗的根源,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熱切希望後代們不要像閏土那樣辛苦麻木地生活,更不要像他們之間那樣隔膜起來。
“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是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4.世道滄桑,兒時玩伴先後離世,閏土後代生存艱難,孫輩章貴實現逆襲
和閏土的見面是魯迅創作小說《故鄉》的重要原動力,而據留存的資料來看,除了一些細節上的處理,《故鄉》裡面的人事描述都是對真實生活的高度還原,關於閏土的描寫更是他真實生活境遇的再現。
人到中年的閏土一年到頭手腳不停,要應付官府的苛捐雜稅,提防土匪強盜,整天為了讓孩子們填飽肚子發愁。哪承想,晚年的閏土生活更為悲慘。
1934年,浙江全境大旱,水鄉紹興城大大小小的河溝都斷流了,田裡都冒煙,大旱過後蝗災又至,閏土的6畝薄田顆粒無收,討債的、官府逼捐的又找上門來,擾得家裡不得安寧。
閏土實在沒有辦法,只好一咬牙把那6畝沙田也賣了,流落外鄉靠打零工和當佃農為生。但日子卻是更苦了,畢竟還要給東家交租,能落到手上的更少了。
年歲不饒人,閏土的身體也越來越差,1936年夏天,他背上長了個毒瘡,剛開始只是紅腫癢痛,漸漸開始流膿。
因為沒錢醫治,他只能忍著疼痛白天繼續幹活,晚上讓老伴幫他擦洗乾淨,再疼也只是小聲哼兩聲。
兒子章啟生看在眼裡,心裡很不忍,在閏土聊起多年前帶他去魯迅家送行的往事時,試探地說:“爹,咱要不要試著給老爺寫封信,他肯定會幫你的。
那年,宏兒跟我玩的可好了,還分給我很多糖果呢。”閏土卻只是輕輕地搖搖頭:“老爺是個好人,可咱這麼多年也沒幫過人家,現在憑什麼麻煩人家?”
一個月後,閏土病重去世,年僅57歲。
同年,魯迅因長期伏案寫作積勞成疾導致肺部病灶加重,不久也逝世了。
閏土去世後,章啟生作為家裡的長子又挑起生活的重擔。但是不幸的是,章啟生本來就體弱多病,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下不到40歲就去世了,留下兩子一女,次子就是章貴。
章貴的母親不得已只好帶著年幼的女兒去城裡給人當保姆謀生。章貴的哥哥小小年紀當了童工,而章貴因為年紀太小,被寄養在叔叔家,當起了放牛娃。
不久,章貴妹妹得了肺病早早夭折。一家人為了生存四散飄零,苦日子似乎沒有盡頭。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章貴終於迎來了命運的轉機。章貴雖然沒上過學,但從小就聽父親講過章家和周家的交往,對於父親口中的大人物魯迅充滿神往和好奇。
當他得知政府要建魯迅紀念館時,就經常跑到籌建處去幫忙,一來二去就和工作人員熟識了。工作人員得知他的身世,又見他口齡伶俐,就邀請他去館裡工作。
一開始,章貴因為沒文化,只能幹些搬搬扛扛的力氣活,但章貴很珍惜這個工作機會,更想深入瞭解魯迅的生平事蹟,於是他白天工作,晚上去讀夜校,刻苦學習文化。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章貴對魯迅作品和生平事蹟有了深入的瞭解,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成了魯迅研究專家和作家。
1982年,章貴因工作出色被任命為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而章家和周家延續數輩的交往在章貴這裡又續上了。1959年,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和章貴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相見,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周海嬰主動提出要為章貴的新書作序。1976年,在魯迅逝世四十週年之際,周海嬰又邀請章貴同去日本,期間,年長几歲的周海嬰對章貴照顧有加,過馬路都要拉著章貴的手,怕他撞到車上去了。
兩人雖然差了一個輩分,卻交往頻繁,無論是你到紹興還是我到北京都要聚在一起坐坐。魯迅先生的在天之靈應該欣慰,他和閏土的後代終於實現了人格與身份的平等。
晚年的章貴對於現在的生活非常滿意,他的兒子當了一名紡織廠機械工程師,女兒做了幼兒老師,工作都很體面。
章貴在1993年退休後還繼續活躍在工作崗位上,經常給來參觀的人們講解,告訴他們今非昔比,閏土的後代們已經過上了好日子,魯迅先生小說裡閏土家的悲慘景象已經永久地成為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