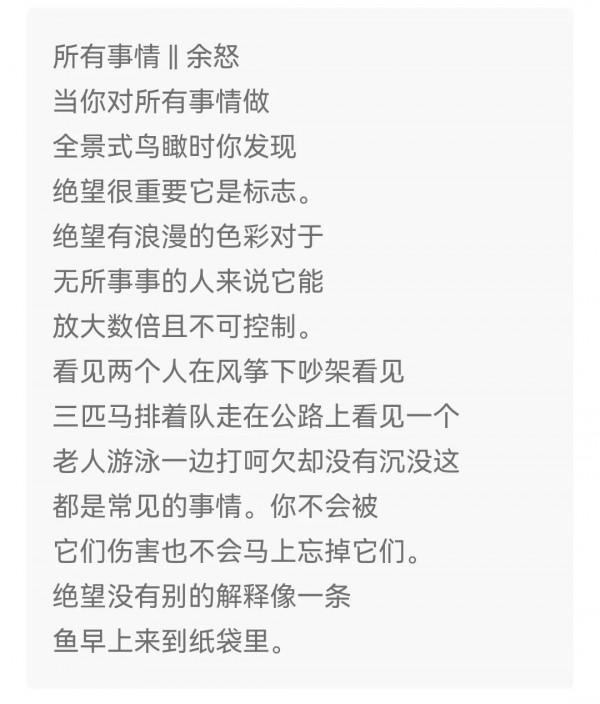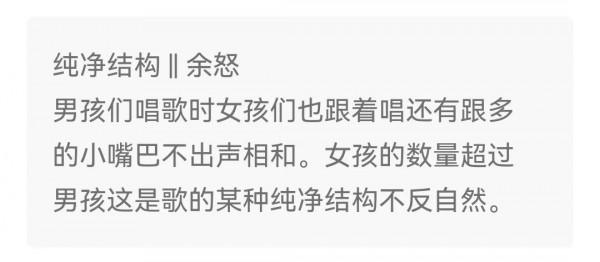說起現代詩,“分行”那是其精髓。我們現代詩的功夫,重點已經不在內容上,而是在了分行上。一句話,分成若干行,管你是什麼內容,那必然就是現代詩。如果“碰巧”得到了哪位大編輯的賞識,那就成了“好詩”。
即使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句話,分行之後,也可能成為好詩。比如,一級作家、“梨花體”創始人趙麗華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這其實就是一句話,卻非要分成四行,於是,就成了詩了。你們看看,寫詩是不是功夫就在分行上?
現在的“著名詩人”們(詩人前面最好都加上著名二字,這樣保險),誰分行分得最好?這個還真不好說。俗話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分行也是如此,輕易沒有誰敢說誰是“第一”。要說誰的分行分得最差?答案同樣也不好找,畢竟,分行是沒有任何原則可講的。
但在這“最差”一列裡,應該少不了一位“著名詩人”,那就是餘怒。餘怒算得上是“資深詩人”,早在1987年就在《湖南文學》上發表了作品。十月詩歌獎、紅巖文學獎詩歌獎、袁可嘉詩歌獎,這些獎項都集中在2015年之後,雖然來得有些詞,但也說明餘怒是“著名詩人”。
當然,這也許還不夠“著名”,但《詩刊》在2018年6月“頭條詩人”裡推薦了餘怒,一口氣發表了他17首詩,那他才真的是“著名”了。從1987年到2018年,餘怒熬過了31年,不可謂不長久。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編輯有多“重要”。
餘怒的詩,最大的特點就是“換行自由”。沒錯就是“自由地換行”,換句話說就是想在哪兒換行就在哪兒換行。餘怒不僅僅是換行自由了,而且是往往在不該換行的時候換行,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
這首詩,讀下來有點讓人喘不過氣來,還有點讓人“措手不及”的感覺。你剛讀得好好的,結果它卻換行了。你以為它要換行的時候,它卻一個標點也沒有地緊接著下一句了。比如第一句,在“做”那兒換行,在這一行裡,後面整句話就留下個孤零零的“做”。
這樣的句子還有很多,“絕望有浪漫色彩對於”,“老人游泳一邊打呵欠卻沒有沉沒這”。所以,餘怒的換行,那確實是“隨心所欲”。想換就換,不管語句意思到了哪兒,是不是不該換,還是該換。
餘怒的詩,還有個特點,那就是他好像只會用句號。在語句之後是句號,在語句中間也是句號。明顯地看出來是兩句話,中間卻沒有任何標點符號。什麼逗號啊,頓號啊,分號啊這些符號都不在餘怒的使用範圍之中。
餘怒自己對於現代詩,是有一番理論體系的。1993年10月,他在《從有序到混沌》這篇文章裡,提出了“混沌詩學”這個概念。這“混沌”二字,好像特別招文化藝術家們喜歡,前天我還寫了一篇文章,說“書法家”石虎的書法精髓也是“混沌”。
餘怒自由分行了這麼多年,為何直到2018年才在主流期刊《詩刊》上成了頭條詩人?其實在前面的那些年裡,餘怒都是詩壇的邊緣人物。他寫詩,算詩人,但卻一直在詩和非詩之間掙扎。他自費辦刊物,自費出版詩集,與主流的刊物和出版社總是沾不上邊。
所以說,《詩刊》在2018年為餘怒“正名”了,他才成了被主流詩壇認可的“著名詩人”。而他的“混沌詩學”,到底混沌在何處,其實除了分行比較“混沌”之外,倒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從內容上來看,比他“混沌”的詩多了去了。
讀了餘怒的詩,不免讓我想起了金庸《天龍八部》裡的虛竹。虛竹揹著天山童姥前往西夏,途中天山童姥教他“天山折梅手”。但這武功口訣讀起來很費勁,該停的地方不停,不該停的地方卻停了,讓虛竹很是傷腦筋。
不過,虛竹那是在練功,是調運真氣的法門,吃點苦頭也是正常的。可讀餘怒的詩也這麼費勁,我們圖的又是什麼?是他的詩內容確實好?好像也沒有多“美妙”。既然我們什麼也圖不到,那何必費這個勁呢?讓他自由地去換行吧,免得因“餘怒未消”,而殃及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