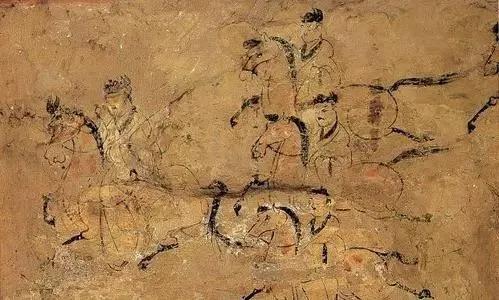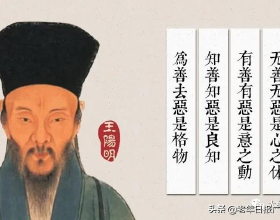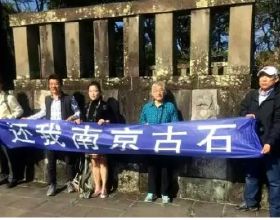天康元年(566),在位僅7年,曾讓陳朝在極短時間內擺脫亡國處境,立隅於東南一足的傑出君主陳文帝陳蒨病重,遺詔由自己年僅14歲的太子陳伯宗繼承皇位。
陳伯宗,他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上最冷門的人物之一。雖然貴為帝王之尊,但他的熱度卻一直不高:在他出生那年,還沒有陳朝。直到他六歲時,他的叔祖陳霸先成為了開國皇帝,因為他父親陳蒨被封為臨川王的關係,他才以嫡長子的身份得以成為王世子。
陳蒨工作優秀,才華橫溢,備受叔父陳霸先的厚待。在陳霸先去世後,由於老陳的大兒子陳昌因為政治緣故被扣留在北周,風雨飄搖的陳朝又不可一日無長君,陳蒨便在大將擁立下成為了皇帝,陳伯宗順理成為了皇太子。之後陳蒨又借大將侯安都之手,殺死了即將歸國的陳昌,消滅了陳伯宗通往帝位的一個潛在隱患。
由於陳伯宗的弟弟們年紀尚小,不構成對他何何的威脅勢力,再加上陳蒨在位時間極短,他也是波瀾不驚地當上了皇帝,只是他這個帝王不僅在歷史上藉藉無名,而且最終在權術的傾軋中慘淡地退出了歷史舞臺。
原因在於他有一個相當腹黑的叔叔——安成王陳頊。
陳頊,陳文帝的弟弟,早在陳朝立國初期,他就在蕩平國內各處叛亂中積累了不俗的聲望。陳文帝對他很是看重,將他封為安成王,輔作政務。短短几年內,陳頊便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威望也如日中天。
陳文帝對他這個弟弟,是既放心也擔憂。
45歲這年,陳文帝身體抱恙,隨後迅速惡化,行將不治,在彌留之際,他特意召集了陳頊和舍人劉師知、僕射到仲舉、孔範等中樞重臣,交待後事。
陳文帝對陳頊說:“如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國家宜賴長君,我看你是不二人選。”
陳頊流涕叩拜:“臣不受此命,臣甘當盡心竭力輔佐太子!”
陳文帝又詢問了劉、到、孔幾位重臣的意見,告訴他們自己要傳位於弟弟陳頊,眾臣齊聲哭拜道:“臣等一意扶保太子,如果安成王有篡逆之心,我們也絕不答應!”
陳文帝見眾臣此舉,心中一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他安心地走了。
陳文帝不放心兒子陳伯宗可以安然成為一位太平天子:畢竟歷史上幼主登基,皇位被篡奪的典故太多了,尤其是宗室內部,王叔要挾皇帝,自立篡權更是屢見不鮮。此刻自己的子侄一輩已經沒有一個能對陳伯宗的帝位產生威脅,所以自己親弟弟陳頊的存在,就是一個頭號威脅!如果陳頊和眾臣有一人膽敢應承他所謂的囑託,他會讓他們頃刻間成為刀下亡魂!
陳文帝希望弟弟像當年周公輔佐成王一樣輔弼太子,但他的大好期許卻完全落空,因為陳伯宗上位後,陳頊並沒有老老實實地待在朝中,而是操縱軍權,直接領兵在揚州駐紮下了!
對這一切,年輕的陳伯宗是毫無辦法,他拿不出任何節制叔叔的行動,因為他剛登基不久,到仲舉和劉師知等一干重臣就直接搬到皇宮裡住下了!
陳伯宗或許是沉澱太少,在朝內,無論大事小事,他的決策都要被到、劉等人左右,自己一直拿不定一個核心主意……一段時間過後,皇帝的意思已經成為了臣子的意思,他已經淪落為劉師知等人的橡皮圖章。
而遠在揚州的安成王陳頊,也不忘插手朝中事務——他已重兵在手,並在朝廷上下佈滿了眼線,所以一直遙控朝政,對皇帝發號施令,他說是一,皇帝就不能說是二。
陳伯宗一視同仁,對叔叔的話也基本是言聽計從,不敢有絲毫的違背。
但是這樣一來,就相當於核心決策權為空,導致了內朝和外朝爭奪朝中話語權的矛盾。
舍人劉師知個性要強,他深知自己雖是先帝的顧命大臣,但對外朝卻無任何的節制能力。此刻陳頊領兵在外,又是至親皇族,如果事事都按照安成王的意願,自己手裡這杯羹企不被人一步步吞噬、地位不保不說,甚至還搭上身家性命?
他最終選擇的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一擊致命,幹掉陳頊。
劉師知作為近臣,時常替天子起草詔書,正是有這個職務之便,他居然擅自假借太后名義,給陳頊寫了一封矯詔,召他回到朝中。
“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陳書》
詔書大意是:現在天下已經基本上沒有戰端,你也不用在外勞苦奔波了,倒不如把手上的兵務先放一放,回到朝廷樂呵他幾天太平日子!
發出詔書,劉師知內心是暗自狂喜的:反正皇帝與太后都是不管事的主,天下共知。你就算懷疑也好,也想象不到內朝已經是我的天下,從此你就受制於我了!
陳頊看到了這份偽詔,也是這麼想的——他是對自己侄兒的話信以為真了。
但是,劉師知機關算盡,也不會想到,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陳頊手下謀士毛喜,一眼就看出了問題的所在,他直接用當年曹爽的典故,點醒了陳頊!
毛喜告誡陳頊:一旦你今天離開了自己的大本營,以後都將是龍游淺灘,身處困境。今天這封詔書寓意不明,萬萬不能以身犯險,淪落為成為劉師知的池中之物!
陳頊火冒三丈,同時他又不動聲色,他透過謊稱自己早已患病、不久於世、不能領命為由,騙得了劉師知隻身前來,在自己的地盤將他扣押了起來!
劉師知想效法司馬懿,最後卻成為了曹爽,也是作繭自縛,遺笑千古了。
陳頊立刻派毛喜進宮,此舉是為了驗證詔書的真偽,毛喜首先拜訪了太后沈妙容,得到太后的答覆是:我不知道。
隨即,毛喜又轉頭去問了小皇帝陳伯宗。
陳伯宗一個勁地搖頭,他本來就置身事外,也沒把叔叔當做敵人,大臣不通氣,他又懂個啥?
確認了太后、皇帝的態度後,陳頊的膽子就更加壯了,他已囚禁劉師知,隨即進宮討要說法,他不僅當著帝后的面彈劾劉師知的罪行,並當場寫下了處決劉師知的詔書。
陳伯宗這個橡皮圖章,再一次為大臣的獨斷,簽署了自己的名字。只是這次,陳頊在通往篡位這條道路上的阻力已經越來越小了。
劉師知被處死,參與他密謀的一干人等也盡皆被治罪,連他的同僚到仲舉也被革職回家,透過一系列行雲流水的操作,內朝的障礙基本被清掃乾淨,陳頊要轉過身面對的對手就是中央的軍權了。
右衛將軍韓子高手握建康城內兵馬最多的軍隊,陳頊也懷疑他參與了劉師知等人的密謀,不過為了不打草驚蛇,陳頊顯現出了一個政治家必備的沉穩作風:先派手下花重金重物穩住韓子高,然後藉口立誰為皇帝太子的問題召開一次會議,將韓子高、到仲舉等人騙到尚書省,輕車熟路地將他們一併處死了。
此時的陳伯宗年僅15週歲,他甚至可能還不懂什麼是床笫之歡,以立太子為話題召開廷議,不是很搞笑嗎?
不論陳伯宗內心有何感想,陳頊再也沒給予他任何的尊嚴,叔叔已經徹底將大陳朝廷變為自己的一言堂——他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完全無視了一個臣子最後應盡的本分和禮節,甚至比那些外戚外臣專權還要囂張一些。
陳伯宗即位後的第三個年頭,即光大二年(568),陳頊以陳伯宗個性軟弱、難當大任為理由,廢除了陳伯宗的帝位,自己堂而皇之地篡帝自立,即為陳朝孝宣皇帝。
一國之主,就這樣,淪落為待宰的羔羊。
僅僅兩年以後,年僅19歲的陳伯宗離奇地離開了人世。此前兩年,他的同胞弟弟陳伯茂也離奇被殺。
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南史》
一國國君,必須懂得駕人馭人的道理,陳伯宗無疑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不懂得政治中最無情黑暗的一面,只能盲目相信他人,以致於自己被架空,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如果他能及早領悟到這一點,或許他就不會讓劉師知那樣盲目自信,使內外朝之間維持的平衡徹底倒向陳頊……
或許,他在不該有的年紀接受了不該有的皇位,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