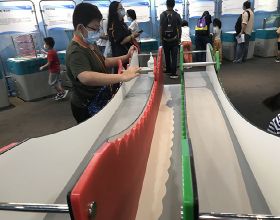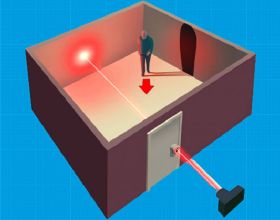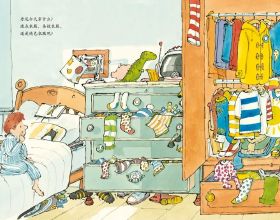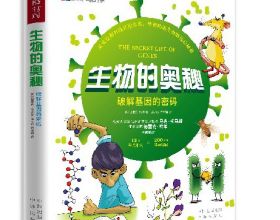自然現象中,氣候和人的關係最為密切,寒燠燥溼是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可以感受得到的。這在遠古時期就是如此。殷墟發掘出來的甲骨文應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其中就有很多有關求雨求雪的刻辭。後來到《禮記·月令》,記載就更為周到。孟春之月,記載著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其後每個月的記載都相當具體。而各史的《五行志》中就愈加詳細。根據這樣的記載,前人亦多所究心,北宋的沈括就是其中的一位,其遺說具見於所著的《夢溪筆談》之中。近數十年來,學者間的研究絡繹不絕,立論雖不盡相同,但對於解釋有關問題,都費了很多心機。
一、進入歷史時期的溫暖氣候
論古今氣候的異同,可以追溯更為渺茫的遠古。但從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其上限也應是由人類最初從事生產勞動的時期開始,這時已進入新石器時期。一般都以半坡文化遺址所顯示的情況作為準則。半坡文化遺址經C(碳)14年代測定為距今5600年至6080年。由於具體遺存物的發現和測定,不盡都能一致,在年代上有所伸縮也是可以理解的。氣候溫暖時期和寒冷時期變遷的顯現,並非短時之內所可覘見,因而有關的年代就難得若何具體,當然也不能過分懸殊。
從進入歷史時期,氣候就顯得較現在為溫暖。由東北部直到長江以南都是如此,就是內蒙古和青藏高原也都不是例外。據估計,東北黑龍江和吉林等處,當時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以上,冬季最冷月平均氣溫比現在高6℃以上。遼寧南部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左右。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各地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2℃—3℃,正月的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5℃。長江中游年平均氣溫也比現在高2℃左右,天山北麓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1℃左右。西藏自治區希夏幫馬峰西北佩估錯低湖旁階地的當時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左右。珠穆朗瑪峰北坡河曲谷地里亞村的當時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3℃。正因為這樣,當時的亞熱帶北界就由現在的淮水流域北移,現在的京津地區在那時已經接近亞熱帶的北緣[1]。當時不僅氣候溫暖,而且顯得溼潤,應是溫溼的亞熱帶氣候[2],和現在很不相同。
確定當時的氣候較現在要溫暖溼潤,是由遺存到現在的動物骨骸和植物孢粉的檢定得出的結果,其中有的還可由文字記載來證明。就以半坡文化遺址來說,其中就發現過獐、貉和鹿等類動物的遺骸[3]。鹿為產於北方的獸類,在半坡出現,實不足為奇。獐到現在只有生存於長江流域的沼澤地區。貉也是喜棲於河湖濱畔。這些喜溫暖潮溼的動物能在半坡生存,證明當時的氣候和現在很不相同。在安陽殷墟的遺物中,有象、貘、獐、犀牛、鯨的骨骼,經古生物學家的研究,它們出土於安陽,是有外來的可能性[4]。不過其中的象是曾經生長於黃河流域的。卜辭記載殷代田獵有獲象的語句,既為獵獲的獸類,當不是由外方來的。卜辭“為”字從手牽象。可見象也是經常被服役的動物。殷人是曾經役使過象的。象的出沒存在,說明當時殷墟的氣候溫暖,適於象的生存。以殷王的威力是可以獲得遠方送來作為進貢的動物。可是半坡遺址的原來居人是不會有這樣威力的,為什麼這樣一些動物也曾經在半坡發現過。看來半坡遺址和殷墟的氣候是相彷彿的。兩者的年代相距較遠,這隻能說其間的氣候沒有很大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溫暖氣候,有關各地所發現的孢粉就是具體的例證。黑龍江省呼瑪縣的榿樹和其他落葉闊葉樹的孢粉[5],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中旗大義發泉細石器文化層不僅中期花粉含量多於晚期,且有喜溼喬木櫟樹和草本十字花科的花粉[6],可見這些北部地區的溫度和溼度都高於現在。就是西北地區天山北麓,當時雲杉生長線也比現在為高[7],而西藏自治區希夏幫瑪峰下和珠穆朗瑪峰北的孢粉和植物化石以及中石器時期的遺存,都可以作為證明[8]。
二、周初的寒冷氣候與其後又復轉為溫暖時期
這樣的溫暖時期,歷史相當悠久。前面說到殷人的獲象乃是武丁時事。武丁為王已在商代後期。直到周初,還是相當溫暖,竺可楨以《詩·國風·召南·摽有梅》所詠的“摽有梅,頃筐塈之”為證。召為周畿內采邑,所謂召南之地,亦只在岐山之陽[9]。《召南》雖有《江有汜》篇,然《摽有梅》似難說到與江有關的地方。岐山之陽也就是今陝西省岐山、眉縣等處。竺可楨於此還徵引了《詩·國風·豳風·七月》為證。兩篇詩據說都作於西周時,但所顯示的氣候卻很不相同。能有梅樹,可見當地氣候仍相當溫暖。可是《七月》詩中所說的季節,卻較《召南》為遲。豳與召相距很近,如何能有兩種不同的氣候?這似乎不能以豳地海拔高的緣故來解釋。《詩序》對這篇詩的寫作年代的說法實嫌籠統,似不易就此得出肯定的結論。
雖然如此,西周時期的氣候確實是曾經由溫暖轉向寒冷。因為《今本竹書紀年》有這麼一條記載:“周孝王七年,江漢俱凍[10]。”而且只有這麼一條,此事未見於《古本竹書紀年》。《今本竹書紀年》的記載雖多不可盡信,然江漢凍結乃自然現象與人事無關,可能並非有意作偽。
就是江漢確有凍結,寒冷時期也不會過長。竺可楨於此徵引了《詩·衛風·淇奧》所詠的“瞻彼淇奧,綠竹猗猗”,作為證明。《淇奧》一篇,據說是美武公之德,當作於衛武公之時。衛武公元年為周宣王十六年[11],是年上距周孝王七年為89年。淇水之旁的綠竹猗猗,應該不是從這一年起才開始有的。《淇奧》這篇詩的撰寫時間雖顯得略早,然以竹證寒溫的變化終究感到勉強,不如徵引《秦風·終南》一篇為合適。這篇詩說:“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這裡明確提出梅樹,梅樹對於氣候變化的感受較為靈敏,能夠說明問題。《詩序》以為《終南》這篇詩,是為了告誡襄公而撰寫的。秦襄公元年為周幽王五年[12]。這一年較衛武公元年遲35年。衛武公在位時久,共55年。衛武公四十七年,秦襄公即已逝世。因此不能就說《淇奧》一篇的撰述就早於《終南》。周孝王江漢凍結之前,是什麼時候由溫暖轉為寒冷的?也無所證實。最早似不能超過周昭王時。周昭王南征不返,卒於江上[13]。若其時氣候已經轉寒,江漢可能凍結,昭王是不會輕易南征的。昭王在位年數說者間有不同,大約以十九年為是[14]。由周昭王十九年至周幽王五年,亦將及兩個世紀。
西周和春秋時期,梅在黃河流域多所種植,這在《詩經》裡曾經有過多次的描述,足以證明當時的氣候是相當溫暖的。但梅在黃河流域並不是直到西周和春秋時期才開始繁殖的,根據《尚書》的記載,在商代即已用梅作調和飲食的調料[15],可見它在黃河流域的種植是很早的。當然也可作為商代氣候溫暖的證明。
證明這一時期氣候的溫暖,除梅而外,還可舉出一些例證,檀、棕、楠、杉、豫章等樹在那時都是黃河流域不難見到的樹木。檀見於關中和中條山上;棕見於秦嶺和崤山、熊耳山,最北且達到白于山和六盤山;楠見於秦嶺和崤山;杉見於終南山;豫章則見於關中[16]。這些樹木大致在唐代以後就很少再見於有關黃河流域的記載。這正有助於說明前後不同時期氣候溫暖的差異。這裡所說的秦嶺、終南、中條、崤山和熊耳諸山,東西相望彷彿成為一線。白于山和六盤山卻遠在今陝西北部和寧夏南部,相差很遠。可見氣候的變化不僅限於秦嶺和淮水的南北。近人論及黃河中游的森林,以現在陝北和寧夏的乾旱,否認歷史時期這些地區曾經有過森林,而不悟氣溫溼度前後的變化。以現在的自然條件如何能夠論證千百年前的情況?
三、氣候的變化與竹的產地
這裡當論述竹與氣候的變化有無關係。近人論氣候皆以竹在黃河流域的生長作證明。如論半坡遺址當時氣候的溫暖,就以竹鼠為證。竹鼠以竹為食料,可見當時半坡多竹,竹鼠賴以生存。後來半坡附近竹林稀少,甚至無存,竹鼠也就消失了。竹也見於山東省歷城縣龍山文化遺址和河南省淅川縣下王崗遺址。這兩處遺址中分別有炭化竹節[17]和竹炭灰[18]的發現,因而就以此證明當時這裡的氣候也相當溫暖,與半坡遺址相彷彿。說到西周春秋時期的溫暖,論者皆舉《詩·衛風·淇奧》一詩所歌詠的“瞻彼淇奧,綠竹猗猗”作證明。其實由西周春秋以迄戰國時期,黃河流域竹的種植是相當普遍的。當時人們日用器皿許多都是以竹製成的。食器有簠、簋、籩、簝,樂器有笙、竽、簫、管,盛物有筐、筥、篋、篚,寢具有簟、箐、籧、篨。記事用簡,信約用符,射用箭,食用箸。如果黃河流域不產竹,以竹製作的器具當不至於這樣的眾多。黃河流域產竹著名的地區當推淇水流域,這是周代衛國的地方。《詩經》中對於衛國的竹林是一再諷詠不止的。上面所舉的《淇奧》就是其中的一篇,還可再舉出另一篇,《衛風·竹竿》也曾歌過:“籊籊竹竿,以釣於淇。”這足見當時人們的重視。齊國也產竹,臨淄(今山東淄博市舊臨淄縣)城西的申池就是一個產竹的地區[19]。汶水流域產竹更是有名。樂毅報燕惠王書中就曾提到汶上的篁[20]。
到了秦漢時期,氣候有了變化。可是還有人認為是相當溫暖的,同樣也徵引有關竹的文獻作證明。這時的竹本來是相當繁多的。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就曾經特別稱道“渭川千畝竹”。這是說,在渭川這個地區,普通人家如果能栽種千畝竹林,他的收入就可以和千戶侯相彷彿。而鄠(今西安市鄠邑區)、杜(今西安市長安區)竹林還可和南山上的檀柘媲美[21]。淇水流域產竹,直到漢代,一直都是有名的。當時黃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陽縣)決口,漢武帝親臨堵塞,堵口的材料就是用的淇園之竹[22]。東漢初年,寇恂為河內太守,也曾伐淇園之竹,製成百餘萬支箭,抵制自南而來的攻擊[23]。光武帝能夠在河北立住腳,和這宗事情很有關係[24]。
經過魏晉南北朝,下至隋唐時期,氣候又轉為溫暖。唐代關中亦多竹[25],竹林蔓延,西逾隴山,直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市)。杜甫《秦州雜詩》中曾經三次提到竹樹,當非偶然[26]。就是太行山東淇水流域的竹林,也仍然受到稱道[27]。隋唐以後,經過宋代一段寒冷時期,至於元代,再度轉暖。竹還是用來作為溫暖氣候的證明。根據《元史》的記載,元初曾於腹裡的河南、懷、孟(今河南省沁陽市和孟州市)和陝西的京兆、鳳翔(今陝西省西安市和鳳翔縣)置司竹監。稍後,又於衛州設定管理竹園的官吏,舉凡輝、懷、嵩、洛(今河南省輝縣、沁陽市、嵩縣、洛陽市)和益都(今山東益都縣)等處的竹園都受到管轄[28]。可見當時黃河流域產竹的地區還是不少的。
作為氣候溫暖時期論證的依據,這些文獻記載或多或少都曾經被徵引過。翻過來說,氣候轉為寒冷時期,應該是原來產竹的地區就不可能再有竹的生長了。這不是產竹地區的多少或大小的問題,而是有無的問題了。前些年間,還有人斷言說,竹不過秦嶺。這顯然是說,秦嶺以北氣候寒冷是不適於竹的生長繁殖的。可是實際情況卻並非這樣。
魏晉南北朝是氣候寒冷的時期。在此以前,可能在西漢時氣候就已經逐漸轉寒。可是班固撰《西都賦》,還說長安附近,“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29]。張衡撰《西都賦》,也說長安附近,“筱蕩敷衍,編町成篁”[30]。班固和張衡之時,長安已廢不為都,但以東漢時人侈述西京舊制,也許還有若干誇張。曹魏時劉楨撰《魯都賦》,則在易代之際,應該不會再有過譽之辭,卻也說到曲阜的“竹則填彼山陔,根彌阪域”[31]。西晉左思撰《魏都賦》,也說鄴城“南瞻淇奧,則綠竹純茂”;說到物產,還特別提到“淇洹之荀”[32]。鄴城如此,洛陽附近同樣是“竹木蓊藹”[33]。晉武帝后宮爭寵,宮人多以竹葉插戶,以引帝所乘的羊車[34]。就是長安城外,也還是“林茂有鄠之竹”[35]。當時有一派所謂名士,放浪於形骸之外,以相標榜。竹林七賢即其著者。據說他們的遊蹤就在現在河南省輝縣[36],因為所謂竹林,就在當地。十六國時期,苻堅曾在阿房宮種植桐與竹數十萬株,以待鳳凰。淝水戰前,長安上林竹死,說者謂苻堅敗亡之兆[37]。現在河南輝縣濱於清水。清水下游正與淇水相合,相距並非很遠。清水源頭亦有竹林,據北魏時酈道元所見,當地竹與剎靈,更為勝處[38]。兩漢時,為了管理竹園,曾經設定過司竹長丞。魏晉河內淇園也各置司守之官[39]。可知左思《魏都賦》中所說的並非虛誇。可是到北魏時,酈道元親至淇水側畔,竟未見到竹[40],這應是人為的砍伐所致,與氣候無關。因北魏依漢魏舊規,仍設有司竹都尉[41]。北魏疆土僅有黃河流域,而清水源頭的竹林仍與柏樹相輝映,就是長安附近,也還是一樣有竹圃的[42]。據說司竹監到北齊、北周時未曾再置,隋唐時期才又得到恢復[43]。北齊、北周歷年短暫,設官不周也是有的。不能因為這兩個政權未曾派專人管理竹園,就認為當時黃河流域已經無竹。如果齊、周之時黃河流域已無竹林,則隋和唐初長安附近能有偌大的司竹園,就顯得突然了。
歷隋唐而至宋代。宋代也是一個寒冷的時期。宋代雖是寒冷時期,產竹之地仍然不少。關中渭水流域的竹林頗受稱道。這一帶的竹林,周圍逶迤約百餘里,西起郿縣,東到鄠杜,北至武功都有竹樹,甚至鳳翔、天水也都有竹的生長[44]。宋朝南徙,女真入主中原。金時規定,司竹監每年採竹50萬竿為防河工程的材料[45]。前面曾經說過,元代曾在京兆、鳳翔以及懷、孟等州設定官吏,管理竹園,還規定所產之竹可以發賣,當時給引竟至一萬道之多[46]。元人這樣設定措施,應該是根據宋金以來的舊規。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元人初到中原,是不會大舉興工,而且立見這樣的成效的。
元亡之後,明初仍於陝西盩厔縣設司竹局,以徵收課稅。這時竹園規模雖已狹小,然直至明代後期,竹林卻仍相當繁茂[47]。迄至清初,猶未稍減[48]。就是到1949年時,西安城中作竹器的手工業仍然聚集在一條街道。這條街道就稱為竹笆市。竹器的材料乃是產自周至戶縣和華陰華縣[49]。此外河南省產竹的地方,仍然是輝縣[50]和沁陽、濟源等縣[51],而山西平陸縣的竹林,也有名於一方。
這些竹林也有毀廢之時。淇園之竹自來都是有名當世的,可是到酈道元撰《水經注》的時候,竟然是“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52],元時懷、孟兩州的竹課是當時重要的稅收,竟然也因“頻年砍伐已損,課無所出”[53]。而盩厔縣的竹園,至明中葉時,也因產竹逐耗,不能不募民種植[54]。就是山西平陸縣的竹園,也因三門峽水庫的興修,而完全淹沒。這些變化顯而易見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酈道元所見到淇川無竹,而未指出無竹的原因。淇川和清水源頭相距鄰邇,若淇川無竹是由於氣候的變化,奈何清水源頭竟未受到影響。可見這並不是出於自然的因素。正是由於自然環境沒有什麼改變,在原來的人為原因消失之後,經過重新培植,就能恢復舊日的規模。也有的因為經濟利益不大,就任其廢棄下去。這樣不再作為經濟林木而加以培植,就更說不上從它的存廢有無來探尋當時氣候變化的過程了。
由此可見,歷史時期黃河流域竹的生長除了一些人為的作用外,一直沒有間斷。溫暖時期如此,寒冷時期也是如此。既然溫暖時期和寒冷時期都是一樣的。再以它來作為例證說明不同時期氣候的變化,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甚而竟是徒勞的。
四、兩漢以迄南北朝時期的氣候轉寒
由上面的論述,可知自西周後期氣候轉暖之後,歷時還是相當長久的。這樣的溫暖時期一直延伸到戰國末年。孟子[55]和荀子[56]所著的書中都曾提到黃河下游,今山東、河北等處,一歲再熱。而《呂氏春秋》所說的菖始生之時,較現在為早[57]。這都是竺可楨所曾經引用和論證過的。可見戰國末葉,氣候還是相當溫暖的。
可是到了漢代,氣候又有了變化,由溫暖轉向寒冷。這由當時種麥時節可以得到證明。麥是主要農作物之一,所以種麥時節很受注意。《禮記》裡面有一篇《月令》,是專記節氣的篇章。這篇書是從《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抄出來編成的,應該看成《呂氏春秋》舊有的作品。根據《呂氏春秋》的記載,仲秋之月,就勸人種麥,不要失時,如果失時,就是有罪了。出之於西漢人士之手的《尚書大傳》也說,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58]。這是一句比較費解的話,虛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是屬於北方玄武之宿的一宿。這一宿在八月裡黃昏時在天正中。也就是說種麥應該在八月。古代曆法的推算有時候會發生差錯,在農家看來,說月份不如說二十四節氣來得準確。西漢末年氾勝之曾經說過,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並且說,種得早了,就容易生蟲,種得遲了,不僅穗子小而且顆粒少[59]。這是說夏至後七十日種麥算是最合適了。夏至後七十日,已近於白露。東漢時,崔寔作《四民月令》,他把麥田分成薄田、中田和美田三種,白露節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再後十天種美田[60]。賈思勰又把種麥的時間分成上時、中時和下時。他說八月上戊社前為上時,中戊前為中時,下戊前為下時[61]。這種說法和氾勝之、崔寔差不多。《氾勝之書》撰於長安。崔寔為涿郡安平人(安平今仍為河北省安平縣),曾作過五原太守(五原郡治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賈思勰為齊郡益都人(益都在今山東益都縣東北),曾為高陽郡太守(高陽郡治在今山東淄博市臨淄西北)。他們的書中所說的當然都是黃河流域的情形。現在山西省西南部和陝西省西安市的種麥季節主要在白露和秋分之間。俗諺說:白露種高山,秋分種平川。這和《四民月令》所說的差相彷彿。如果和《氾勝之書》相比照,西漢時種麥還要早些。《氾勝之書》明確指出,種得早了,容易生蟲。可是它所定的種麥日期還在白露之前,可見當時氣候已經轉寒。
近人論西漢氣候,認為尚屬於溫暖時期,就以《史記·貨殖列傳》所說“蜀漢江陵千樹橘;……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為證,並指出橘、漆、竹皆為副熱帶植物,漢時既能在陳、夏、渭川栽種[62],這些地區的氣候當然是溫暖了。按:黃河流域在所謂溫暖時期和寒冷時期都有竹的種植,前文已有論述,可見竹是不能作為黃河流域氣候變化的證據的。不僅竹是這樣的,橘和漆也是一樣的。這裡先來說橘。西漢時,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曾經說過:“盧橘夏熟,黃柑橙榛[63]。”這是司馬相如對於長安城外上林苑中景物的描述。後來到唐時,李德裕撰《瑞橘賦》也曾說過:“魏武植朱橘於銅雀,華實莫就[64]。”銅雀臺在鄴,鄴為今河北省臨漳縣。這兩條不同的事例,就被用作西漢和曹魏氣候不同的證據。可是也還有和《上林賦》所說的相反的記載。《三輔黃圖》說:“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本注:宮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林異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柑橘皆百餘本。上木,南北異宜,歲時多枯瘁。”兩者所記,殊不相同。移植異木,自是一時盛事。所植在上林苑中,司馬相如作賦,也必然會據以描述。後來沒有成活,就和司馬相如無關。充其量也只是和後來的鄴宮一樣,似難說曹操時就較漢武帝時為寒冷。固然,在司馬相如之後,東漢張衡撰《南都賦》時也曾說過:“穰橙鄧橘[65]。”東漢南都在今河南省南陽市,穰縣在河南鄧縣,而鄧縣在今湖北省襄陽市。這幾處地方都在江陵之北。可以作為橘樹北移的途徑。但南都、穰、鄧畢竟距江陵較近,似不能以之證明長安和鄴城的氣候。唐代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66]和宋代樂史在《楊太真外傳》中[67]都曾經指出:唐玄宗天寶年間蓬萊宮殿前栽種柑橘,並結得果實事。李德裕《瑞橘賦》也說過:唐武宗時,宮中還栽種橘樹,並結得果實。李德裕為武宗首輔,段成式亦唐代人,樂史較後,生於宋初。目睹耳聞,皆當有據,非同虛妄。然這些只能證明唐時氣候的溫暖,不應以之上論西漢時的變化。至於漆樹,司馬遷之後,崔寔亦曾道及。《四民月令》說:“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所說種漆之地還應在陳、夏之北。可是曹魏時何晏撰《九州論》,卻明白指出:“共汲好漆[68]。”共,今為河南省輝縣,汲,今為河南省衛輝市,皆在陳、夏之北。曹魏為寒冷時期,黃河以北的共、汲就有漆樹,因而就不應再以“陳夏千畝漆”來證明漢時的氣候尚在溫暖時期。
曹操在鄴城銅雀臺所種的朱橘未有華實,自是漢魏之際氣候寒冷的證據。接著廣陵故城之下的一段邗溝水道結冰,也確是前所未有的大事。這宗事發生在魏文帝黃初六年(公元225年)。這一年十月,魏文帝為了征討吳國,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可是就在這一年,天氣大寒,水道結冰,船隻不得入江,因而退兵引還[69]。近人引用這條記載,多有誤釋處,難免與事實不符。不妨在這裡略作說明。這裡所說的廣陵故城,相當於今江蘇省揚州市。曹魏雖移廣陵郡於今江蘇清江市。然既明言故城,就不是位於今清江市的廣陵城。這一次行軍是以舟師自譙(今安徽省亳縣)循渦水入淮,從陸道到徐縣(今江蘇省泗洪縣),然後再至廣陵故城。為什麼改行陸道?是因為淮水以南廣陵郡城和廣陵故城之間有一段水道不通,幾千只戰船皆停滯不得行。由於蔣濟的努力疏浚,才得繼續前進,一直進到精湖以南。後來退軍回來,由於精湖以北水淺,蔣濟再沒法疏浚,才得全軍歸來[70]。精湖在今江蘇寶應縣南,今猶稱為津湖,蓋音近易訛。精湖以南,距江已不很遠。這一段水道當是邗溝的蹤跡。所謂水道結冰,當指這一段水道而言。這段水道不如淮水的深廣,是可能容易結冰的。由於這段水道結冰,魏國的舟師才不得入江。論者引用這條史料,卻認為結冰的水道竟是淮水。如果是淮水水道結冰,何須蔣濟疏浚淮南水道?舟師又何能進到精湖以南?如果是淮水冰凍,當然也可以說是一次氣候的變化,但與精湖以南至於江邊的水道結冰相比,其意義就顯得有所差距,甚至不必作為重要的事例,特別提起。
這次在廣陵故城附近的水道結冰,雖是曹魏開國未久的事故,可以和後來南朝在建康覆舟山下建立冰房事相聯絡,可知這一時期寒冷季節的悠長。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南京結冰是少見的。南朝為了藏冰而特建了冰房,也是以前少有的。竺可楨舉出這宗事情來說明當時氣候的特點,饒有意義。
南北朝時氣候寒冷的事例,還可舉出北魏賈思勰在所著的《齊民要術》對於當時果木樹的記載。據賈思勰的記載,當時黃河流域杏花在三月始盛開,而棗樹生葉和桑花凋謝在四月初旬。當時的三月約當現在陽曆四月中旬,其四月初旬應為現在五月上旬。顯然可見,當時這些果木樹的出葉和花開花謝還較現在為遲。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冬季對於石榴樹的保護。當時石榴樹越冬,須用蒲藁裹而纏之,不然就要凍死。這在現在黃河下游也是未曾有過的現象。這宗事例和南朝在建康建立冰房事分別見於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雖說都屬於孤證,卻是應予重視的。
五、隋唐兩代氣候轉暖時期
氣候再次轉為溫暖,是在隋唐時期。但早在南北朝後期已有相當的徵象。遠在殷商時期,黃河流域曾經有過關於象的記載。下迄秦漢之時,這種記載竟至闕如。這裡面的原因還需要從長研究,可能也與氣候變化有關。秦漢時期人口增多,土地利用日廣,象也許多藏於森林之中。由於氣候的轉寒,象也就逐漸向南遷徙,故黃河流域就不復再見象的蹤跡。可是到了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南兗碭郡(今安徽碭山縣)卻發現了巨象[71]。這樣的巨象顯然並非當地土產,因而當地人引為奇事,捕獲後送於鄴城。碭郡位於淮北,距淮水並非甚遠。這隻象恐也不是淮水流域所產。如果是淮水流域的象,則北來到了碭郡,當不至於認為奇事。象的北來正可說明淮北氣候已漸轉暖,故自然流竄至此。
隋唐時期氣候轉暖,當時關中梅花盛開,移種的橘樹還能結出果實,都是具體的例證。唐代長安宮中種植橘樹,這是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唐代詩人對於關中的梅花多有題詠[72],當非杜撰之辭。這樣的事例是近人論證隋唐時期氣候時皆有所徵引的。不過這裡還有些問題需要澄清。近人論西周春秋時期的氣候,皆以其時黃河流域能有梅樹作為溫暖的證明。而論證隋唐時期氣候的又復溫暖,其例證還是梅樹。這兩個溫暖時期之間,還夾有一個相當長久的寒冷時期。在這樣寒冷的時期,黃河流域當然沒有梅樹了,既然黃河流域沒有梅樹,隋唐時期又怎麼繁盛起來?東漢時,張衡在所撰的《南都賦》裡曾說過:“櫻梅山柿。”這是說當時南都有過梅樹。所謂南都,乃指宛城而言,也就是現在河南省南陽市,南陽市不屬於黃河流域,卻近於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氣候轉暖的時候,梅花就由附近地區繁植移種過來。
隋唐時期的溫暖氣候,直到宋初,尚無很大差異。據《宋史》記載,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黃陂有象自南來食稼;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有象入南陽,虞人殺之[73]。黃陂縣今為武漢市黃陂區。南陽即今河南省南陽市。前面說過,南北朝末年,碭郡曾經發現過象。碭郡治所在今安徽碭山縣。南陽、黃陂兩縣皆在碭山縣之南。距黃河流域更非附近,亦可顯示當時仍然相當溫暖。當時如果氣候已經轉寒,象是不會遠至這些地方的。
六、隋唐以後各時期氣候寒溫的變化
宋代的氣候還是轉向寒冷的。黃河流域再度不栽種梅樹就是明顯而重要的證據。蘇軾詠杏花詩所說的:“關中幸無梅,賴汝充鼎和。”王安石詠紅梅詩所說的:“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蘇軾這首詩作於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74]。上距黃陂見象正為百年。蘇軾為蜀人,其初至東京開封為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75]。王安石北來,略早於蘇軾,其間相差也不過幾年[76]。在這前後百年上下,北人竟已不認識梅花,可知其間變化還是相當巨大的。這裡還可再舉郭璞和邢昺的《爾雅》註疏為證。《爾雅·釋木》曾舉出梅樹。郭璞注:“似杏實酢。”邢昺無疏。郭璞為晉時河東聞喜人,邢昺為宋時曹州濟陰人。聞喜,今仍為山西聞喜縣。濟陰,今為山東菏澤市。蓋均為北人,宜其難得說得具體。由郭璞作注,更可以知道晉時北方已無梅樹。宋時不僅黃河流域無梅樹,就是東南沿海的荔枝樹,也曾不止一次被凍死[77]。長江下游的太湖,湖面廣闊,為東南大澤,也曾經全部冰封,洞庭山上的柑橘樹同樣被凍死[78]。就是江南的運河,也不止一次結冰[79],這都應是前所未有的氣候變化。
到了元代初年,論者根據邱處機所作的《春遊》詩。指出氣候又趨於暖和,這首詩中有句說:“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80]。”現在杏花也在清明時節開放,可知當時的氣候和現在相彷彿,已較為轉暖。邱處機這首詩撰寫於公元1224年,這一年是成吉思汗十九年,宋寧宗嘉定十七年。證明元代氣候轉暖的文獻,目前所可知者僅這一點。雖屬孤證,然以得之於目睹親見,當非虛妄。自然景象,也不是偶然作為,因而是可以徵信的。近人論元代氣候的溫暖,皆以當時黃河流域竹林為證。竹的有無不足以證明氣候的變化,已見前文,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不過這樣的溫暖時期並未繼續很久。就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已經有了江南運河結冰的記載[81],接著太湖又連續封凍,柑橘樹也被凍死[82]。溫暖時期就這樣再度轉入寒冷期。這樣寒冷的氣候一直持續到明清兩代。據竺可楨所徵引、明清兩代最有說服力的證據,當數到明代袁小修所寫的《日記》和談遷所撰的《北遊錄》。袁小修《日記》曾記錄明萬曆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公元1608-1619年)湖北沙市附近的氣候。據所記錄,則當時沙市春初的物候較現在武漢市物候約遲7天到30天。《北遊錄》則記載談遷於清順治十年至十二年(公元1653-1655年)往來於杭州及北京間的經歷。據其所記,則當時北京的物候也較現在約遲一兩星期。袁談兩家撰述的時候,前後相差50年上下,華中和華北兩地區的氣候大致相彷彿,皆較遲於現在,這當非偶然的現象。談遷由杭州赴北京,乃是乘舟前往,在經過天津至北京一段路程時,運河冰凍,不能不改乘車輛。按照所記的日程推算,運河封凍期間竟多達107天。這段運河迄至現在,冬季也是會封凍的。不過據1930年至1949年的記錄,平均封凍日期只有56天,其間相差是很懸殊的。就是春季開河的日期,清代初年也要較現在遲12天。根據這樣的記載,應該說:明清兩代的氣候是轉為寒冷時期的。
由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從人類最初能從事生產活動時起,一直到現在的幾千年間,氣候時有變化。遠古的溫暖時期較為長久,秦漢以後,變化就較為頻繁。愈到後來,寒冷時期卻顯得較長。這樣溫暖和寒冷時期的變化,只是從若干年月和具體事例顯現出來的。應該說,氣候的變化不僅在較長的時期有所顯現,就是短暫的年月中也不是不可能體驗出來的。歷代史籍中的五行志就曾記載著酷寒、燠暑、早霜、嚴冰,這樣的事例甚至是頻繁有過的。但這只是一時的現象,難得作為一個時期顯著變化的根據。
七、氣候乾溼的變化
歷史時期不僅氣溫的寒暖有所變化,就是乾溼同樣也是會顯出變化的。近年來不斷髮現古代遺留下來的孢粉。根據這樣的孢粉,不僅可以測定原來植物存在的年代,還可以測定當時溼潤狀況。根據學者的探索和研究,距今五六千年前,與溫暖的氣候同時,為一相當溼潤的氣候[83]。其後由溼潤的氣候轉變為乾旱氣候。但到了距今2500年前,氣候又稍顯得溼潤,這不僅由孢粉的測定得到證明,也是和文獻記載相符合的。
前面說過,古代黃河流域是曾經有過許多湖泊的。這些星羅棋佈的湖泊應該會對氣候起著調節的作用。古代黃河流域正因為這些湖泊,所以顯得相當溼潤,至少沒有現在這樣的乾燥。因為溼潤的關係,所以一直到春秋時期,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下游的人們還是喜歡住在丘陵地區。據說齊景公尊重晏嬰,打算替他另起一座新的住宅,說是舊宅湫隘,新宅爽塏[84]。在現在說起來,山東地方正是爽塏的地方,如果古代和現在一樣,那麼,晏嬰的住宅就不必勞齊景公替他另行建築了。再以現在山西西南部來說,這是春秋時期晉國的土地。論起地勢來,應該比山東還要高亢。春秋時期晉國曾經打算遷都,有人主張遷到郇瑕氏的地方,這裡有鹽池的利益,應該是不錯的。可是另外一位大臣韓獻子卻提出異議,說是郇瑕氏地方土薄水淺,住得久了,人們是會容易生災生病的。晉國的臣子們考慮的結果,認為韓獻子說得不錯,所以就沒有向這裡遷徙[85]。由其他記載看來,韓獻子的話卻不是正確的。因為《詩經》中《魏風》裡面就已經提到汾水附近有沮洳的地方[86]。既然是沮洳地就很難得高亢爽塏了。
這樣溼潤狀況由當時森林的分佈,也可以得到證明。應該說,溼潤的氣候促進了森林的生長髮育,而茂密的森林也顯示出氣候的溼潤程度。2500年前,黃河流域森林相當繁多,分佈的地區也相當廣大。這就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奇怪,因為有些樹種現在已不再見於黃河流域,有些森林分佈地區已經沒有什麼樹木,因而認為是難以置信的。當時的氣候既是溫暖而又溼潤,為什麼不能生長那麼多的樹木和森林,而所生長的地區又復那麼廣大?如果以現在的情況忖度以前,怎麼不會有這樣的疑問。這樣溼潤的氣候後來又再次變幹。據說這個變乾的界線出現在距今700年。這已經是元代初年了。這是據古蓮子經過C14年代測定所得的結論。這樣的結論在文獻記載中同樣可以得到驗證,因為黃河流域的森林繁盛茂密的程度,並未有過多的減低。當然,人為的摧殘是不應該計算在內的。
溼潤和乾旱的變化雖是時有顯現,但持續時期的長短,卻也不盡相同。經研究證明,如果以公元1000年作為界線,把前後分成兩段,則在這一年以前,乾旱時期持續時間短,溼潤時期持續時間長。這一年以後,溼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近400年中,黃河流域旱災的發生比較頻繁,就是證明。如前所說,黃河流域的森林在距今700年還是相當繁盛茂密,近四五百年,森林地區有顯著的縮小,這固然是由於人為作用的破壞,但乾旱時期的持續時間較長,也不能說就無影響。
由此可見,歷史時期氣候是有過變化的,而且相當頻繁,並非短暫稀少。論述氣候的有關影響,是應該以當時的氣候作為依據的。以今論古或以古論今,都是不恰當的。
注 釋
[1]龔高法等《歷史時期我國氣候帶的變遷及生物分佈界限的推移》。
[2]《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時期的氣候變遷》。
[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1963年。
[4]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田獵與漁》。
[5]華北地質研究所《黑龍江省呼瑪縣興隆第四紀晚期孢粉組合及其含義》。
[6]周昆叔等《察右中旗大義發泉村細石器文化遺址花粉分析》,刊《考古》1975年第1期。
[7]周昆叔等《天山烏魯木齊河源冰川和第四紀沉澱物的孢粉學初步研究》,刊《冰川凍土》1981年第3號。
[8]郭旭東《珠穆朗瑪峰地區第四紀間冰期和古氣候》,徐仁、孔昭寰等《珠穆朗瑪峰地區第四紀古植物學研究》,刊《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1966-1968)·第四紀地質》,1977年。
[9]《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索隱》。
[10]按: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原注:牛馬死,是年,厲王生。《御覽》八十四引《史記》: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11]《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
[12]《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
[13]《左傳》僖公四年。《史記》卷四《周本紀》。
[14]《太平御覽》卷八四引《帝王世紀》:“昭王在位五十一年。”《外紀》同,又引皇甫謐曰:“在位二年。”《今本竹書紀年》:“昭王十九年,王陟。”按:《古本竹書紀年》於昭王十九年後即再未有記事,則昭王在位當以十九年為是。
[15]《尚書·說命下》:“若作酒醴,爾唯麴櫱;若作和羹,爾唯鹽梅。”《說命》為殷高宗時所作,可見其時梅的栽培已相當普遍。
[16]有關這些樹木在當時繁殖的文獻記載,已徵引在《植被的分佈地區及其變遷》中,這裡不再贅述。
[17]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18]賈蘭坡、張振標《河南淅川縣下王崗遺址中的動物群》。
[19]《左傳》文公十八年,襄公十八年。
[20]《史記》卷八〇《樂毅傳》。
[21]《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22]《史記》卷二九《河渠書》。
[23]《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
[24]《後漢書》卷三一《郭伋傳》:“伋為幷州牧,……始至行郡,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美稷縣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兒童數百皆有竹馬可騎,可能當地就有竹林。不過有謂其時竹馬已經成為定稱,不一定都是取用竹竿。唐時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記他從五臺山起程赴長安時說:“為往長安,排比行李。……齋後便發,……取竹林路,從竹林寺前向西南。”尋此文意,五臺山下當有竹林,不然竹林路和竹林寺就無所取義。又考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一〇《支植》:“衛公(李德裕)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唐北都為今山西省太原市。太原種竹如此艱辛,五臺山如何能有竹林,美稷縣如何能有製作竹馬的竹?書此志疑。
[25]《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京兆下》:“司竹園,在(鄠)縣東十五里,園週迴百里,置監丞掌之,以供國用。義寧元年,義師起,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舉兵於司竹園。”
[26]《全唐詩》卷二二五,杜甫《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九:“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又之十三:“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又之十六:“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同。……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
[27]《全唐詩》卷二一二,高適《自淇涉黃河途中作十三首》之四:“南登滑臺上,卻望河淇間,竹樹夾流水,孤城對遠山。”
[28]《元史》卷九四《食貨志》。按:《食貨志》說:“腹裡之河南、懷、孟”,中華書局本《元史》對於這句有校語說:“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中書省統山東西、河北之地,謂之腹裡。河南府不屬腹裡。此‘河南’或系‘河間’之誤。”按:《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下八》:“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泊稅不及百錢蠲之。”滄州治所在今河北滄州市,濱州和棣州治分別在今山東省濱縣和惠民縣。竹木之稅他州俱無,僅這三州有之,當系其地產竹。元時並滄州於河間府,是河間府亦產竹。校語改腹裡河南為河間,應該說是有道理的。不過元時河南省亦有竹課。《元史·食貨志》:“竹木課:腹裡,竹二錠四十兩,額外竹一千一百錠二兩二錢。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又“竹葦課:奉元路三幹七百四十六錠二十七兩九錢”。河南省的課稅雖沒有奉元路那麼多,卻遠超於腹裡懷、孟等州。元河間路治河間縣,今河北省河間市。奉元路治長安縣、今陝西省西安市。
[29]《文選》卷一。
[30]《文選》卷二。
[31]《初學記》卷二八《竹部》引。
[32]《文選》卷六。鄴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洹水流經今河南省安陽市,東入白溝。白溝即曹操引淇水所修鑿的人工水道。
[33]《文選》卷一六,潘安仁《閒居賦》。
[34]《晉書》卷三一《胡貴嬪傳》。
[35]《文選》卷一〇,潘安仁《西征賦》。
[36]《水經·清水注》。
[37]《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
[38]《水經·清水注》。按:《水經·沁水注》:“上澗水導源西北輔山,……歷析城山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於王屋也。……下有二泉,……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於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流上下,步徑才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蘢茂密,奇為翳薈也”。這樣的小竹細筍應為竹的一類。因為是小細筍,所以另著於此。析城山在今山西陽城縣西南。
[39]《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監》。
[40]《水經·淇水注》。
[41]《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
[42]《水經·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流,……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又說:“渭水逕(槐裡)縣之故城南,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於竹圃,東北流又屈西北入於渭。”
[43]《大唐六典》卷一九《司竹監》。
[44]《蘇軾詩集》卷三至卷五,編有蘇軾為鳳翔府節度判官時所作的詩多篇,其中往往提到鳳翔府所屬各處的竹林。並在一首詩下自注說:“盩厔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這裡錄在鳳翔縣的兩首:一、《李氏園》(自注:李茂貞園也,今為王氏所有):“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二、《大老寺竹間閣子》:“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葉綠,不知汧水黃。”
[45]《金史》卷四九《食貨志》。
[46]《元史》卷九四《食貨志》。
[47]雍正《陝西通志》卷七三《古蹟》引《馬志》:“斑竹園在盩厔縣東二十里,週數頃餘,隸秦府。內植斑竹,其大如椽,其密如簀。”按《馬志》纂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
[48]雍正《陝西通志》卷四四《物產》引《盩厔縣誌》:“植竹,竹皆成斑,其大如椽,其密如簀。”所引的《盩厔縣誌》,當為康熙時所修,其文雖引自馬理所修的《陝西通志》,亦可證明其時這片竹林仍然存在,並未殘毀。
[49]現在西安城是明初在唐末韓建縮小的長安城的基礎上改建的。現在一些街道的名稱可能上溯到明初建城之時,如竹笆市、木頭市、騾馬市、五味什字等都是。這些街道長期保持著和它的名稱有關的店鋪設定。竹笆市更是特別明顯。這樣的街道如果不是明初舊有的,也是多歷年所,有其淵源可尋的,1949年前後,竹笆市還有不少的製作和出賣竹器的店鋪,由竹笆市的名稱,就可證明關中一直是產竹的地區,並非是由明代後期秦藩斑竹園的廢去而了無蹤跡的。
[50]嘉慶重修《清一統志》卷二〇一《衛輝府》:“竹,舊出淇縣。《明一統志》,輝縣出。”
[51]嘉慶重修《清一統志》卷二〇四《懷慶府》:“竹,河內出。《府志》,國初貢竹,康熙年間裁免。”直至清朝末年懷慶府的竹林還是到處叢生,與其他灌木和柏林相交錯,風景優美,為過往者所稱道。產竹既多,竹器的製造自然也發達起來。近來(五十年代)報載,政府對於這一區域人民製作竹器的副業曾經加以提倡。
[52]《水經·淇水注》。
[53]《元史》卷九四《食貨志》。
[54]乾隆《盩厔縣誌·古蹟》。
[55]《孟子·告子上》:“今夫麥……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56]《荀子·富國篇》:“今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倍,一歲再獲之。”
[57]《呂氏春秋·任地篇》。
[58]《齊民要術》卷二《大小麥》引。
[59]《齊民要術》卷二《大小麥》引。
[60]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
[61]《齊民要術》卷二《大小麥》。
[62]《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漢時潁川郡治陽翟縣,南陽郡治宛縣,分別為今河南省禹縣和南陽市。《貨殖列傳》又說:“陳在楚夏之交。”其地在今河南省淮陽縣。
[63]《文選》卷八。
[64]《李文饒文集》卷二〇。
[65]《文選》卷四。
[66]《酉陽雜俎》卷一八《木篇》。
[67]《說郛》卷三八,樂史《楊太真外傳》。
[68]《太平御覽》卷七六六《雜物部》引。
[69]《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
[70]《三國志》卷一四《蔣濟傳》:“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帝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水經·淮水注》引《三州論》說:“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
[71]《魏書》卷一一二《靈徵志》。
[72]《全唐詩》卷四〇一,元稹《和樂天秋題曲江》:“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全唐詩》卷五三九,李商隱亦有以《十一月中旬至扶風界見梅花》為題的詩篇。這皆可以證明長安以至關中各處,當時都是有梅樹的。
[73]《宋史》卷一《太祖紀》。
[74]《蘇軾詩集》卷三《次韻子由岐下詩》共二十一首,《杏花詩》即在其中。按:這組詩的引文說:“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廨宇之北隙地為亭,亭前為橫池,……池邊有桃、李、杏、梨、櫻桃、石榴、樗、槐、松、檜、柳三十餘株。”蘇軾為鳳翔府節度判官為宋仁宗嘉祐六年十一月事,這組詩應作於這一年。
[75]《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嘉祐二年,試禮部。”
[76]《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
[77]李來榮《關於荔枝龍眼的研究》,1956年,科學出版社。
[78]陸友仁《研北雜誌》捲上,《寶顏堂秘笈》普集。
[79]蔡珪《撞冰行》,見元好問《中州集》卷一。
[80]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一。
[81]據竺可楨的徵引,此事見元《郭天錫日記》。
[82]陸友仁《研北雜誌》捲上。
[83]《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時期氣候的變遷》。下文論述溼潤氣候的變遷,所引證的材料亦見此文。
[84]《左傳》昭公三年。
[85]《左傳》成公六年。
[86]《詩·魏風·汾沮洳》。
來源:《歷史地理學十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