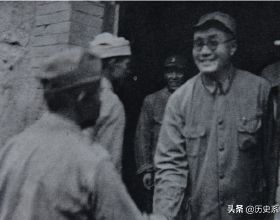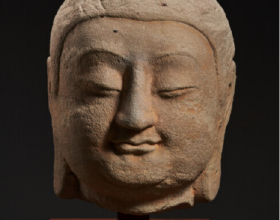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記載:1964年春,作《賀新郎·讀史》: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蹠莊 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賀新郎·讀史》最早發表於《紅旗》雜誌1978年第9期,同年9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並附毛澤東的手跡。這首詞1978年發表時所署寫作時間,是根據原在毛澤東身邊做醫護工作並曾幫他儲存詩稿的吳旭君的回憶。據她回憶,在那段時間裡,毛澤東在辦公之餘,一直在看《史記》和范文瀾寫的《中國通史簡編》。
這首詞以政治家的氣魄、詩人的才華、歷史學家的淵博、理論家的思辨縱論中國歷史,勾畫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藝術圖景,是對中國歷史的史學思考和哲學概括。這首詞筆墨縱橫,氣象恢宏,意境深遠,風骨雄健,是毛澤東詩詞中別具一格的作品,堪稱毛澤東晚年詞作中的壓卷之作,被譽為詠史詩詞的“千古一篇”“千秋一闋”。
讀史:一篇讀罷頭飛雪
毛澤東嗜書不倦,終生以書為伴。他常說,讀書治學沒有什麼捷徑和不費力的竅門,就是一要珍惜時間,二要勤奮刻苦。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以一日不讀。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期間,他抄錄(有改動)一副對聯:貴有恆,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930年2月,毛澤東在江西省吉安縣渼陂村“名教樂地”書院住過一段時間。其屋內照壁上寫有一副楹聯:“萬里風雲三尺劍,一庭花草半床書。”古人讀書講究“三上”,即枕上、廁上和馬上。毛澤東睡的床與眾不同,差不多有兩米寬,睡一小半,剩一大半擺書,擺滿了各種書籍。無論是長征途中,或是槍林彈雨中,還是走路、騎馬、坐在擔架上,毛澤東都會背誦古人詩文或者推敲自己的詩詞。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很豐富,除此之外,他還經常到一些圖書館借書。1958年,北京圖書館為毛澤東辦理了第1號借書證。另外,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廬山等地的圖書館都留有毛澤東的借書記錄。據不完全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9月,他先後從北京圖書館等單位借閱的圖書達2000餘種、5000餘冊。至1975年時,毛澤東已病魔纏身,眼睛又做了白內障摘除手術。醫務人員勸他暫停看書,他根本不聽,醫務人員只好為他設計了一副特殊的單腿眼鏡。當他右側臥看書時,戴沒有右腿的眼鏡;當他左側臥看書時,則戴沒有左腿的眼鏡。《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記載:1976年9月8日,“在接受搶救,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孔插著鼻飼管的情況下,全天由工作人員託著檔案或書閱看十一次,共二小時五十分鐘。最後一次看檔案是下午四時三十七分,看了約三十分鐘。夜,處於彌留狀態”。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毛澤東與世長辭。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學到老。
1949年5月7日,在《學習毛澤東》的演講中,周恩來指出:“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在浩如煙海的圖書中,他最偏愛的是文史古籍。從先秦到明清不同歷史時期的著作,包括正史類、稗史類、演義類、文學類……幾乎無所不讀。一部3000多卷、4000多萬字的線裝本《二十四史》,他幾乎不離身邊,反覆閱讀。一部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鑑》,他竟看了17遍。
趙以武主編的《毛澤東評說中國歷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書,提供了一份除《二十四史》《資治通鑑》以外,毛澤東讀過的史書清單:《通鑑紀事本末》42卷、《續通鑑紀事本末》110卷、《宋史紀實本末》109卷、《元史紀實本末》27卷、《明史紀實本末》80卷、《十六國春秋》102卷、《戰國策》32篇、《東觀漢記》輯佚本24卷。另外,毛澤東還閱讀過比如《讀史方輿紀要》《華陽國志》一類的地理、地方誌書籍,以及今人史著,比如郭沫若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也是經常放在手頭,要隨時取來選讀的。
1964年《文史哲》雜誌發表了山東大學教授高亨的詞作《水調歌頭(掌上千秋史)》,其中“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一句,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毛澤東濃郁的歷史情結和史家氣質。由於他熟讀史書,在文章、報告、談話和詩詞中,能夠將史料掌故信手拈來。以《毛澤東選集》為例,他旁徵博引了大量歷史典籍,如《左傳》《呂氏春秋》《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禮記》《易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孫子》《列子》《山海經》等。涉及的歷史人物,既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學者、詩人,比如曹操、孫武、司馬遷、韓愈、朱熹等;又有佞臣奸相,比如魏忠賢、李林甫、劉瑾、秦檜等。對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比如陳勝、吳廣、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毛澤東則傾注著更大的熱情與關注。對於中國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戰役,比如楚漢的成皋之戰、新漢的昆陽之戰、袁曹的官渡之戰、吳蜀的夷陵之戰、秦晉的淝水之戰等成敗得失的評述,也都多次出現在他的著作和講話中。
詠史:但記得斑斑點點
詠史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步入詩壇,始於東漢班固《詠史》一詩。南北朝梁朝昭明太子蕭統在《文選》“詩類”中專列出“詠史詩”一部,輯錄了9家21首詠史詩。自此,詠史詩正式成為標註詩類的一個專業術語。毛澤東博古通今,很多詩詞作品引經據典、談古論今,寫下了許多純粹的詠史詩詞作品,而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賀新郎·讀史》。
《賀新郎·讀史》的上闋以形象比喻解讀了人類社會的歷史,主要是中國社會的歷史。“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寫人類的起源和人類歷史上最初出現的原始社會。人和猿相互拱手作揖告別,人學會用石頭磨製生產工具,進行勞動,那是人類的童年時代。“人猿相揖別”,精煉寫出從猿到人的進化過程。“揖別”兩字極為傳神,手筆奇特而幽默,舉重若輕地道出了其中的區分。而人與猿“揖別”的根本標誌,就是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人類經歷了兩三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生產力低下,故稱為“小兒時節”。
“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寫的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銅鐵爐中翻火焰”,生動地寫出了人類冶煉銅鐵和製造青銅器、鐵器的壯麗情景。我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究竟始於何時,學術界眾說紛紜,所以詩人說“為問何時猜得”。但不管怎樣“猜”,這兩個時期也不過幾千年罷了,於是作者用“不過幾千寒熱”對此作了說明。“寒熱”,是冬去春來,歲月嬗變。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這是對中國幾千年階級鬥爭歷史的概括。“人世難逢開口笑”,化用唐朝杜牧《九日齊山登高》的“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之句。進入階級社會,世間多有不平之事,苦樂不均,貧富不等,對立階級之間不可能笑臉相迎。“上疆場彼此彎弓月”,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彎弓張弩,刀兵相見。其結果是“流遍了,郊原血”,干戈鏗鳴,血染大地,屍橫遍野。正如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所說:“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詞的下闋夾敘帶議,批判歷史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謳歌人民群眾推動歷史發展的唯物史觀。“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首先點明《讀史》這個題目,同時也生動說明舊史的浩繁難讀,讀到頭白年衰,也難以窮盡。“一篇讀罷頭飛雪”,既是中國史籍博大精深之寫照,也是毛澤東終生酷愛讀史之刻畫。
“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這是對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舊史書的大膽嘲諷和徹底批判。“五帝三皇”即“三皇五帝”。三皇,一般指天皇、地皇和人皇;或指燧人、伏羲和神農。五帝,一般認為是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和虞舜。其實“三皇五帝”都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人物,但一些史家把他們說成是真正的歷史人物,並將有關傳說當成正史,說他們是歷史上最有才能最賢明的君主,最神聖的英雄。於是乎“騙了無涯過客”,矇蔽了古往今來無數人。
“有多少風流人物?”風流人物是指在歷史上對一個時代有重大影響的英雄人物。宋代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句。“盜蹠莊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蹠是春秋時魯國人,奴隸起義的領袖,被古代統治階級誣衊為“盜”,後來襲稱盜蹠。莊是戰國楚懷王時的農民起義領袖。“流譽後”是指其美名一直流傳於後世。陳王則指陳勝,公元前209年,他和吳廣共同領導秦末的農民起義,“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黃鉞則是飾以黃金的大斧,是建立政權的象徵。“揮黃鉞”表達了毛澤東對農民起義的讚美之情。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只有這些奴隸和農民起義的領袖,才是真正的風流人物,才是真正的英雄。
“歌未竟,東方白”,詠史之歌尚未唱完,東方已經發白。唐代杜甫《東屯月夜》有“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李賀《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詩云:“葛衣斷碎趙城秋,吟詩一夜東方白。”結尾二句,語意雙關,意味深長。從實寫的角度看,指作者自己徹夜讀史,直至天明。從象徵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為階級鬥爭的歷史之歌尚未唱完,中國革命已經大功告成。“東方白”與毛澤東《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雞天下白”一樣,都象徵中國革命取得勝利。
評史:推翻歷史三千載
宋代嚴羽《滄浪詩話》雲:“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賀新郎·讀史》具有極強的概括力,僅用區區115個字,便囊括以中國歷史為主體的、跨度幾百萬年的人類社會發展軌跡。作品縱觀古今成敗,歷覽先賢得失,集述史、抒情、議論於一體,一詠三嘆。誰是真正的英雄?誰是歷史的創造者?是人民群眾還是英雄豪傑?這些問題是唯物史觀的重大問題。貫穿《賀新郎·讀史》全篇的深邃哲理是:勞動創造人類的觀點,階級鬥爭的觀點,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這首詞堪稱是毛澤東歷史觀的詩詞化表達。而該詞最突出的特點,是目光深邃、思想深刻、見解獨絕、振聾發聵,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閃耀著睿智的光芒。“推翻歷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柳亞子昔日稱讚毛澤東的兩句詩,用來評價《賀新郎·讀史》恐怕是再恰當不過了,可作千秋定評。
毛澤東多次引用《孟子·盡心下》中的一句話:“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讀書時提倡“四多”,即讀得多、想得多、寫得多、問得多。他特別強調學思結合,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學而不思則罔”。毛澤東不但勤於讀史,而且善於思考,從不盲從盲信史書。埃德加·斯諾所著的《西行漫記》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描述了毛澤東讀私塾時的情況:“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儘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這一發現,對毛澤東後來的農民觀和歷史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賀新郎·讀史》中最令人費解的一句,是“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毛澤東具有深厚的國學修養,他不可能不瞭解有關“三皇五帝”的故事與傳說,也不可能不清楚歷代史家對他們的評說與讚譽。司馬遷《史記》第一篇是《五帝本紀》,以“五帝”作為中國歷史可以上溯的最早記錄。但司馬遷沒有為“三皇”立一篇本紀,只是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透過君臣議論帝號時提及過。黃帝在打敗了原先統治諸侯的神農氏炎帝,平定了諸侯中反叛作亂的蚩尤以後,才被尊為天子的。黃帝之後的其他帝王,包括後來的夏、商、周的統治者,都是黃帝的後代。這樣一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就以黃帝及先前的炎帝作為源頭了。直到今天,中國人還在自豪地以炎黃子孫自稱。
毛澤東詩文裡引用的一些典故,涉及上古“三皇五帝”的神話傳說。他在1935年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談及長征時,就有“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的說法。1930年春寫的《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不周山下紅旗亂”用到了共工與顓頊爭奪帝位的傳說。1937年3月,他起草的《四言詩·祭黃陵文》中,有“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這樣的讚語。1958年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億神州盡舜堯”句提到了堯帝、舜帝。1961年寫的《七律·答友人》中,“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等詩句,都化用了舜帝的兩個妃子娥皇、女英至蒼梧追尋舜帝的典故。在這些詩文中,毛澤東提及“五帝三皇”,既有時事政治的需要,有修辭造句的需要,也有形象思維的需要。而“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本質上是否定“五帝三皇”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認識史前史的科學結論。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不能將其混為一談。
毛澤東堅信是勞動創造了人,是勞動人民創造了歷史,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而不是“五帝三皇”的作用和功勞,不能僅僅滿足於熟悉那些“斑斑點點”“幾行陳跡”的記載。《新華文摘》1994年第2期所載盧荻所著的《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一文描述,1975年毛澤東同盧荻談二十四史時說道:“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去讀了,那是形而上學。”毛澤東強調必須把握歷史的特點,掌握歷史的規律,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
毛澤東在歷史中讀出了大學問,讀出了大智慧,讀出了豪情壯志,更讀出了中國革命。龔育之等所著的《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1月版)中,逄先知在《古籍新解,古為今用——記毛澤東讀中國文史書》一文中指出:“毛澤東讀古書,有一個基本觀點,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中國很多古書裡,歷代農民起義運動及其領袖人物,大都被當作‘賊’‘匪’‘盜’‘寇’,任加貶斥。但毛澤東則給他們以很高的歷史地位。”林林總總的史書籠罩著歷史唯心主義的迷霧,難以道破歷史的真諦。它們一方面為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歌功頌德,另一方面又極力貶低、醜化人民大眾。“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蹠莊 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前者是奴隸起義的首領,後者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毛澤東認為這些人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風流人物”。
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解釋《沁園春·雪》時說“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這是信奉人民史觀的必然結論。
(來源:《黨史文苑》,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