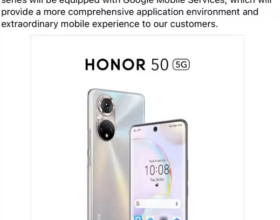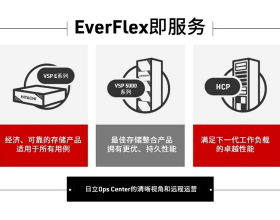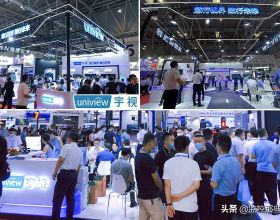《好人好夢》使我們相識、相知、相愛,演繹一曲浪漫情歌,同時也告訴人們有情人未必要成眷屬。
我叫她惠,她叫我壞。
一 曲 定 情
惠是省城一所知名大學的助教。她曾有一個幸福的家,丈夫是一家證券公司的副總,整天忙乎於股票指數技術分析。讀小學的兒子是她唯一的寄託。惠是已離休的南下老軍人的小女兒,掌上明珠,幾個哥哥和她都當過兵。惠是部隊文工團的臺柱,復員後又考上大學,畢業分配結婚成家育兒走完一個女人平凡的重複生活,如涓涓流水平靜不息。
我和她相識是在三年前的平安夜。那夜寒潮驟至,寒風凜冽格外冷。我獨自在蝴蝶夢音樂廳,面對紅燭晃動,喝著檸檬奶茶,聽著輕音樂。那是多年來第一次這麼輕鬆,我在一家外資公司任老總,常常忙得沒有白天黑夜,愈到那些洋人的節日就愈不得閒。這次洋老闆提前回去述職過聖誕,公司就放了假。我不願回到冷冷清清的宿舍,吃完飯就早早來這兒休閒。
先生,對不起,能不能挪個位置。侍者小心奕奕地問,他指著牆角那張已經坐著一位女士的小園桌,補上一句:已徵得那位小姐同意,今兒人太多,真太對不起。
那就是惠,初次見面的惠。部隊的文藝兵,秀髮飄逸,儀態萬方,給人一種朦朧美。我不好色,外資公司有的是漂亮的小姐,不過我很看重對方氣質。惠就是。很快,兩人就像熟識的久違友人般談起來,很慶幸自己的女人緣,大凡帥哥,對漂亮的女孩都會鍾情,尤其孤寂的時刻。我們唱《好人好夢》吧!惠提議,取筆在燭光下填歌單和祝詞:平安夜好人好夢,好人一生平安。
她抬頭望我的時候,眼神中閃過一絲淡淡的鬱憂。我們唱得很投入。
你唱得真好。惠由衷地。
掌聲證明;不是我,不是你,而是我們配合得自然、默契。
我糾正她的恭維。
夜深了。我為她披上大衣,送她走出歌廳大門。
我送你回去!不管惠是不是同意,就在她上車那一瞬間,我也擠上計程車車。
嘿,莫非你真敢上我家,不怕我家裡那位吃醋!
I LOVE YOU!我摟住她,緊緊地,熱唇堵住她的笑聲。沒有掙扎,沒有反抗,只有車輪壓在冰渣上的沙沙響。
良久,她喘過一口氣,推開他:你,你真壞!我笑了,笑得很得意儘管是第一次。
不過,我很喜歡你這樣霸氣的男人。惠說。
我貼近她耳邊:記住,以後,《好人好夢》只許和我唱。
惠順從地點點頭用熱吻回應。
直到下車,二成才鬆開她柔柔暖暖被捏得發燙的手。
情 深 意 切
我覺得和惠在一起最好感覺是在綠茵閣。並不是我們熱衷西餐,而是那裡鬧中取靜,環境優雅。
每每在靠落地窗的座位上,一杯法蘭西葡萄酒、一杯咖啡、一曲《梁祝》,兩人都陶醉在喋喋絲語之中。
以我的閱歷、經歷、比惠大十多歲,百般呵護,話語幽默風趣,常使聽得十分投入的惠一時為之感染而發出忘情的笑聲。噓!升會故作玄虛地制止她,並心甘情願地接受她輕輕地嬌嗔的一錘。你壞,你真壞!
惠說,我好多同學戰友都有情人,感覺好極啦!
同學,是女同學嗎?我明知故問。
男人有情人天經地義,女人擁有情人卻讓人感覺怪怪的。
不過,事情得想回來,在這人問題上如果沒有紅杏出牆,男人上哪兒去尋覓知音——恨不相逢未嫁時,是大多女人的嘆息。
你是我的情人!惠宣佈。我喜歡你,喜歡你講話神采飛揚、喜歡和你在一起幽默而富有浪漫的情調,喜歡你寵著我依著我……她那麼直言不諱,又問:你知道我最“討厭”你什麼嗎?
我淺淺地呷了一口豔紅的葡萄酒,很詫異地搖著頭。你咄咄逼人的霸氣,和你的壞!惠說這話時眼神嫵媚地看著我。
此時不壞,更待何時!我想。
人們常對中年人調侃有賊心沒有賊膽,有賊膽沒有賊心,待到賊心賊膽都有了,沒賊了。現在,賊就在你身邊,你不壞,行嗎?
我也有家,孩子上外地讀大學。妻在政府機關工作。我坦白地,敢不敢上我家坐坐,下樓出門轉彎,孺子亭小區裡。沒準我太太在家你見見她,比一比誰更優秀?
哦,真的!惠起身,真敢去。才進家門,不及關上門,惠就用胳膊環著寧,吻著他,嘟嘟嚷嚷地說:你壞嗎?我不管,就讓你老婆看見,看看你有多壞,多壞。
家裡靜悄悄。
妻不在家裡住,不是出差就是住孃家趕材料,只有週末我們才好不容易會面談談兒子的事。
一切該發生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感覺真好!
惠依偎著我,心間湧起一陣陣甜美的漣漪。情深了,人累了。
年復一年,我們陶醉在夢中。
永 採 情 愫
又是一個平安夜。
我有三個月沒有見到惠。
只是透過電波傳遞思念。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我會跟她聊上半點鐘、一點鐘,放下電話又發簡訊,簡訊過後再拿起電話,直折騰到天色蒙朧。
我是9月初奉命到哈爾濱建立外貿視窗,必須坐鎮三個月,待一切理順交班才能返回。
倘如沒有惠,我會兢兢業業全身心地投入。有了惠,忙碌之餘常常會想起她,有時整夜整夜地。
明天我來看看太陽島,陪你過平安夜!惠在電話中告訴我。
抑制不住想見見她的感覺,只是知道她近期玉體欠佳,北方的寒冷她受得了嗎。
不,我不管,明晨來機場接我。惠喊了一句就放下電話。
見到惠,我怔住,怎麼憔悴得這樣!
我陪她品嚐鱈魚後,建議到斯大林公園,隔著松花江,對面就是太陽島。
正逢冰雪節後,室內冰雕世界有名。想讓她適應二天再去,先到公園曬曬太陽,述述衷腸。
長椅上,我們坐在長大衣上,陽光下人感覺軟軟的暖暖的。
惠偎著寧,輕輕哼著:不管以後將如何結束,至少我們曾經相聚過……我一直在想著你。
惠淚水湧出如落線珍珠,使我更加憐惜。不知怎麼,對惠的到來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不祥感覺。
壞!惠貼近他耳邊懷著濃郁的深情:吻我!我們若無旁人盡情相擁相吻!
我告訴你。惠一臉嚴肅:三年前的平安夜是我收到醫院死亡通知書的那天,我在街頭無目標地倘佯了一下午。後來,碰上了你在歌廳你的大膽的吻,給了我力量和生活的勇氣。
那你丈夫呢?寧問。
他和孩子都死於車禍,我是積憂成疾。惠平靜地。
後來,我真不願離開你,很想很想嫁給你,嫁給你這樣知情知義知冷知熱的男人。可我不忍心拆散你的家,傷害你的妻子。
寧震驚,他明白惠為此付出的代價,天哪,其實我和妻早已分居,只差沒有辦手續,她是機關幹部,礙於面子!
壞!昨天醫生告訴我癌症已擴散,我將去很遠很遠的地方。記住,以後,不許和別人唱《好人好夢》,只能和我。
如果我不在啦,那就,就一個人唱。惠說得淚流滿面。
我將她緊緊擁在懷裡,任自己的淚灑在她削瘦的臉上。
我們結婚吧!在哈爾濱,我們度過刻骨銘姓的三天。
二週後,我回昌前與在醫院的惠通了話,待下飛機開啟手機,螢幕上卻留著她的話:好人好夢,我會永遠在你夢中。
我瘋一般奔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