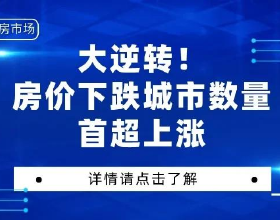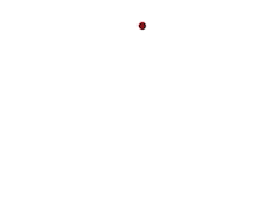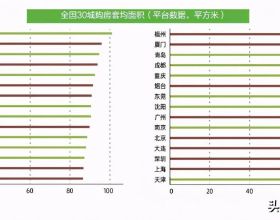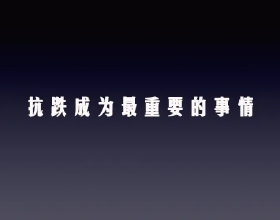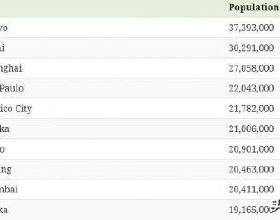中西方教育的差別、到底孰優孰劣一直是人們討論的話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有許多人認為西方所謂的“快樂教育”更勝一籌,認為“中式教育”給孩子過大的壓力,讓孩子變得死板、只會做題。
但如今越來越多人開始認同“中式教育”的優點,尤其是在“雙減”之後,似乎有更多家長開始憂慮,擔心這樣會導致孩子的成績下降,乃至“前途堪憂”。這種觀念的改變,不僅僅出現在國內,也出現在西方世界。
有一些接受西方教育長大的父母也開始將孩子送到中國接受“中式教育”,例如那個從斯坦福畢業的華裔媽媽朱賁蘭,她就將自己的兒子萊尼送到上海的公立學校讀書,在此過程中,面對中西教育的差別,她也曾“迷茫”、不解甚至“抗爭”過,那麼,她到底後悔了嗎?
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誘惑”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大多數人都覺得“中式教育”存在著諸多弊端,例如過於死板、教導學生死記硬背,導致孩子們創新力不足,“高分低能”等等。相對而言,西方世界崇尚的“快樂教育”則能夠讓孩子在玩樂中學習,有著諸多優勢。
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種觀點也在不斷改變,2010年前後大概是這種觀點變化最為明顯的時間段。
當時,美國經濟還沒從危機中恢復,西方世界一片蕭條,但中國經濟卻率先恢復,併成為了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2010年,我國GDP總量更是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樣許多媒體紛紛“預測”,中國經濟將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讓西方人一度感到十分迷惑,在此之前他們並不認為“中式教育”有什麼“可取之處”,可2009年上海學生參加國際學生評估專案測試排名第一的結果,讓西方人不得不開始正式之“中式教育”的優勢。
畢竟後來的測試還顯示,美國學生的成績尚不能進入前十名,只能在平均線上下徘徊。
西方——尤其是美國——精英群體似乎在那時才真正意識到中國、中文乃至“中式教育的重要性,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關注“中式教育”,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們開始學習中文,以免將來落後於人。
例如華裔虎媽蔡美兒就是在2011年時“隆重登場”,以其嚴格的“中式教育”方法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成為了當年的風雲人物。
例如美國金融大鱷羅傑斯就為了讓女兒們擁有更好的中文學習環境而舉家搬到新加坡,還在演講時號召大家都讓孩子學普通話,因為“中文將是他們餘生最重要的語言”。
也許正是受到了這樣社會氛圍的影響,成長於美國教育體系之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曾供職於路透社和CNN等媒體的華裔媽媽朱賁蘭,決定讓自己的兒子告別“快樂教育”,將孩子帶到中國,接受真正的“中式教育”。
在那時,似乎美國精英群體和美國媒體都在討論,是不是應該讓孩子接受“中式教育”,以提升他們能力。
因而,當朱賁蘭和丈夫決定趁著前往中國當駐華記者的機會決定將18個月大的兒子帶往中國、接受“中式教育”時,他們的許多美國朋友都對此流露出了羨慕之情。
中西方教育的差距:該服從權威嗎?
朱賁蘭和丈夫初到上海時,其實也為孩子到底應該讀什麼學校而糾結過,最初,他們將兒子萊尼送入了一家雙語託兒所,在這裡孩子們既說英文、又說中文,似乎能夠給孩子一個更好的適應機會,不過這家託兒所的缺點也很明顯:老師總是不停地更換,不太穩定也不利於孩子的教育和成長。
因而,當萊尼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時,他們沒有像其他外國朋友一樣,將兒子送入國際學校,而是選擇了家附近的一所極為著名的公立幼兒園——宋慶齡幼兒園。
朱賁蘭在後來談到此事時,表示雖然費用過於昂貴是他們沒有選擇國際學校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聽說中國的公立學校更善於管理孩子的紀律,她希望萊尼能夠在學校裡養成自律的習慣,並且打下紮實的數學基礎。
萊尼就這樣入讀了上海的公立幼兒園,對於這個美國家庭而言,關於教育的“衝突”才剛剛開始。
當兒子真正進入中國的教育體系之中,朱賁蘭才意識到中西方關於教育理念的衝突有多大,最先讓她感到震驚的是,家長們對於老師號召總是十分積極。
例如,當幼兒園老師詢問家長們是否有某些演出要用的道具或者演出服時,家長們總是積極響應,要麼就是說自己有,要麼乾脆說自己可以馬上去買,朱賁蘭覺得,這似乎意味著老師就是“權威”,而家長們正在積極“服從”這種權威。
很快,朱賁蘭就真正認識到了什麼叫“服從權威”。有一天,朱賁蘭和往常一樣接萊尼回家,像許多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萊尼頭上貼著一顆“五角星”,還怎麼都不願意摘下來。在詢問中,朱賁蘭得知,這是兒子“一直坐著沒動”所得到的獎勵。
這對於朱賁蘭是極大的衝擊,因為在美國學生們會因為表現超過其他同學而得到獎勵,但在這裡,孩子們卻是因為“聽老師的話”而受到表揚。
不僅是“坐著不動”會受到表揚,中午乖乖午睡、吃飯的時候不挑食又吃得快都會受到獎勵——簡單而言,只要遵守學校和老師的規矩,就能獲得表揚。
朱賁蘭開始意識到在中國的學校中,老師就是那個“權威”,而“中式教育”就是要求孩子服從權威,她用一個例子生動描述了中西方教育的差別。
萊尼是一個不喜歡吃雞蛋的孩子,在家裡的時候不管朱賁蘭怎麼誘導、教育,萊尼總是“說不吃就不吃”。但在幼兒園裡,老師發現萊尼不吃雞蛋後,就“強行”把雞蛋塞到了孩子嘴裡。
朱賁蘭對於此事感到很震驚,她告訴老師,在美國他們通常會給孩子講道理,用“有營養”鼓勵孩子們吃雞蛋,而不是強迫他們吃。
老師在得知透過這樣的方法,萊尼也不是每次都會吃雞蛋,甚至還有一次因為反抗“吃雞蛋”將牙摔裂了之後,只是簡單的表示“他需要雞蛋中的營養,不吃也得吃”。
後來,老師還告訴朱賁蘭,在孩子面前,她應該說“老師說得對,媽媽也會這樣做”。
雖然朱賁蘭對此仍有所質疑,但她沒有再幹涉老師的教育方式,萊尼在“中式教育”中順利成長。
一段時間後,朱賁蘭發現了萊尼身上的變化,他開始願意吃雞蛋,會主動完成作業,晚上自己收拾好書包、早上去幼兒園時還會主動與老師打招呼……
這一切都顯示出萊尼的自立能力和對規則的尊重感已經越來越強,雖然朱賁蘭仍舊認為這是由於兒子已經學會了“服從權威”,但她也開始享受這種“服從”所帶來的好處——萊尼變得更加自律,學習成績也不錯。
而且,萊尼並沒有因為在學校裡遵守規矩而變得“盲目服從”,朱賁蘭發現萊尼會說“老師也不是都對,她也會撒謊”,這讓她感到一絲安慰。
“興趣第一”還是“努力帶來成功”?
除此之外,朱賁蘭發現“中式教育”與西方還有另外一處巨大的差別,那就是西方教育似乎更強調激發學生的興趣、認為孩子的天賦能力更為重要,而在中國,老師們認為孩子的成績不好是“不夠努力”。
為了更好地瞭解中西方教育的差距,朱賁蘭曾對中國和美國的學校進行實地走訪,在此過程中,她發現中西方的教育從師資力量、授課方式到課堂氛圍都有著很大的區別。
例如,在中國,學校老師都有自己教授的科目,數學老師不會去代班教英語,語文老師也不會代班去教物理;但在美國,一些老師會同時負責2-3門課的教學,並不會只專注於一門學科。
例如,在中國課堂上,老師們大多數時候都專注於講課,將更多的知識點灌輸給孩子,很注重學習效率,學習氛圍濃厚且嚴肅;但在美國,老師們會更多采用小組討論、“一對一互動”等多種形式授課,引導孩子自己思考,氛圍相對輕鬆,但教授的知識也更淺顯。
例如,在中國,老師們大多認為孩子的努力更重要,他們大多會將孩子的成績不理想歸咎於“不夠努力”,中國老師致力於告訴學生努力就會通向成功;
而在美國,老師們卻會將一些孩子的成績不佳歸咎於他“對此不感興趣”或“沒有天賦”甚至是“智商差異”,鼓勵挖掘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賦。
在經過了調研之後,朱賁蘭認為,中西方的教育都是有利有弊的。一方面,她十分欣賞“中式教育”中的勤奮、刻苦的精神,她認為正是因為“中式教育”中“天才在於勤奮”的觀念,讓中國學生在遇到難題時會選擇“迎難而上”,而非以天賦為由逃避。
而且,由於“中式教育”對於基礎知識的強調,讓學生為將來的學習打下很好的基礎,讓未來的學習之路變得更平坦。
但在另外一方面,朱賁蘭認為“中式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扼殺了孩子的好奇心和創造力,這一點就是“快樂教育”佔據更大優勢了。
朱賁蘭強調,在中國的課堂上,學生們畫的孔雀羽毛都要是“同樣的角度”、畫的雨水必須是“規定的形狀”,這無疑扼殺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也許這也是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指缺乏創新能力的原因所在。
正是因為這樣,朱賁蘭並不認同學校懲罰孩子一些偶爾的“冒險行為”,她認為這是在扼殺孩子的獨立思考和創造能力。
不過,即使中式教育充滿了種種弊端,但朱賁蘭似乎也並沒有後悔將孩子帶到中國來接受教育。
如何平衡教育的利弊?
現在,已經讀小學的萊尼已經成長為了一個陽光男孩,從小接受“中式教育”的他,養成了極為自律的習慣,他能夠主動學習,會擔心遲到、不完成作業會“讓老師失望”,而且,萊尼還養成了極為堅毅的性格品質。
朱賁蘭曾提及,有一次她帶著兒子去看牙醫,驚訝地發現兒子竟然可以在僅僅接受“牙齦麻醉”的情況下,配合地張嘴進行根管治療。
因為在美國,兒童牙科醫生都會採用“全麻”方式進行手術治療,因為美國醫生根本不指望小朋友能配合治療。這讓朱賁蘭認識到,中式教育帶來的另外一項好處——培養孩子堅毅的品格。
當然,最重要的是,萊尼現在各項基礎教育的水平都遠超於美國的同齡人,中文也很不錯,基本上完成了朱賁蘭的目標,因此,儘管朱賁蘭仍認為“中式教育”有種種弊端,但她並不後悔。
而且,朱賁蘭還提及,現在上海的學校已經開始嘗試平衡中西方教育之間的利弊,例如學校在依舊強調語文、數學等基礎科目重要性的同時,讓孩子們上選修課,調整授課方式、提升孩子們批判思維的能力,這也是她所認同的,真正對孩子成長有利的教育方式。
朱賁蘭曾總結道,結合中西方教育的優勢才能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成長,因而“先緊後松”“先中後西”可能是更好的教育方式,即在基礎教育階段,讓孩子接受“中式教育”,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等孩子長大以後,就大膽放手,讓孩子接受西方教育,引導他們探索、創造。
隨著萊尼的成長,朱賁蘭覺得讓兒子脫離“中式教育”系統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加上現在兒子還要面對越來越多的“老外”身份認同難題,朱賁蘭正計劃在兒子中文水平更加精進之後,就帶兒子回到美國,接受西方的教育。
朱賁蘭的經歷也許對我們也是一種啟發,在基礎教育階段,教會孩子遵守規矩、自律是很重要的,但在孩子讀到中學乃至大學時,我們就更應該鼓勵學生的探索能力、創造能力,讓孩子可以獲得全方位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