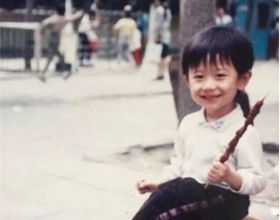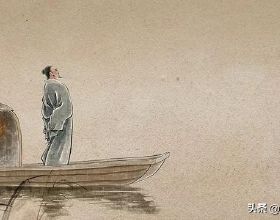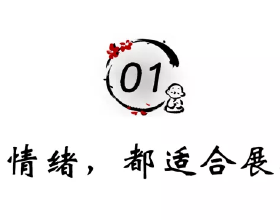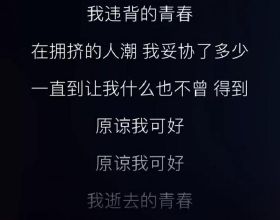周朝是歷史上第一個設立攝政王的朝代,但攝政王卻是中國歷史上最高危的職業之一。因為攝政之人一般都不得善終,唯一個人除外。他就是千古第一攝政王周公旦,也是後世輔國能臣紛紛效仿之楷模。這個活成了神一樣的人物有著怎樣的一生,他內心就沒起過一點兒波瀾嗎?
從公子旦到周公旦
周公旦生活的年代在商末周初,周公是他的封號,他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嫡四子,武王姬發的母弟。文王在世的時候,就時常誇讚,在眾多兒子中,唯有發和旦最賢。這兩個人就成了文王的左膀右臂。後來姬發被封為太子,旦被封采邑在周。
從封賞就可以看出老爹文王對姬旦的寵愛,遠遠超過了其他兒子。這個封地周在什麼地方呢?其實就在岐山。也就是說文王把老家之地給了旦。其實老父親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王座只有一個,既然王位許給了老二,家裡的產業就給老四吧!不過這種封賞跟封蕃還是不一樣的,屬於內服,對土地沒有實際的管轄權,只是可以享受封地的供奉。所以,此時還不能稱他為周公,而應該叫他公子旦。
公子旦為什麼如此受文王寵愛?除了乾淨利索的處事能力外,主要因為他比較賢德,多才多藝,又孝順仁厚。據說公子旦在文王身邊輔政時,事必稟命,從不擅專。這麼聽話又能幹的兒子,哪個當爹的不喜歡?還有一點就是,他比較節儉,也不張狂,謙遜有禮,修身自愛。這是非常難得的。人在高位,要想低調是很難的。因為你的身份、你所處的環境不允許你低調。公子旦跟他的幾位哥哥不太一樣,他出生時,周國的國運已經起來了,可以說他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但他卻時時刻刻謹言慎行,所以深受滿朝文武和老百姓的喜愛,得了一個賢德的美名。
當然,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他比較愛惜自己的名聲。而且他愛惜的程度,已經到了嚴苛的地步,這或許就是他一生宿命的根源。
公子旦是怎麼變成周公旦的呢?實際上是武王姬發為他鋪的路。武王姬發繼位之後,就開啟了東征之路。公子旦隨王伴駕,當了一名謀士。在兩次伐商之戰中,公子旦都為武王出謀劃策,提供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對戰局也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他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得到了極大地施展,也令文武百官看到了他總攬朝政、掌控全域性的能力。
尤其在牧野之戰時,丞相姜子牙率軍衝鋒在前,他留守後方,調配軍需,保障國家機器正常執行,為武王建立了一個非常穩固的大後方。雖然在《封神演義》裡他並沒有太多出場的機會,但是實際上,公子旦對周國定鼎天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牧野之戰後,武王姬發大封功臣,公子旦被封魯侯,但不就蕃,由其長子伯禽代理國事。此時的公子旦既有藩國封地,又有百官之首的實權,成了名副其實的周公旦。
由於周朝初建,外有虎視眈眈的東殷餘部,內有滿目瘡痍的中原大地百廢待興,武王一個人是首尾難顧,對周公旦的依賴也越來越多,周公旦手中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真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是周公旦依然保持著他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風格,像當年侍奉父王一樣,對二哥也是事必稟報,夙興夜寐、殫精竭慮,在二哥的領導下,一門心思地搞發展。周王朝安撫殷商遺民、東遷國都、分封天下等定國方針,都是這個時期定下來的。毫不客氣地說,公子旦的角色類似於清朝雍正年間的頤親王胤祥,整個一個“常務副皇帝”。
周公旦的上位之路
可惜好景不長,武王還都後的第二年,就一病不起。他自知命不久矣,這個時候最緊迫的事莫過於敲定繼位人。因為在周立朝以前,只有夏、商兩代,所以武王可以參考的歷史經驗並不多,加之這兩個朝代的繼承製度比較靈活,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兼而有之,且各有利弊。武王就犯了難。
父死子繼雖然從人倫情感上是順理成章的,但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幼主登位。畢竟一個小孩子坐在大殿之上,底下站著一群大人,大臣們打著官腔,小皇帝能聽懂幾個字?如果由太后垂簾(當時還沒有太后這個職稱,也沒有垂簾的先例),那必然重用外戚,自家的江山就指不定落到誰手上了?武王的嫡長子誦尚在沖齡之年,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卻成了別人的嫁衣,怎麼能嚥下這口氣。
再說兄終弟及,雖然江山可以不改姓,但落不落到他這一脈就不好說了。此時政治呼聲最高的就是自己心愛的弟弟周公旦,而且旦的人品也是有目共睹的,成年之君繼位,必能使國家可以平穩過渡。但是權力會讓人腐化變質,連商湯那樣的賢王也沒能阻止自己的子孫會變成帝辛那樣的暴君,何況自己的才能怎麼能勝過商湯呢?等到旦百年之後會把王位還給自己的兒子嗎?他當上天子之後,難保不把誦當成眼中釘肉中刺……
武王沒想到自己戎馬一生,打下了江山,卻保不住自己兒子的一條命,不禁悲從中來。然而,生命倒計時已經開啟,留給他的時間已經來不及感嘆人生了。他必須想一個兩全的辦法,既保住兒子一命,又保住江山社稷。可是世上哪有兩全之法,沒有人吃虧,怎麼有人能佔到便宜呢?
於是,武王強撐身體,召見了周公旦及一干重臣。自從他生病以來,周公旦一直代他主政,朝政大權已經落入其手。現在不是武王想讓誰繼位的問題,而是周公旦認不認可繼位之君的問題。所以最緊迫的事是安撫周公旦。只要周公旦支援兒子繼位,那滿朝文武也必然奉之。
偌大的寢殿裡,武王掙扎起身,用盡最後一點力氣,扶起了伏於床前的弟弟周公旦。兄弟倆眼中都噙著淚花,眼見從小一起長大的兄弟馬上要天人永隔了,兩人內心具是百感交集。
武王對周公說,“是上天要滅殷興周,我等秉承上天旨意行事,天必佑之,可惜大業初定,百廢待興,我卻要撒手人寰了,我願意把王位傳給你。只有你能擔負起祖先大業,不至於令周室衰敗下去。假使你不顧大局,不能追先人之德,下無以應人民之望,我也無法見祖先和上帝了。現在就占卜一下你的新都城,選好了就著臣工們興都建業。”
雖然武王說得信誓旦旦,但是周公旦畢竟也受權力薰染多年,深知國之重器怎可輕付,何況武王亦有嫡長子,二哥若真想兄弟傳位,為何不單獨召見他?至少不會讓召公奭和一干外臣在場。
而召公奭也是一臉狐疑,心想這大王不是病糊塗了吧?雖說周公旦居功至偉,但周自古公立國以來,一直都是父死子繼,突然間改成兄終弟及,難保其他兄弟不想入非非,再說真要論國賴長君,周公旦上面還有一位管叔鮮呢?
正當眾人猜測之際,還未行占卜之術,武王就發話了,“新都應該建在洛邑。”
洛邑在哪兒呢?洛邑就在今天河南洛陽的老城區一帶。這個地方距離朝歌不遠,但距離西岐卻不近。武王為什麼要捨近求遠選這個地方營建新都呢?
一來是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仗打完了,接下來的治國重任自然是發展經濟。論普天之下物資豐富、交通便利之所,肯定是華夏中心,非朝歌莫屬。不過,朝歌畢竟是商朝舊都,殷商遺民多,商朝的舊勢力也匯聚於此,所以只能遺憾捨棄。那麼離朝歌不遠的洛邑就成了最合適的選擇。
二來是遠離西岐故地,便於培植新的政治人脈。西岐雖然是周的龍興之所,但舊貴族、舊勢力也多,彼此盤根錯節,姬誦繼位後,又出現了主少臣強的局面,那些老貴族們怎麼可能聽一個小娃娃指揮;另外,也是武王捨近求遠的初衷:如今的大周是天下人的大周,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偏安一隅的小諸侯國了,需要有新的格局、新的制度和新的人脈,而洛邑是一個全新的都城,沒有老貴族的掣肘,也沒有殷商殘餘的虎視眈眈,正好可以來個“人事兩新”。
武王這話一出,周公旦立刻就明白了:這哪是在給我選都城啊,分明是給他兒子誦選的新都。眾人也明白了,這明裡是託國、暗中卻是敲打,告誡周公旦要盡心盡力輔佐新主,而召公和一班老臣便是這場託孤大戲的見證人。
哥倆兒再好,到了生死關頭,心裡這點小算計還是難免的。此時周公旦心裡縱使有一萬個不樂意,也只得連忙推辭,搶著去開壇禱告,說要用自己替代武王去陪伴祖先。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顯然是在向武王表白。
也不知是周公的禱告感到了祖先,還是這一番表白令武王放下了心中芥蒂,總之這場法事過後,武王居然真的迎來了短暫的迴光返照,而年輕的周王朝也在這幾天內發生了鉅變:武王立嫡長子誦為太子,繼位為成王,周公旦為太宰,攝政稱王,召公奭等一干老臣輔政。一概大事安頓妥當後,武王駕鶴西去,大周最強天團走馬上任,而中國也即將步入一個璀璨的時代。
武王為何選中周公旦攝政
關於武王晚期為什麼要立攝政王一事,諸多原因前面已列舉不少,成王年幼、國家初定,這些都是無法迴避的硬傷,但是武王為什麼選擇周公旦攝政,而不是勞苦功高的姜子牙?這可能是兩千多年來,人們心中最大的一個疑問。
其實除了姜子牙以外,召公奭作為老貴族的代表,頗具政治實力,也是輔政的良選。為什麼後人單單把姜子牙和周公旦視為競爭對手呢?其實這種思想是從明清以後才逐漸流傳開來的,主要是由於《封神演義》這部小說的問世。對歷史人物進行藝術加工,提煉人物身上的優點物質,以使人物豐滿,甚至可以賦予傳奇色彩。這是小說進行藝術創作的手段。但小說不能當成歷史來讀。在真實的歷史上,的確有過文王夢飛熊之事;《史記》等書籍也有姜子牙出任大周軍師、並率軍平叛等記載,但這隻能說明姜子牙的軍事才能,僅此而已。
所以,從這仨人在文、武兩朝的職務和才能來看,顯然周公旦的綜合能力更強一些。從行政能力來看,周公旦輔佐了兩代君王,老爹文王和二哥武王,而且都是高階秘書、貼身智囊。我們都知道,一般提拔領導幹都是從秘書這個崗位來選。而召公奭雖然也一直在中樞工作,但並沒有真正接觸過全面工作,而周公旦在武王東征和武王生病期間一直是代管國政,總領全域性的,這是召公所不能比的。
從軍事才能來看,雖然姜子牙一直是周軍的軍師、智囊,但他的才能主要是在戰術佈局、調兵遣將、指揮作戰方面,實戰經驗比較豐富;至於如何保障大軍糧草運輸、怎樣籌措軍備物資,與此同時還要保障後方生產供應、社會穩定、經濟正常執行,這些人員排程、政府機構執行方面的工作,他涉足較少,而這些恰恰是周公旦一直在做的工作。從這點來看,姜太公顯然輸了一截。
除了選賢以外,還要看血緣。商周乃至春秋戰國時期,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丞相、太宰這樣的百官之首,一般都是選擇王子、公子這樣的直系王室成員擔任,比如商末時帝辛就任命自己的王叔比干擔任丞相一職,有名的戰國四公子中有三位都跟國君是兄弟叔伯關係,但外戚當這種級別大官的就比較少見。這一點與漢代以後的封建時期不太一樣,所以那個年代外戚專權的情況比較少,外戚很難成氣候。
那麼姜子牙是誰呢?妥妥的周王室外戚,武王的老丈人,成王的姥爺。如果姜子牙攝政,一班姬姓老貴族必然不答應,為了鞏固攝政之權,他必然要任用姜姓或其他外戚。這樣一來,姓姬的就靠邊站了。
周公旦就不一樣了,即便他日後搶班奪權自己當了大王,天下還姓姬。換了個大王,江山還是周王室的江山,不會動搖國本,也不會引起太大的騷亂。外姓掌權就不妙了。人們會想明白一件事,原來天下不一定姓姬;既然姓姜的能當大王,我們也能當。如此一來,必然天下大亂、塗炭生靈。
那麼,同樣是姬姓貴族,召公奭與武王同輩,在宗族中的地位並不比周公旦差,他說話沒有威望嗎?這要看什麼事了。如果是宗族事務,召公奭和周公旦同樣有發言權。但現在是為國家選才,說的都是軍國大事,自然要以王族親疏為尊,周公旦是成王的親叔叔,是所以王族中血緣最近的。而召公奭只能靠邊站了。
除了這兩點外,還有一點是武王不得不選擇周公旦的原因——只有周公旦能幫他完成未盡之業。在眾多兄弟中,周公旦是最瞭解武王的。兄弟倆年輕時一起給老爹輔政;等到武王繼位後,周公旦又為他輔政,成為武王領導班子的核心。周公旦跟著武王摸爬滾打多年,深知武王的政治理想。所以當伐商大業完成後,武王就和周公旦開始繪製周王朝的美好藍圖,把未來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構想都細細篩了一遍。武王深知,即便自己不在了,只要周公旦在,這個美好藍圖就能一步一步地實現,而他的兒子將享有這一切。倘若換了別人,他的政治理想就真的成了一張藍色的圖。
那麼,武王不怕周公旦奪權嗎?為什麼還要給他遇大事可稱王的特權?這就要了解“攝政”是怎麼一回事了。攝政是指代國君處理政事。這一個“代”字,就把攝位之人的身份結結實實地擋在了王座之外。至於稱王一事,只是為了便宜行事,比如發號政令時,以王命釋出的稱為旨,這樣就可以蓋上王印,法律效力就不一樣了,當然也便於史官記載。春秋時的魯隱公也是攝政稱公的。
被猜忌的一生
年富力強的周公旦成了大周王朝的實際掌舵人。然而,不要以為他的人生就此開掛了,實際上他的磨難才剛剛開始。
周公代政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經。其中就包括管叔鮮。當然他有這個實力。管叔鮮是文王的嫡三子,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的三哥,兄終弟及的第一順位繼承人。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管叔鮮對周公旦攝政極為不滿,認為周公旦繼位無望就抬出成王來當擋箭牌,自己把持朝政,暗地裡當起了周王。不僅管叔鮮,武王的很多兄弟、召公奭在內的很多王室親貴都有這種想法。起初,周公旦積極地為自己辯駁,一找到合適的場合就發表了感慨——諸如武王病重時,他代武王向先祖禱告那類的表白。漸漸地他就發現,這種表白沒什麼用。因為不管他說什麼,只要他在攝政的位置上坐一天,大家對他的誤解就不會消除。
其實有這種想法也算是人之常情,畢竟是世間最大的誘惑,誰能不為所動?難道周公旦真的絲毫沒動過心嗎?甚至在某個時刻產生過一絲雜念嗎?這很難說。誰也不可能鑽進周公旦腦子裡看個究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從未表現出對權力的留戀。
周公旦剛剛攝政,就迎來了最大的信任危機,來自頂頭上司成王的猜忌。列位要說了,成王不是個小孩嗎?他怎麼也猜忌起自己的親叔叔了?況且周公旦不是經常見到成王,還教給成王為君治國的道理,按說叔侄關係不錯呀?怎麼就鬧上了信任危機呢?
這個事也不難分析。娃是好娃,但是架不住耳邊風。管叔和蔡叔一直對監視商王之子武庚的差使不太滿意,認為是周公旦在背後搗的鬼。因為此時的商人對周王朝並沒有真正的臣服,隨時都可能叛亂,一旦叛亂,這二人必落個監管不力的罪名,實際上成了商人的墊背。同是文王之子的周公旦卻在朝中混得風生水起,甚至能攝政稱王,這兩個怎麼能不眼紅呢?於是,他們就想了一個陰招:讓在京城的內線散佈謠言,說周公旦欲據攝纂位,將對幼主不利。成王畢竟是個半大孩子,既沒有政治鬥爭經驗,又處在叛逆期,一下子就相信了這個流言。只是他此時沒有親政,也不能把周公怎麼樣,可是臉和心是騙不了人的。他開始疏遠周公,對周公的態度不像以前那麼恭敬了。
周公也聽到這些謠言了,而且他得知這些謠言是出自那兩位好兄弟之口,就藉著一次朝會的機會講了一個故事,藉以提醒成王和眾臣,也作為自白。但是他發現,這招不太好使。畢竟他之前太愛表白了,動不動就發一番感慨,聽得人都有些審美疲勞了,也自然就不拿他的話當回事了。心涼的周公並沒有就此灰心,他知道自己那兩位好兄弟也不是等閒之輩,必然還有後招;他收到訊息,邊境的一些小諸侯國蠢蠢欲動,於是就藉機親自到東方去審察工作,暫時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從出居東方,到全身而退。周公雖然離開了權力中心,但是朝廷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耳目。不能說他在監視成王,只能說他來了一招外鬆內緊,給好事之徒空出來一個表演的舞臺。果然不出他所料,好兄弟管、蔡二人坐不住了。這兩個早已聯絡好東方的徐、奄等小諸侯國在邊境整兵,對內則聯合武庚,允諾把原來商朝的地盤還給武庚。這麼大的誘惑,武庚可就來勁了。他明白,即便他老爹帝辛在位,當商王這等好事也輪不上自己。於是,就準備跟著管、蔡兄弟倆大幹一場。這一下子裡應外合,剛剛建立的周王朝可真是危若累卵了。
周公早就預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他出居東方,正是為了提前謀劃。此時唯一的阻礙就是成王和自己之間的隔膜。天底下最難修復的有關係就是信任。怎麼重新建立信任呢?周公旦就給成王寫了一首名為《鴟鴞》詩,還收編到了《詩經》中。——《詩經》是沒有作者名字的,所以這首詩到底是不是出自周公旦之手,無從可考。我們權當它就是出自周公旦之手,問題就來了。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這首詩大致講了一隻母鳥的哀鳴,辛辛苦苦修建起來家舍,自己卻被趕出家門,眼看著家舍被人搗壞,卻無計可施的故事。在詩中,周公自比鴟鴞,不僅在向成王喊冤,更像在責備成王偏聽偏信,以致自己不得不離開家園。這哪兒是在求和呀,分明是端著王叔的架子教訓侄子。可是周公忘了,此時的成王已經不是那個太子誦了,是正正經經當了一段時間大王的人。在他眼中,周公首先是臣子,而後才是叔叔。周公卻用教訓的口吻同他講,他怎麼可能接受呢?可以想見,這首詩的命運必然是束之高閣了。
可是朝臣們著急呀,眼見武庚起兵殺來,殷商一旦死灰復燃,這些周朝的王公大臣、姬姓貴族們,一個也跑不了,下場要多慘就有多慘。所以,一些文筆好的大臣也開始給成王寫詩,比如《伐柯》呀,《九罭》呀——都可以在《詩經》中找到。成王每天有一項重要公務,就是讀詩,各種各樣的正能量詩。
詩嘛,讀了,也就讀了,成王心想,寡人就當文化娛樂活動了,反正每天做功課也得學習嘛。這樣處理政事跟學習結合在一起,兩不耽誤,還挺好。群臣們見大王一直沒反應,一來二去,這股子勁也就洩了。
說來是周公運氣不該絕。這一年秋天,王畿附近颳起了龍捲風。現代人見到龍捲風還害怕呢,你想兩千多年前的人見到電閃雷鳴、狂風大作,大樹連根拔起,四下飛沙走石,坐在屋裡就感覺天旋地轉,肯定以為是天譴啊!於是成王就跟幾位近臣就開啟專門藏著王室典籍的金滕櫃,想查一查資料,結果翻來翻去就看見了武王病重時,周公想為武王替死的那篇祝文了。這一讀不要緊,成王是涕淚橫流,想起了叔叔的千好萬好,平日對自己的諄諄教導湧上心頭,一時後悔不已,便決定親自前往東方迎接叔叔還朝。
周公和成王這對叔侄破天荒地精誠團結起來。兩人決定就把平叛的指揮所設在東方,就地平叛。周公這邊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劃佈局,其實已經整頓好兵馬,打好的埋伏,就差收網了,所以整個平叛之戰比較順利。原本跟著管、蔡二人一同起兵的那些小諸侯們,一看周公回朝坐鎮,嚇的直接投降了。武庚深知自己跟這些周國的諸侯不同,自己本身就是前朝餘孽,周王恩澤勝天,自己卻不知好歹,還妄圖恢復殷商舊制,是萬萬沒有迴旋餘地了,所以乾脆頑抗到底,選擇了一條速死之路。
叛亂平息後,周公和成王班師回朝,這一次與前次大為不同。周公的誠心和忠心終於被世人所理解,大家也漸漸習慣了身邊立了一個道德標杆。周公還朝後,馬不停蹄地幫成王幹了幾件大事:一是分化殷商餘民,將大支遷往各地,使殷商後人難再聚集生事;二是營建新都洛邑、制定禮樂,以使王朝有一個煥然一新;三是分封諸侯,以安天下。當然,成王也投桃報李,正式冊封周公嫡子伯禽為魯侯。周公謝恩請辭,成王效法先父,請求周公留下一脈代其輔國之職。周公則在告老還鄉後病逝,得以安享善終。
周公旦的自醒與自知
周公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攝政王,而且是由先王允諾攝政稱王的。可以說,在後世攝政王中,是絕無僅有的。況且,歷史上有一個怪現象:但凡當過攝政王的,都沒有好下場,要麼像魯隱公一樣被毒死,要麼如多爾袞一樣橫死,為什麼周公旦卻能得善終,而且還能永受後代祭祀、推崇呢?這與他的自醒和自知有著莫大的關係。
明白自己離王座有多遠。周公的清醒在於他明白自己從來都不是父親眼中的繼位人選,雖然早期與二哥一同輔政,但周公旦自知並沒有二哥的果敢,對父王更多地是順從,凡事必稟。到了二哥武王時代,他的清醒來自於擺得正自己的位置。雖然有“常務副皇帝”之實,但他也深知,倘若自己奪位,其他兄弟必然聯手對付他,屆時他以寡敵眾,並無必勝把握;況且剛剛建立的周王朝一旦陷入內戰,必將迎來滅頂之災,即使他得到了這個王位,又能坐多長時間呢?所以,他既是離王座最近的人,也是離王座最遠的人。
有而不爭,愛惜羽毛,剋制權力的誘惑,以使自己不迷失本性。周公是一位非常愛惜羽毛的人,一生極其看重名節。他所追求的大道,不是九王至尊的人間高位,而是道德上的至高點。這才是高於一切的存在。所以,他可以不謂權力的誘惑,即便在手握帝國大權時,在沒有人能夠掣肘他時,他依然能夠保持清醒和自制,依然能夠守住成王的王位。這也是武王放心將成王和江山交託與他的原因。而這一點卻是管、蔡之流,那些近利小人所不能理解的。《道德經》中講“有而不爭”,正如周公一般。所以周公雖未繼位,卻在百年之後得以入享太廟,永享後人祭祀。當然,也正是因為這份清醒和自知,才令他成為了歷史上唯一一位得以善終的攝政王。
特別說明:以上圖片均來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參考文獻: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