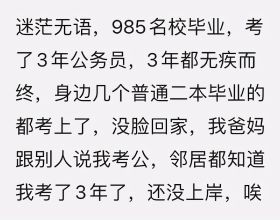揚之水
一年一度的“正倉院展”10月30日將在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第73回展覽共有55件寶物,其中8件為首展,重點展品包括樂器、筆墨紙硯、經卷、染織品、文書、佛具等。
學者揚之水的新書《與正倉院的七次約會》不久前出版。於她而言,正倉院是一個想了很久的題目,很早就計劃寫一本與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有所不同的書。因自二〇一二年起至二〇一九年,她與幾位朋友年年秋天往正倉院看展(唯二〇一八年是個例外),像是認真履行一個不變的約會。“正倉院乃寶山一座,既無緣遍觀,則不過著眼於‘可意’者,於‘他人見不到處’得其一二,也算是小小的心得。”
《澎湃新聞·古代藝術》(www.thepaper.cn)經授權刊發此書第二部分。
坐夏日偏長,知師在律堂。
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涼。
苔色侵經架,松陰到簟床。
還應煉詩句,借臥石池傍。
——項斯《寄坐夏僧》
展陳於第六十四回的“紫檀金銀繪書幾”,是我關注已久的物事。初唐時候,印刷術尚未發明,書皆卷軸式,閱讀則須雙手卷持,自然不很方便。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有一篇《臥讀書架賦》,略雲:“伊國工而嘗巧,度山林以為格。既有奉於詩書,固無違於枕蓆。樸斫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鉤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枘制鑿,術仍取於縱橫。功因期於學術(一作殖),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雄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每待蘧蘧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風清夜淺,每待蘧蘧之覺”,用《莊子》之典;“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用後漢邊孝先故事,都是切臥讀之意。這篇賦文義並不深,難於解讀的卻是臥讀書架的形制與式樣究竟如何。所謂“其始也一木所為,其用也萬卷可披”,註釋家或曰此句意為“書架只用少量木材製成,卻可插放萬卷圖書”‹7›,未免更令人增加疑惑。那麼且看這一個“紫檀金銀繪書幾”:小小的方座上一根立柱,柱上一根橫木,橫木兩端各有一個圓託,圓托里側則為短柱,柱上兩個可以啟閉的小銅環。若展卷讀書,便可啟開銅環,放入卷軸。
所謂“兩足山立,雙鉤月生”,“不勞於手,無費於目,開卷則氣雄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唐人賦詠之物究竟如何,見此而解。掛編則色連翠竹 ,應該是指收起書卷,納入竹編的書帙。第六十九回展覽中, 展出名品最勝王經帙的同時, 又展出一件竹書帙(原用於收納經卷),正教人見得真切。
晉城博物館藏一件青蓮寺出土的北齊乾明元年(五六〇)曇始造像碑座‹8›,其中一側榜題“波林羅”之下方是坐在方榻上的僧人,右側一個經架,式樣與正倉院藏紫檀書架幾乎無別。
紫檀金銀繪書幾通高五十八釐米,用於“臥讀”固然尺寸偏大,但臥讀書架的形制與樣式與此經架相仿應該是不錯的。臥讀書架的創意或者就是來自經架,經架也多在敦煌唐代壁畫中構成敘事‹9›,可見它的使用在這一時期之普及。項斯《寄坐夏僧》:“坐夏日偏長,知師在律堂。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涼。苔色侵經架,松陰到簟床。還應煉詩句,借臥石池傍。”釋子讀經與士子讀書竟是一般況味。
《正倉院考古記》提到中倉所藏十七枝唐式筆,不僅可見古式,且“裝潢之華麗,尤足驚人”。展覽第六十七回裡,我見到了其中裝潢華麗的一枝。
斑竹杆,兩端分別套金箍,末端的象牙飾好似塔剎。憶及柯橋博物館藏唐墓出土一枚被稱作戒指的金箍,外膨如扁鼓,內徑一點五釐米,外徑兩釐米,重二點九克。口沿內斂,緣邊上下均打作連珠紋。兩道弦紋內的裝飾帶以規整的魚子紋為地,其上打製四個飛奔的有翼獸:虎、豹、獅子、鹿,鹿身鏨出梅花。雖體量很小,卻製作甚精。以正倉院藏品為比照,或可推知它是這一類物品的裝飾件。
筆之難得固不待言,不過更令人關注的是與筆同在而尤其不易儲存的筆罩亦即筆筒。宋無名氏《致虛雜俎》中說道“(王)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裘鍾”似乎很難與筆筒相聯絡,然而有此實物,這裡的意思渙然得解。“裘”,此指毛筆,“鍾”是形容筆筒的造型。後世或名斗篷曰“一口鐘”,也是形容它上銳下闊之狀。至於陳放在桌案用於置筆的筆筒,是在高坐具普遍使用的時候才廣為流行,早期言“筆筒”,均指筆罩或曰筆帽。
北倉藏品中,有兩枚中土傳入的唐代人勝殘件,人日風物,這是稀見的實物遺存,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北倉上”一節記所見“人勝殘闕雜張”雲,“據齊衡三年(八五六)《雜財物實錄》稱:「人勝二枚,一枚有金薄字十六,一枚押彩繪形等,緣邊有金薄裁物,納斑藺箱一合,天平寶字元年(七五七)潤八月二十四日獻物。」今品則以二殘片粘合為一者。一片繫於淺碧羅之上,粘有金箔剪成十六字雲「令節佳辰,福慶惟新,變(當為燮字之訛)和萬載,壽保千春」。《雜財物實錄》所稱有金箔字者即此,今金箔諸字已變黝黑,羅色亦暗矣。又一片較大,約四分之三粘於其下,邊緣圖案以金箔剪成,上粘紅綠羅之花葉,緣內左下端有彩繪剪成之竹林,一小兒戲犬其下。金箔邊緣及彩繪人物,色彩如新,惟犬形已殘耳,此當即《實錄》後稱之物。考人勝為用有二,一以金箔鏤成,人日貼於屏風;一剪綵為之,戴於頭鬢。今觀正倉院所存殘片,可知乃屏風貼用之物”‹10›。
正倉院展第六十六回中適有此物,因得以仔細觀摩。人勝殘件之一,是貼了十六字吉語的一枚綠羅,吉語字上面的金箔雖已全部脫落,但在展櫃的燈光下,仍可見黑字上面泛出幾點細細的金光。
《荊楚歲時記》曰人日“翦綵為人,或鏤金簿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隋杜公瞻注云:“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吉語中的“令節佳辰,福慶惟新”,正是“人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之意。另一枚人勝殘件,卻是各樣剪綵花分層貼上在一尺見方的橘紅色絹帛上。緣邊圖案下邊的一層剪作紅花和綠葉,上面一重,是粘覆金箔的楮紙剪作圖案,鏤空的花和葉正與下面的紅花綠葉相套合。剪紙的四角,各一個連珠紋緣邊的方勝或曰疊勝,殘存的兩朵紅花,便是疊勝的內心。兩枚人勝的製作,都是剪綵與鏤金共用,所謂“鏤金簿”,此“金薄裁物”即是;“為人”,乃為小兒。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時屬盛唐至中唐的墓葬出土剪紙人勝,可與它互看。用作隨葬,大約有祈福之意。不過《荊楚歲時記》中說到的“華勝”,似與此式樣不同。隋唐以前,勝的造型乃中圓如鼓,上下各有一個梯形與圓鼓相對。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的祥瑞圖中有此物,兩勝之間以橫杖相連。唐代銅鏡中也還有這樣的影象,如許昌博物館藏一面祥瑞圖十二生肖鏡,祥瑞之一便是“金勝”,與榜題相應的金勝影象即為古式。此鏡的時代約當初唐。
金勝作為祥瑞,也當是來自古義,《宋書》卷二十九《符瑞下》曰:“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唐代作為人日風物的人勝卻是取了別一種樣式,即如正倉院藏人勝殘件。當然它不是孤證,卻是因為伴隨著與人日風俗相合的吉祥語而意義最為明確。由此發現,唐代廣為流行的所謂“菱形”圖案,原來就是來自人勝,當名作方勝。方勝相疊,可稱疊勝,但方勝也不妨作為通名。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地宮出土一枚金花銀片,懸墜於銀鉤的方形銀片邊長九釐米,造型以及鏤空的地紋均與正倉院藏人勝佈置於四角的疊勝相同,兩個方勝交錯相疊的四個角,上下各一隻“金雞”,左右各一隻“玉燕”,方勝中心一隻牛,乃一一與新春裡的節物相合,此即唐代的人勝。它也常常用於銅鏡,書寫“千秋”吉語,並且不以用於“聖節”的千秋鏡為限。
方勝又成為唐代圖案中的一個基本元素,每以各種方式組織到不同的紋樣中,如邊飾,如花心。而綴瓔珞、垂流蘇成為幡勝,也都是常用的構圖方式。第六十四回展品中有一件黃地花文夾纈,紋樣可視作花的套疊, 也可視作勝的套疊。
由此想到方勝和疊勝設計構思的來源之一,或是建築中流行的鬥四藻井。若進一步延伸,則寶相花的基本構圖也是若干花朵疊相斜向交錯,以此不斷伸展,蔚作花光五色。而正是這些大體同源的意匠,形成裝飾領域裡豐美富麗的唐風。
‹7›《楊炯集箋註》(祝尚書箋註),頁72,中華書局二〇一六年。
‹8› 承學友李丹婕相告,遂專程前往參觀並拍照。
‹9›郭俊葉《敦煌壁畫中的經架:兼議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頂南側壁畫題
材》,頁70~74,《文物》二〇一一年第十期。
‹10›《正倉院考古記》,頁46,文求堂一九四一年。

《與正倉院的七次約會:奈良博物館觀展散記》揚之水 著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21.7
責任編輯:陸斯嘉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