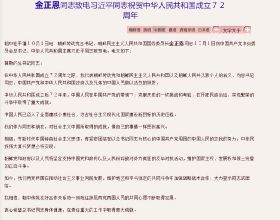雷化緣出生那天,有和尚上門請求佈施,父親認為這是一種預示冥徵,所以為他取名“化緣”。據說雷化緣的祖父,乃是嘉靖帝親策取中的進士郎,以耿介不阿聞名士林,為當世君子。但他的君子陰德,卻未及惠益子孫,《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雷家的福澤,只延續兩代便消耗殆盡了。雷化緣兩歲那年,雙親相繼下世,他被安縣一戶姓陳的人家收養。十歲時,養父母亦雙雙見背,孤苦的雷化緣,輾轉流離,最終來到灌縣青城山下。一個姓童的老爹見他可憐,領了他去,這才有了個遮風避雨之所。
童家赤貧,老爹自己尚且衣食不周。雷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日入山打柴賣與縣裡人。縣裡人也都憐他,每見他背柴下山,便拿一升半升穀米來換。雷化緣也不計較穀米多寡,但給便換,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
這年正逢嚴冬,一天夜裡紛紛揚揚,卷下好大一場雪。次日一早,雷化緣冒風摸上山來,但見冰塞溪壑,積雪彌谷,白漫漫一片,往日走慣的樵徑盡皆掩沒。他全無雪天山行的經歷,茫茫然不辨東西,只顧亂闖。突然腳下一空,身子直往下墮去,刷地跌進了積雪之中。這一失足,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忙爬出雪坑,俯察周身,全無損傷。原來此地乃是一處深谷,谷底積雪足有六七尺厚,將他下墮之力盡數卸去了。可是雷化緣舊愁方去,新愁又起,抬頭看那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兩面的山壁斬絕巉聳,直似刀削,如何爬得上去?
雷化緣生怕再遇不測,絕足不敢亂走。蜷了一刻,耳聽沙沙聲響,巖壁後轉出一個老人,白鬚垂胸,手持一柄拂塵,微笑走到跟前,拉他起身,攜著他手迤邐循谷而行,來到一株大樹之下。那樹枝冠虯茂,樹下幾方平石,乾燥整潔,二人便在石上盤坐休息。少頃,又一紫衣老人,長眉大腹,拄一根藤杖,衣袖飄飄而來,同坐石上。雷化緣只覺胸中安寧,一時不再作出谷之想。三人自此住在樹下,挖黃精生食,雷化緣漸漸抵得飢渴,朔風著身,亦不再寒苦,如是累月。
一日,二老人忽指向雷化緣所坐之石道:“這裡是你前世尸解之處。”取出一條鞋子大小的枕頭,交與雷化緣。雷化緣沾枕即睡,睡不片刻,翻身坐起,叫道:“大奇,大奇!”二老人走到下首處,作禮拜倒,尊稱雷化緣為“樵陽子”,不再直呼其名,禮畢忽然不見。
雷化緣從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坐樹下,耳中隱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尋聲往探,又寂寂然一無所有。又數月,有樵子結伴進谷,經過樹下,見雷化緣敝衣蓬首,形同枯木,識得是童家的打柴少年。早前聽說他雪日入山失蹤,都道早已葬身野壑,沒想到居然在此,要帶他出去,他卻不肯。樵子回鄉提起,說童老爹撿來的孩子在山裡熬了一冬,不但沒有凍死,反而要修成神仙了,一時傳為奇談。
事情漸漸傳到灌縣縣令耳朵裡。這縣令姓景,卻是個愛奇之士,風品行事頗為不俗。聽了這話,趁著空閒日子,不乘車馬,只偕同兩三個幕友,帶著小廝徒步進得山來。一路上涉溪登嶺,快然忘倦,不覺走入幽谷,見雷化緣危坐樹下。縣令問他,何以要選在這麼個荒谷修行?雷化緣道:“我的前世軀體藏在此樹之中,今世方得重生為人。”縣令將信將疑,命隨從伐開大樹看看。隨從操起斧子,尚未砍落,樹幹中喀地一聲巨響,彷彿起了個焦雷,火光迸射,樹幹從中裂開,露出一具遺蛻,身著布衲,髻頂戴冠,腰繫黃絲絛,頭枕一劍,劍身至柔,可以繞指。肌膚完好,竟未腐爛,而頭髮披散,長及丈餘,指甲亦極長,繞足盤旋。遺蛻之側放著口石匣,匣內丹書一頁,文字皆為古篆,迴圈反覆,古奧難明。縣令與幕友等各各驚歎而去,回署後命製造神龕,以奉樹中遺蛻,併為樵陽子修築庵觀,滿縣人敬奉如神。
在本書作者錢希言的時代,雷化緣曾往遊江南,自梁溪至姑蘇,抵杭州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縉紳有幾人聽說過他的名頭,略事接待。雷化緣與衣冠大僚士族子弟相見,亦不為禮,酬對甚簡,只教人於心中領悟宗旨而已。盤桓江南不到一年便去。譚希思譚大人巡撫四川時,曾在青城山下為樵陽子建大通道觀,至今尚存。
樵陽子,姓雷氏,名化緣,或雲孔文進士1之孫,西川大足縣人也。初生時,有僧乞食於母門,遂名之化緣。生二歲,父母相繼死,育於安縣民陳和家。十餘歲,陳夫婦亦相繼死,輾轉寄養於灌縣之青城山下童老家。童老家赤貧,無以自食。化緣衣破腹空,寒色可掬,日日入山採薪以給灌縣人。人見化緣負薪下山,輒持一升半升粟來易,化緣盡所負,與之便去,亦不爭較。往來出入,艱苦不辭,連年如此。
一日天大雪,誤迷失道,陷絕壑中,積雪可六七尺許。望見蒼崖古木,若在雲霄。忽有白鬚老人荷拂而來,引之起,同行亂石間。至一大樹下,相與盤憇。少頃,又一紫衣老人,修眉便腹,策杖於前,亦來共坐。三人常斸2黃精生餌之,漸覺不飢,耐寒輕捷,如是者累月。二老人忽指大樹下而告之曰:“此是子前身脫化3處也。”出囊中一神枕,若履子大,授化緣枕之。化緣既覺,憬然而悟,遂起坐於石上,嘆曰:“大奇大奇!”於是二老人下地作禮而拜甚恭,尊之曰“樵陽子”而不名。後灌縣人驚傳其事,皆呼為樵陽子矣。
徘徊之間,忽失二老人所在。化緣自此誓不出山,終日結跏趺危坐大樹下,耳中隱隱聞隔谷鳴琴之聲,或時聞人語。窮而跡之,寂無有也。又數月,人有逐伴入山採樵,遇見化緣,敝衣蓬首,形如枯木,頹然識是童家負薪兒,相與大怪異之。
事稍稍聞於灌令,灌令景君,愛奇之士也,暇日屏車騎,與二三賓客左右徒行入此山中,涉溪登嶺,攀頓忘疲。乃至大樹下,具問所由。化緣曰:“某前身託此樹中,今乃得復行為人耳。”令遂命伐樹。操斧未下,忽樹中聲震如霹靂,火生其腹,劃然洞開,見遺蛻焉:身著布衲,髻頂戴冠,腰繫黃絲絛,猶未爛。頭枕一劍,劍柔可繞指,發垂覆額,已長丈餘,指爪盤旋,環其足矣。尋復於蛻旁得石匣,匣中有券,其文字皆古篆,丹砂所書,迴圈反覆,竟不曉其義理。景君與賓客左右各各驚歎而還。遂下令制龕,以奉樹中遺蛻,築庵居樵陽子。灌縣百姓龕然敬事之,以為師。
數年前,來遊江南,自梁溪至姑蘇,屆於武林之西湖,俗流多不識。梁溪士大夫稍有一二接遇之者,然其見衣冠大僚士族子弟,亦不為禮,所酬對甚簡,只教人於心地上領悟宗旨而已,世莫能窺其旨者。未一歲而還。譚中丞4秉鉞西川時,嘗為樵陽子建大通觀於青城山下,至今尚存。
1.孔文進士:雷孔文,明四川大足(今重慶大足區)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曾官戶部主事。
2.斸[zhú]:挖。
3.脫化:尸解羽化。
4.譚中丞:或指譚希思,湖南茶陵人,字子誠。曾任萬安、永豐縣令,順天府丞。萬曆二十二年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萬曆二十七年遭參劾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