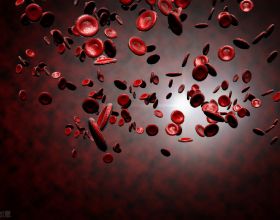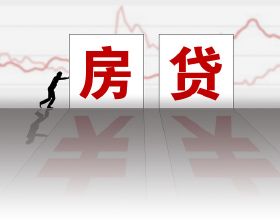我們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節點遇到選擇的時候,那選擇的到底是對還是錯呢?對了還好,那錯了怎麼辦?選擇重要嗎?看看陶勇醫生講的,我是受益匪淺,相信也會對你有幫助的,無論是看病還是人生問題。
學者劉擎指出,現代人擁有自由選擇信仰和理想的權利,但這種自由可能成為沉重的負擔。
從看病這件事便可見一二。在我爸和我小時候的年代,醫生是比較好當的。因為缺醫少藥,病人也沒有選擇的機會。人的平均壽命短,病也不多,藥物基本就是抗生素,惡性腫瘤之類的也治不了,所以要麼就是青黴素能治的病,要麼就是青黴素治不了的病。病人只有“沒有選擇的無奈”,沒有“選擇”的糾結。現在就不一樣了,醫藥科技如此發達,化學藥物就有好幾千種。分子靶向的生物藥層出不窮,養生保健營養品琳琅滿目,微創器械不斷更新迭代,治療方案之間的排列組合多如牛毛。
以前是病少要少,現在是病多要多,用白巖松老師的話來說,進入了患者賦權時代。醫生只是提供建議,由患者自己選擇,然後簽字確認。常見的現象便是患者和家屬要跑好幾家醫院,聽不同專家的說法,然後會發現專家們的說法不盡相同。於是便在網上搜索,打若干電話問清楚,最終選擇一個“騎牆”的方案。整個過程充滿疑問,糾結和痛苦。
有的患者實在沒轍,就會問醫生:“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選擇?”醫生便會回答:“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做選擇。”皮球又被踢回去。沒辦法,花錢和承擔後果的是病人。主題是誰做主,誰負責。其實醫生也感到鬧心,有時比較簡單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變得複雜了。
看病以外,也充滿選擇的苦惱,高知分子一樣難逃“想不明白”和“不會選擇”之網。
我身邊有一個一流院校的狀元級學霸,是個男生,他畢業後去了一家比較清閒的企業,被單位同事帶著,染上了炒股的毛病。先是加了聊天群,每天就在聊天群裡看,不知張三還是李四放出來的訊息股。然後幾個人線下分析討論這些股票,成天討論的不是基本面,就是k線圖,熱衷於從訊息股中選股。他說不討論還好,天天討論都暈了,而且就算是幾個人達成共識。一根陽線就改變信仰。“那怎麼辦呢?”我問他。“我們學不能白上啊,學了程式設計我們就自己開發高頻操作軟體。用軟體炒股,計算機自動分析,買進賣出,不用我們管。”這高科技炒股還真是令人心動,人腦哪算得過電腦?用不了多久,世上的錢還不都得被他們賺光了?“賺了很多吧?”我問他。“哪兒啊?都賠光了。”
幸虧我這些年按著他,要不然他都要抵押房子去補倉,不過每次我倆討論“究竟是選擇重要還是努力重要”時,他都還是堅定的認為選擇更重要。
我想試圖說服他:“我不是說選擇不重要,選擇也重要。努力也重要,但是我們不可能在當下的時間節點。看得清楚未來,所以選擇是沒有把握的。”
他也試圖想說服我:“選擇錯誤的方向,越努力越完蛋,我原來有個同事,在BP 機剛出來那會兒,選擇做BP 機,囤了很多貨,借了不少錢,還貸了款,結果BP 機不行了,手機很快出來了。他就完蛋了啊,借的錢現在還沒還清。”
我不放棄:“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基本都不是一次創業成功的,有的創業好幾次。積累經驗,最後一次成功啊,第一次選擇錯了也不是就沒有機會了。”
他從機率論的角度來反駁我:“創業成功的企業家能有幾個?大部分還是失敗。能活過三年的企業只有3%,最後能盈利,活得不錯的企業也就1%。”
我也不服:“那是因為他們後來放棄了,認命了,沒有堅持到底的失敗。也沒有半途而廢的成功。”
當然我們是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所以到現在基本上他還是在選擇的道路上觀望,希望找到捷徑。而我也在以他鄙夷的蝸牛一般的速度,在醫學雪山上攀行。
雖然我學術進步很快,但我沒有實現他認為的成功標準——財務自由,當然他也沒有。
不過我們都沒有想到的事,這幾年趕上了國家大力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我關於眼科檢驗的技術專利不斷的轉化應用。未來實現財務自由的希望似乎比他大一些,至少到目前來看是這樣。
總想在選擇的時候選最對的,過程既痛苦,結局還令人失望。哪裡會有完美的結局,總會有這樣或那樣不盡如人意之處,所以結果百分之百是後悔。資訊爆炸的時代,正的反的,左的右的,各種建議,各種聲音圍繞在我們身邊。想從中挑選一個最對的,也許這個念頭本身就是錯的。
高瓴資本的掌舵人張磊說:追求大問題的模糊正確遠比追求小問題的完美精確要重要的多。
回到看病這個話題上來。
對於常見病和多發病,因為有專家共識和指南,醫生都是照著標準來的,多看幾個同級別的醫生,其實結果都差不多,病人只是塗了個自己心裡踏實。但對於疑難病,少見病和重症,多看幾個醫生,危害是極大的,因為對於這些疾病的治療並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常常是醫生要觀察一段時間病情的變化,邊治邊看邊修正治療方法,有些摸著石頭過河的意思。如果反覆穿梭在看不同專家的路上,沒有將耐心和時間給到任何一位醫生,結果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奮戰在對抗疾病的前線。
我常和病人說的一段話就是:也許張三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80分;李四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78分;王五醫生的意見最後結果是82分,其實差不多。但如果總是希望從他們的意見中挑出一個最正確的,結果往往是自己混亂了,要麼在不斷看大夫的過程中遇到騙子;要麼最後把自己變成裁判,把這些醫生的意見綜合起來,組合出一套適合自己的方案;即使是從一而終,選擇了其中某一位醫生的意見。但最後也嘗試不滿意——因為從一開始,心中就帶著疑問和不信任,總能在結局中挑出毛病。以此來證實自己最初的選擇不是“最對”的。
下面的這段對話,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熟悉。
“醫生,你說我這個情況最好的結果是什麼?最壞的結果是什麼?要花多少錢?做幾次手術?”
“你這個病是慢性病,過程很長,就像是小孩兒上一年級,家長問老師,小孩兒高考最好上哪個大學,最差怎麼樣,根本沒有辦法回答。因為上學過程中的努力程度學的怎麼樣,不是完全由老師決定的,老師能做到的,只有和學生一起努力,去爭取最好的結果。”
“大概呢?我就想知道大概。”
這種對話場景對三甲醫院的專家來說,每天都在進行。因為醫生們會理解坐在面前的這個患者,太想知道準確的答案,只有這樣才能在不同的醫生的答案中去做簡單的對比。“張三專家說視力最好可以到0.5,李四專家說視力最好可以到0.4,我就選張三。王五專家說要做2~3次手術,趙六專家說要做3~4次手術,我就選王五。錢七專家說要花2萬,賈八專家說要花15000,我就選賈八”。對於這個患者,看病是一道選擇題,選完答案對了就對了,錯了就是錯了,但看慢性病和疑難病恰恰是一張試卷,很多道題需要的不是挑醫生,而是每次在和醫生做選擇的時候,讓他可以放心的和你一起選擇成功機率最高的那個選項。只有這樣,整張試卷的分數才能更高。
看病的時候,很多患者堅定的相信,選擇比努力更重要。但作為醫生的我,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選擇重要,努力也重要。如果是慢性病和疑難病,努力更重要,那是不是就意味著要完全放棄選擇呢?也不是。如果坐在面前的主治醫師沒有把握的話,聽他的建議。選擇去上級醫院,最好是請他幫你做選擇。英國作家詹.豪厄爾說:選擇朋友應當向選擇閱讀的書籍一樣,一要謹慎,二要控制數量。在疑難病面前,我們選擇的醫生朋友是不是也應該控制數量呢?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前董事長兼執行長傑克.韋爾奇更斷定的認為:我們能做的就是把賭注壓在我們所選擇的人身上。
“懷疑”這隻雞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面對選擇時放棄選最對的想法,如果經驗和直覺夠用,就把肯定錯的那個去掉。
剩下的怎麼辦呢?也有胡亂選的,例如我們科的“考霸”朱老師,逢考必過,無論考大學還是考研,選單位甚至“選擇老公的考試”她也以事實證明,她在關鍵選擇上總能成功。我們向她請教經驗,她口吐真言:“三長一短選最短,三短一長選最長。看哪個順眼就選哪個,就憑第一感覺。”朱老師,老公偷偷和我們說:“她就是選哪個就信哪個,可不總選對嗎?”
選擇失敗也是可以翻盤勝利的。例如從常青藤大學歸國的王教授,她是生物學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生物大分子基因修飾後的結構和功能改變上,做了不少開創性和引領性的工作。有一次吃飯時,她和我說起,她上大一下學期的時候就抑鬱了,我驚訝萬分:“你這樣的狀元級學霸,怎麼會抑鬱呢?”她說她根本不喜歡生物學專業,上學的時候整天就是去摘葉子,抓蝴蝶,一點都提不起興趣。我問她專業是怎麼選的?她說:“就是我爸洗車的時候,聽見廣播裡有人說了一句。21世紀是生物的世紀,所以就給我填了生物專業。”我又問她:“現在還抑鬱嗎?”王教授使勁搖頭:“不了,現在可開心了,我後來發現我特別喜歡英語。尤其是生物,英語在國外的時候,老闆說我是他見過的英語最好的外國人。別人論文投稿的時候,編輯一般都是說英語不夠native(地道),而給我的評價卻是太Flamboyant(花哨) 來。”“哦,英文能怎麼花哨呢?”“就是押頭韻啊,就是來回倒裝,定語套從句。讀起來朗朗上口,就和寫詩一樣。”
感情這個王教授選擇了掛生物的牌子,努力幹寫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