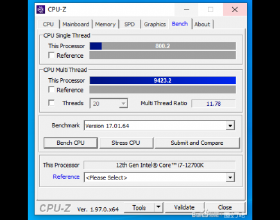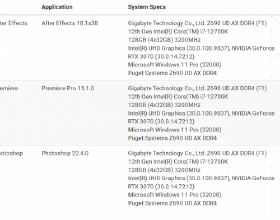(一)洮河林區唐朝立國以後,貞觀之治,農業生產大發展,官吏和駐軍實行屯田制,成丁之年授田百畝,並鼓勵農民前往地多人少之處開墾。唐末,河惶重陷吐蕃。宋熙寧5年(1072年),透過熙河之後,收復熙、河、挑、崛、疊、宕六州,置茶馬司。元代,由山西移民,設立宣慰司,開始屯墾。更是“天下無不可屯之田,亦無可耕之地”。洮河林區洮河沿岸,從卡車以下,河陰可耕之林地已闢為農田。但屯墾面積不大,畜牧業仍占主導地位。所以,洮河林區森林無大的改變。
(二)白龍江林區安史之亂以後,土地兼併日益劇烈,許多農民不得不四處逃亡,依靠開闢荒閒陂澤山原。這一時期,毀林之風波及隴南;到宋代,連徽成盆地南面陡峭壁立的山地也被開墾,人稱“雲下田”。這一時期,森林採伐的規模很大,成為破壞森林的重要因素。儘管如此,在白龍江上游,唐時林多林好,南秦嶺山地東部亦多森林;在今迭部林區,森林比秦漢時期雖有下降,但仍有85%的土地被森林覆蓋。隴南山地仍然是“大山喬林,連跨數縣”。詩人杜甫於乾元2年(759年)棄官西行,度關隴,客秦州,寓同谷,取道慄亭、當房村,越木皮嶺,由白水峽入蜀。他沿途創作的詩歌描繪了隴南山地千姿百態的自然面貌:鐵堂峽“修纖無垠竹”;法鏡寺“冉冉松上雨”;青陽峽“林回峽角來”;木皮嶺“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髮,煥若靈芝繁”。原始森林中群獸出沒的恐怖情景也在詩中得到繪聲繪色的反映:“熊黑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絨又啼”。唐末,河惶重陷吐蕃。宋熙寧5年(1072年),透過熙河之後,收復熙、河、挑、崛、疊、宕六州,置茶馬司。元代,由山西移民,設立宣慰司,開始屯墾。但屯墾面積不大,畜牧業仍占主導地位。所以,白龍江中上游林區森林無太大的退化。兩宋時期山南川北幾度軍旅殺伐,蜀道也屢修屢毀,消耗了沿途某些林木,有的地段森林減耗已較嚴重,尤其是修棧架閣對森林損耗較大。但伐林砍木多在林區邊沿,加之宋代蜀道沿線州府官員較為重視棧道兩旁植樹表路,補種樹木,蜀道沿線森林恢復轉快,許多地方森林景觀與唐代相彷彿。如南宋寶佑六年(1258)蒙古軍勁旅一支越米倉山伐蜀,因米倉道山大林密,榛莽阻道,遂“伐山開道七百餘里”才進入蜀中。另據南宋輿地志書載,當時巴州山野“古木森立”、“萬木森翠”,大巴山南北坡幾乎全為原始林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