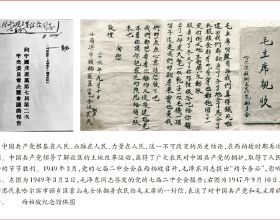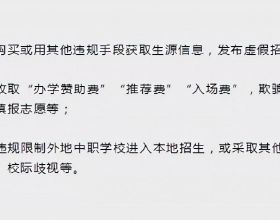許輝/文 黑龍江職業大學張美玉學姐查寢事件,讓本就被邊緣化的職業教育,走向了更尷尬的境地。除了校園內的管理亂象,筆者十年前臥底重慶富士康的經歷發現,圍繞中國職業教育更為底層、多年未決的亂象——濫用學生工,正將中國職業教育推向岔路口。我們不禁要問:當人口紅利耗盡,比農民工成本更低的學生工成為替代性選擇;當無論在職業學校學什麼專業,學生的歸宿都是去流水線上當螺絲,中國職業教育究竟要去往何方?
濫用學生工亂象背後
十年前,筆者刊發了一篇題為《“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職技校批發》的文章,當年那篇報道的背景有兩個,一是沿海地區企業用工成本上漲,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進行產業轉移;二是富士康各地工廠連續發生農民工自殺事件。
筆者臥底重慶富士康一個多月,調查發現,大量使用學生工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解決“年輕、廉價而馴服”的勞動力供應問題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職校學生以實習名義進入工廠,企業不需要像社會招工簽訂勞動合同併購買社會保險,大大降低用工成本。另一方面職校老師會進駐工廠,利用自己的權威協助管理,學生如果有違背紀律的反抗行為,可能招致扣發畢業證的處罰。
這兩方面因素導致在過去十年,學生工問題不但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反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愈演愈烈,無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都在普遍使用學生工。學生工亂象,反映的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普遍實行的師徒制是工人技能形成的來源,而國家統籌的勞動、人事與分配製度保障了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轉向依賴外部勞動力市場,“入廠包工”成為一種新型的用工方式,導致它們投資內部技能培訓的意願不再,師徒關係逐漸被合同關係取代。
此外,出口型製造業普遍採用去技能化的流水線生產技術,工人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就能完成被高度分解的裝配動作,而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大量無技能農民工,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完全沒有必要進行技能投資。
當人口紅利耗盡時,比農民工成本更低的學生工成為替代性選擇。無論在職業學校學什麼專業,他們的歸宿都是去流水線上當螺絲,這就使職業教育中的專門性技能培訓喪失了必要性。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資源投入在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並不均衡。雖然兩者招收的學生比例相差無幾,但職業教育所獲得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職業學校變成了被層層考試淘汰所謂的“差生”收容所,為中低端產業輸送廉價勞動力。
正是在這種命定式的軌跡下,政府和職業學校都主動地參與到“倒賣”學生工的生意中。
比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職業學校為本地用工企業輸送學生工。因為給企業大量輸送學生工,既是地方政府吸引產業轉移的籌碼,又為職業學校賺取不菲的管理費。
這種看似三贏的局面,本質上是權力尋租,對學生工來說,學而不得、學無所用,必然會影響他們一生的職業命運。從整體角度看,政府、企業和職業學校濫用學生工上癮的社會後果,將是勞動力市場陷入“低技能、壞工作”陷阱,並長期處於技能短缺的狀態。
技能短缺困局
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釋出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指出,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受教育水平上有所提升,但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接受過相關技能培訓,僅有5.9%的農民工具有職業技能等級或職業技術證書,而且大多數農民工的職業技能都是透過非正式的培訓方式獲得的,包括“幹中學”“拜師傅”等。
國家統計局2019年的調查顯示,七成左右農民工為初高中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學歷僅佔11.1%,接受過官方組織的職業培訓的農民工僅佔33.3%,具有職業技術等級認證的農民工更是極少數。
經濟學視角把這種現象歸結為技能培訓市場的失敗。對企業來說,技能投資必然存在外部性風險,即一些企業儘管沒有進行技能投資,卻可以透過“搭便車”的方式,從培訓企業獲取所需要的勞動力,從而佔有部分培訓收益而無須分擔成本。
“搭便車”的企業越多,其他企業喪失培訓成果的風險就越大,對培訓投入也就越消極,從而形成一種惡性迴圈,因此理性的企業往往不願意投資於員工的遷移性技能培訓,因為員工的流動性使他們難以確定自己是否可以獲得培訓收益。
但是,技能投資在產生私人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收益,比如公民素質的提高,犯罪率的下降,以及促進整個經濟領域技術的革新和應用。
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能培訓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因此,當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無法滿足經濟增長對技能的要求時,需要政府進行干預。
但濫用學生工的情況表明,各級政府實際上對勞動力市場的技能短缺現象是放任的,或者說干預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因為包括學生工的農民工,長期以來缺乏工資和就業保障,高流動性導致勞動關係短期化。企業對農民工過度剝削,農民工對企業沒有歸屬感,雙方均沒有意願參與技能培訓。
而且,農民工在工作中掌握的技能無法獲得相應的資格認證,“有技術無地位”的困境無法激勵他們持續地積累技能。
儘管改革開放開放以來,中國憑藉“世界工廠”模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奇蹟。
但由於企業和政府長期忽視對農民工的技能投資,勞動力市場一直存在技能短缺,使得經濟增長陷入低附加值、低技能和低工資的惡性迴圈狀態。
這種戰略選擇雖然可以帶來短期的增長收益,但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如果不進行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不但工人無法提升技能水平,企業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也不能相應提高。
因此從技能角度看,中國產業升級本質上是要從“低技能均衡”向“高技能均衡”轉變,使企業的技能需求刺激技能供給,促進勞動者接受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意願和行動。
過去五六年間,中國製造業利用新技術革命的契機加快推進自動化、資訊化和數字化轉型,“中國製造2025”“機器換人”“工業物聯網”等政府提出的頂層設計和實踐指引,在企業層面帶來了不小改變,比如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快速增長,使得中國自2013年以來成為全球工業機器人第一大市場。
另一方面,新的機器裝置需要掌握更多技能和知識的工人的操作和維護,否則資本替代勞動得不償失,因此人力資本的改善是勞動力市場發展的應有之義,只有工程師比重的提高和工人技術能力的增強才能從根本上發揮生產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
從這個意義上說,實施職業教育改革,培養新技術工人是推進產業升級的必然要求。
構建技能形成體制
以筆者長期關注的工業機器人行業為例,隨著汽車、電子、家電等行業應用機器人數量的快速增加,企業對掌握工業機器人以及非標自動化裝置的設計、安裝、除錯、程式設計、保養和維修等技能的新技術工人的需求存在很大的缺口。
按照工信部的測算,如果工業機器人裝機量達到100萬臺,大概需要20萬相關的從業人員。由於這是一個新興行業,存量的工程師不多,因此教育部2015年把“工業機器人技術”列入高等職業教育專業目錄,2016年全國共有240所高職院校以此專業招生,其中廣東省有20多所。
據測算,如果開設工業機器人技術專業的高職院校保持在300所的規模,每年預計會培養3.3萬人,基本可以滿足市場需求。但新設專業往往存在師資薄弱、實訓裝置不足、培養週期較長等問題。
由於職業學校培養存在這些不足,市場化的技能培訓應運而生。過去幾年,一些工業機器人本體生產企業和系統整合商紛紛開辦技能培訓機構,由於在實際專案中積累豐富的經驗,在培訓方面具有技術和資源優勢,教學裝置更新換代快,教學場景不拘泥於書本理論,更貼近現實操作。這類培訓適合有一定工作經驗的工人,幫助他們在短期內快速上手,培訓結束後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並在實踐中積累專案經驗、提升技能。
但市場化培訓的質量往往參差不齊,費用也相對較高。
為激勵和規範工業機器人行業的新技術工人培養,201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工業機器人系統運維員和系統操作員確認為新職業,並於2020年制定國家職業技能標準,為工業機器人領域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提供指引。
在製造業自動化、資訊化升級背景下,工業機器人行業是一個典型的反映技術進步與技能形成關係的例子,而且政府和市場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可以看成是現階段中國構建技能形成體制的雛形。
按照資本主義多樣性理論的研究路徑,發達工業國家的技能形成體制可以根據企業和政府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參與程度分為四類,分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技能形成體制,以日本為代表的分割主義技能形成體制,以瑞典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技能形成體制,和以德國為代表的集體主義技能形成體制。
以此為座標,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後的技能形成體制存在明顯的轉向。
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和企業對技能形成的參與程度都比較高,國企採用師徒制,開辦技工學校,國家提供財政補貼,具有集體主義技能形成體制的特徵。
而在市場化轉型時期,隨著國企改制和師徒制解體,企業逐漸退出對工人技能的培養,而國家參與技能形成的方式轉為透過公共財政支援各類職業學校的發展,具有國家主義技能形成體制的特徵。
他山之石
但正如學生工問題所反映的,僅靠政府有限的投入,職業學校的生源質量、師資和教學水平、以及社會認同度都存在不足,無法適應產業結構升級時代對技能形成的要求。
因此,中國在現階段構建新的技能形成體制離不開企業的積極參與,《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就強調要借鑑德國“雙元制”模式,推進校企合作,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
這意味著新的技能形成體制將重新納入集體主義的特徵,即國家和企業分擔技能培訓成本,由職業學校提供理論學習,由企業車間提供技能實際操作訓練。
對企業來說,投入資金購買先進機器裝置,如果沒有足夠的新技術工人,生產效率的提高將受到制約,因此會有動力承擔對工人的內部培訓,但是隻有解決技能形成中的“搭便車”問題,企業投資的積極性才能真正提高。
在德國企業聚集的江蘇太倉已經形成了一種跨企業培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具體來說,在地方政府支援下,當地職業學校和德資企業合作成立專業技術工人培訓中心,學生在課堂、實訓中心和企業車間接受培訓教育,所學內容主要為行業專用技能,畢業後獲得德國商會的職業技術證書。
這種模式不限制畢業生在行業內企業間流動,但企業間進行有組織的競爭,透過合作協議,一方面進行薪酬控制,實現級差工資的壓縮;另一方面直接控制員工流動,限制挖人,從而降低員工跳槽和企業挖人的動力。未參與技能培訓的德國企業,如果需要聘用技術工人,需要向其培養企業支付一定的費用,這些措施和行規降低了當地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保障了企業進行技能投資的獲益。
當前,中國的職業教育正處在岔路口:一邊是製造更多的學生工,一邊是製造更多的新技術工人。儘管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良好願望是後者,但這個目標並不容易實現。
除了長期投入之外,更需要制度和政策的改善。因此,政府和企業必須放棄短期利益和路徑依賴的誘惑,認識到濫用學生工是一種竭澤而漁。
唯有投資技能,讓學生學有所得,學以致用,既有技術又有地位,才能使未來的經濟發展進入“高技能均衡”的良性迴圈,即企業依賴高素質勞動力擴大市場份額,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階,這將進一步強化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質量要求。
(作者系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