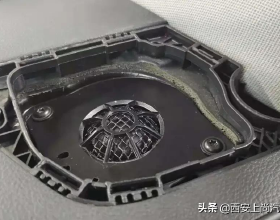回憶以前,我任性妄為的時候,總捨不得讓麟掛電話,讓他把電話裝兜裡,想幹什麼幹什麼就好了,我可以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也可以時不時說上一句,這就算是陪伴了。大多數時候,他總會答應我這些很詭異的要求。有時候在辦公室裡,還跟我直播他辦公的樣子。
但有的時候確實不方便,他得見人,還得去現場,想要和我分開一會兒去忙,我又不讓他掛電話,他就很著急還要安撫我,著急忙慌地給我講原因,我就可勁兒地挖苦他,不給他臺階下。
看他那樣子就忒可愛,是一種笨拙的可愛,也是一種來自於我這裡難捨難分的愛。
回憶以前,我任性妄為的時候,總捨不得讓麟掛電話,讓他把電話裝兜裡,想幹什麼幹什麼就好了,我可以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也可以時不時說上一句,這就算是陪伴了。大多數時候,他總會答應我這些很詭異的要求。有時候在辦公室裡,還跟我直播他辦公的樣子。
但有的時候確實不方便,他得見人,還得去現場,想要和我分開一會兒去忙,我又不讓他掛電話,他就很著急還要安撫我,著急忙慌地給我講原因,我就可勁兒地挖苦他,不給他臺階下。
看他那樣子就忒可愛,是一種笨拙的可愛,也是一種來自於我這裡難捨難分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