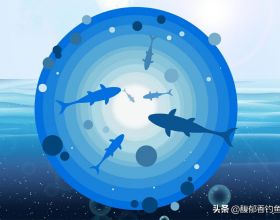▍鹽財經
作者 | 譚保羅
春節前後,2021年的城市經濟資料出爐,給人一種“洗牌”的感覺。
一線城市的四大金剛之中,北京和上海超過了4萬億,分別為4.03萬億和4.32萬億,成為我國最先晉級“4萬億俱樂部”的城市。廣州和深圳同樣保持了穩步增長,GDP分別達到2.82萬億和3.07萬億。
四座城市經濟體量穩步提升,充分顯示了中國一線城市經濟的韌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過去的一年,每一位兢兢業業,同時忍受著城市擴張所帶來巨大通勤成本的工薪族,無不為城市經濟總盤貢獻了微小而不可或缺的份額。
現在,一種觀點認為,從體量上看,一線城市的傳統格局可能已經過時。
首先,北京和上海晉級“4萬億俱樂部”,明顯拉開同廣州、深圳的差距,可以說獨為一檔。同時,後面的重慶和蘇州也追了上來,其GDP分別達到了2.79萬億和2.27萬億,和廣深的差距並不大。因此,一線城市的陣營未來是否應該加入重慶或蘇州?
然而,一線城市從來都不是一個可量化的概念,它包含的東西遠遠超過了GDP。
不同城市兩種“結構”
城市的GDP資料到底是多少,和工薪族,特別是白領、中產階層的關係並不大,真正關係的巨大的是GDP資料中的服務業(第三產業)狀況。
服務業到底有多重要?它讓你的生活更有品質,因為有更好的生活服務提供給你,一出門就有按摩店、理髮店等。顯然,這些只是對服務業的字面理解。
城市服務業的真正價值在於,它決定中產階層是否可以在這座城市安身立命,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找到合適伴侶、組建家庭和安居樂業的機率。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在很多GDP資料非常可觀,甚至有著晉級一線之勢的大工業城市,年輕白領面臨著嚴重的擇偶難。擇偶難,在一線城市不是很普遍嗎?大家要求高而已。不過,在一些大工業城市,擇偶難則是真的難,不是矯揉造作。因為在於,無論線下撮合,還是透過交友軟體、相親網站等線上方式,可以選擇的“合適約會物件”並不多。
長三角的蘇錫常和廣東東莞、佛山無不是著名的工業強市,我曾和其中某座城市一些非常優秀的年輕人交流,他們就遇到了這個問題。當線下有人介紹物件,那麼對方極有可能在另外一座城市,需要坐著高鐵,穿越半個省去約你;如果自己去網路徵友,更會發現,如果某座工業城市GDP是某座一線城市的1/2,那麼這個地方可供選擇的適齡青年的資料庫規模,可能只有那座一線城市的1/5,甚至更少。
這並不讓人吃驚,造成這種不成比例差距的原因,在於城市的服務業。
在工業城市,社會是一種M型結構,即低收入者(工廠務工的勞動者)和高收入者(工廠老闆、拆遷受益者等)佔據多數,他們是“M”字母的兩個尖端,而中間的中等收入者(寫字樓白領、公務員和工廠管理層)群體則出現塌陷,處在“M”的中段,向下凹陷,數量少得可憐。
當然,也不排除一部分中等收入者希望和高收入者進行婚配,然後實現了財富的階層跨越。但現實情況是,擇偶除了財務因素之外,意趣相投也很重要,所以,並不是所有中等收入者都願意和這裡的高收入者進行婚配。於是,中等收入者必然出現擇偶難。
在一線城市,社會則是一種橄欖型結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兩頭小,中等收入者則數量巨大,猶如橄欖球的腹部。這種健康的社會結構,功臣就是發達的服務業,而絕大多數白領的工作崗位都在服務業。
我們看一組2021年部分城市的服務業資料:2021年,廣州的第三產業增加值為20202.89億元,深圳為19299.67億元。蘇州的GDP為2.27萬億,約為廣州(2.82萬億)的80%,深圳(3.07萬億)的74%,但第三產業增加值卻只有11655.8億元,幾乎只有廣州的一半、深圳的六成。
這是巨大的“斷崖式”差距,遠比GDP差距大得多。當然,蘇州是非常優秀的城市,可以說是中國工業的“支柱城市”之一,但它畢竟屬於工業城市,和一線城市並不處在一個範疇之內。
服務業有很多種分類,我們以傳統的兩分法來看,它分為消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前者是指那些直接給個人消費者帶來效用的服務業,生產和消費往往同時、同地發生,比如按摩、餐飲等。生產性服務業則是不像消費者提供直接效用,而是為工業生產提供“配套”的服務業,比如金融、物流、商貿和資訊服務業(包括網際網路)等。
一般來說,產生中等收入者的服務業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但兩種服務業也是互相促進的,只有中等收入者足夠多,那麼才會消費暢旺,消費性服務業才會發展。而消費性服務業發展,又反過來證明城市的工薪族收入殷實,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錯。因此,服務業作為一個整體資料,衡量一座城市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群體結構,無疑有極其關鍵的參照價值。
服務業的價值遠遠不止於此,它還關乎到城市社會結構中的公平正義。
資本與勞動的分配問題
2016年,城市經濟領域發生一樁不起眼的大事。當年,我國首次突破1萬億(10089億)大關。其中,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的個稅收入總和超過4000億元,在全國的佔比竟然達到了40%。要知道,四大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不到全國城鎮總人口的10%。高薪來自高階服務業在一線城市的集中。
在國民經濟的統計概念中,所謂高階服務業並不是一個常用概念,只是透過人們的約定俗成,讓它逐漸開始指代某一些對提升城市能級很重要,對其他產業影響很深、很廣,同時也產生高薪崗位較多的服務業。它們也主要集中於生產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和資訊服務業(包含網際網路)兩大“天王”。
2020年,中國最洋氣的本土投行中金公司高層的總薪酬,約為1.7億元。中金一直都以高薪著稱,也因此引來了不少議論。但和騰訊比,中金還是差點意思。同樣是2020年,騰訊公司13位高層總酬金大約31.64億元,之前的2019年,這一數字約為26億元。
中金特別是騰訊的薪酬,無疑是高階服務業中的“極端現象”。它說明了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越是“高階”的服務業,在分配上,越是會對勞動者有利,而後者主要就集中於一線城市。

2019年6月18日,工銀中金美元貨幣市場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
在這些行業,資本和勞動者之間並不一定是此消彼長的存量博弈,而是一種基於共贏的新型分配模式。此外,由於股權激勵制度的廣泛存在,資本和勞動者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騰訊的總裁劉熾平的年收入最高超過了4億元人民幣,而且,他還持有騰訊的股份,雖然不到1%,但在股價的高點,市值達到了330億港元(騰訊在香港上市),摺合人民幣也差不多280億元。
高薪,它最能代表一個社會對勞動者的尊重。錢,畢竟是這個世界上最不會撒謊的一種存在。當然,炫富式超高薪是另外一回事,並不值得提倡,並要堅決打擊。但適當的,足以維護勞動者體面居住、舒適生活和教育子女需要的薪水,的確可以體現勞動者的地位和價值。而且,有足夠的,有著體面薪酬工薪族的存在,也是一個城市保持核心競爭力的最好體現。
在工業城市,顯然是另一種情形。資本在分配中會佔據絕對的優勢,超高收入的工廠廠主(提供的資本是機器和廠房)和拆遷受益者(提供的資本是建設工廠、住宅的土地使用權)是最富裕的階層,他們決定或影響著分配機制,而工廠工人作為勞動者,在分配機制的構建中並沒有什麼影響力。相對而言,在高階服務業集中的一線城市,勞動者在分配上往往有著更大的話語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一線城市也是對勞動者最友善的城市。

在江蘇省南通市,工人在位於崇川區陳橋船舶配套工業集中區的一家企業內作業
除了以上這種市場化的分配,另一種非市場化的“分配”—公共服務,也是一線城市的獨特優勢。公共服務的底氣來自城市的財力,而一線城市顯然不可能輸。以深圳為例,2021年,深圳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257.76億元,人均財力位於全國所有城市的頭部,這比蘇州高出一大截,遠遠超過了兩座城市的GDP差距。究其原因,既有稅收體制的因素,也有兩座城市產業結構不同,導致經濟“含稅量”有差異的原因。
基於雄厚的財力,以及財力帶來的對基層管理者的激勵和充裕的公共資源,再加上本就相對高的地方治理水平,一線城市能提供中國第一流的公共服務,越來越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新冠大流行的這兩年,這一點表現得更加明顯。
一線城市遠遠不止於GDP資料,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中國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心理期待,投射到城市領域的一種符號,它指向了一種和諧的社會結構,一種讓人滿意的生活品質,一種可以衝破固化並出人頭地的可能性。
對工薪族來說,一線城市無疑最適合奮鬥。當然,這些思考都排除了資產價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