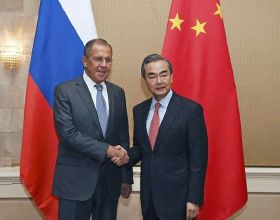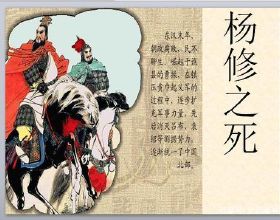前言
今天,可能我要講得有點瘋狂,不過也是基於我本人的一些看法,就如之前講過的共工怒觸不周山的故事,本人猜測就是炎帝后裔中一支善於水利工程的共工部落被黃帝部落打敗之後,破壞上游水利工程,而引發的史前那次大洪水;而夸父追日的故事,很可能就是炎帝后裔的夸父部落,一路追隨共工部落而北上,最後被黃帝部落追上被殺,等等。
當然,你還可以把上古時期,瞭解成為有地外文明,諸如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牛首人身的神農等等都是外星人,而很多故事傳說都是外星人降臨地球的故事,云云。
目前,關於上古時期的傳說故事,基本來源於春秋到西漢時期的著作,不說流傳下來是否還是那時候的原著,就說春秋時期距離上古時期都有好幾千的時間,怎麼就能保障當時的著作就是真實的上古事件呢?更何況一件事件在不同的著作中的描述有些都不盡相同,更甚者,同一件事卻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說法。所以我們也就僅能通過歷史遺留下來的這些碎片,靠自己的理解,分析一下,不能說是正確,卻能為更多的人提供一個更廣闊的思考空間,也僅此而已。
下面正文開始:
鯀治水
我們在上文書講述在唐堯晚期發生了大洪水,唐堯首先是安排了鯀去治水,在《山海經·海內經》有記載:
“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
鯀受命開始治理洪水水患。起初很順利,是因為鯀是盜取了天帝的一樣神物,名為“息壤”,據傳這種土是可以自動增生的,用“息壤”修築的堤壩,洪水長一米,堤壩也自動長一米。
當鯀治水到了第九年的時候,眼見馬上就成功了,就在這個關鍵時期,天帝發現了鯀盜取息壤的行為,大為震怒,就收回了息壤,這樣鯀的治水就功虧一簣,被增高了的堤壩瞬時崩塌,發生了更大規模的洪水,唐堯於是命令當時的祝融(這個時候已經是一個官職了,關於祝融可以參考我之前炎帝文章中的表述),在羽山(今山東郯城縣東北)的郊野把鯀殺了。
鯀之死
關於鯀之死,在《史記.夏本紀》的第二卷中,也有描述:
“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 ...”
說的是在唐堯時期,舜被提拔重用,代理執行天子的職務,按時巡行視察各地諸侯所守的疆土。於巡行中發現鯀治水太不像話,就在羽山誅殺了鯀。而天下的人都認為舜處理得當。
我們之前也說過,當時唐堯並看不上鯀,說“鯀違背教命,敗壞宗族,不行”,是四嶽再三舉薦,唐堯才讓鯀去治水,所以說很有可能唐堯和鯀之間是有矛盾的。在《韓非子》之《外儲說右上·說三》中還有一段這樣的記載: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上面說的是另外一個版本的故事,當時的唐堯要把天下共主的位子傳給舜,但是鯀反對,所以唐堯就把鯀殺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得出一個結論,鯀是在唐堯時期被殺的,而殺鯀的原因可能既不是治水無力,也不是死諫之過,而很可能是唐堯無論如何也要找個藉口除去鯀,所以後世的屈原在《天問》和《離騷》中都對鯀抱著強烈同情之情︰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河海應龍,何畫何歷?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天問》屈原
“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
《離騷》屈原
炎帝與黃帝之戰
從上面的文字中,我們還發現了一件事,就是共工氏,共工氏是炎帝的後裔,也不同意唐堯禪位的決定,也被唐堯討伐。
那麼其實你品,你細品,你再品,我之前就說過炎帝的後裔共工氏與黃帝的後裔從顓頊就開始打,一直打到夏禹時期(屈原《天問》中的”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說的就是在大禹時期,討伐共工氏的傳說故事),所以炎黃之戰並不是簡單的阪泉之戰,涿鹿之戰,共工怒撞不周山等幾場簡單的戰役,而是整個貫穿於五帝整個時期,可以說炎帝部落的後裔與黃帝部落的後裔之間的戰爭就從未中斷過。
世襲的“禪位”
讓我們縱觀整個五帝時代,從黃帝作為始祖開始,大家有沒有發現了一個秘密,就是所謂的禪讓制其實根本不存在,天下共主的寶座其實都是黃帝的後人,一支是以長子玄器為後裔的,先後出現了帝嚳,唐堯等;而另外一支則是以次子昌意為後裔的,先後出現了顓頊,重黎,鯀,舜,夏禹等。所以無論是哪一支最後登上了天下共主的寶座,其實都是黃帝的血脈,那麼這個所謂的禪讓和之後的世襲又有何不同呢?
作為黃帝后裔其中一支的鯀為何死於唐堯之手呢?
黃帝內部的權力爭奪
我們曾經講過,帝嚳殺重黎,如今又是唐堯殺鯀,這兩件事是如此的相似,所以有沒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在黃帝后裔的內部其實也不平靜,為了爭奪天下共主之位,黃帝這兩支後裔也在暗中角力,相互殘殺呢?
所以,這就能解釋為何唐堯為何非要找個藉口殺掉鯀了,但是隨之的問題又來了,那為何唐堯又要“禪位”於不屬於黃帝長子玄器一支,而是和鯀同屬黃帝次子昌意一支的舜呢?
《竹書紀年》中記載: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這個說法和我們之前的認知又是大相徑庭,說是唐堯在晚年已經不能控制下面的諸侯部落了,所以被舜囚禁起來,而且就連唐堯的兒子丹朱都因為舜所設計的重重阻攔而無法與父親相見。
如果說僅是《竹書紀年》一文有這樣的解釋可能說不過去,但是戰國時期的荀子、韓非子亦先後有類似的說法。《荀子·正論》中表述:
“夫曰堯舜禪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是陋者之說也。”
而《韓非子·說疑》中也有記載:“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人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與《竹書紀年》成書時代約略同期的《山海經·海內南經》中也稱呼丹朱為帝,間接否定了堯直接禪位予舜的觀點,“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
更有唐朝著名詩人李白,在其《遠別離》寫到:“堯幽囚,舜野死”的句子。
所以,歷史上被儒家所歌頌的五帝禪位,到底是真還是假,還需要各位自己斟酌了。
結束語:本人的猜想
根據現有的思路,本人大膽做了個猜測:
1. 上古五帝時期,所謂的禪讓根本不存在,天下共主的位子一直是由黃帝一脈牢牢把控。
2. 黃帝血脈以長子玄器為一支,另外一支出自次子昌意,這兩支輪流作為天下共主,但是相愛又相恨,內部其實也是暗潮洶湧,相互角力。
3. 炎帝與黃帝之戰,其實貫穿了整個上古時期,所以華夏一族的融合是經過了千百年才最終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