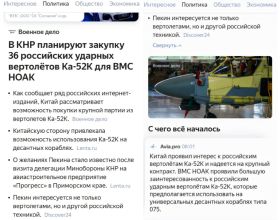一
田野和種植園漸漸消失,駛向昆卡(Cuenca)的汽車開始盤山而上。
最初霧不大,好像一層綠色輕紗,不一會兒卻濃得吞沒了公路。我睜大眼睛盯住前方,導遊哈維仍然邊吃薯片邊開車。汽車一直在爬坡,綠色海洋般起伏的群山偶然一顯。山連著山,一座山峰呈方形佇立於群山之上,間或一塊山石突兀而至,但並不險峻。這一帶已是安第斯山脈北端南坡,作為厄瓜多第三大城市的昆卡就在山那邊的一片谷地裡。
隨著爬升,雲霧開始在山間徘徊。終於爬到了雲彩之上,來到位於山頂的卡哈斯(Cajas)國家公園門口。此地海拔3600多米,天空晴朗,植被不再茂密,樹種也完全不同。據介紹,該公園穿越高山,常綠雲林和數百個湖泊,面積達285平方公里。安第斯禿鷹、大蜂鳥和浣熊(Coatis)等野生動物棲息於此,但人類能進入的只有幾十平方公里。溫帶的山脈到了這樣高的海拔,根本看不到大蜂鳥。厄瓜多面積雖小,但地貌氣候多樣,居然擁有地球18%的鳥類,10%的物種,難怪我們大學的生物老師經常來厄瓜多考察。
沿著木製通道向山下去。雲暗,腳下的那片湖呈深灰色。褐色的茅草漫山翻卷著,那些枯萎的針葉不僅抵禦風寒,也保護了苔原茵綠柔嫩。行不久,就見涓涓細流,此地為亞熱帶高海拔山區,少雨且終年無雪,那些細流全賴苔原植被涵養。這裡已是樹線之上,但因靠近赤道,一種喬木仍能生長。當地人稱之為“紙樹”,其樹皮薄如紙張,長得四腳八叉。苔原上生有多種肉肉類植物,灰綠色,摸上去毛茸茸。一種長長的植物葉小而多肉,頗似一把長柄毛刷,毛刷頂端開著橘黃色的小花。一些印第安人治病的植物,其中的一種類似北美西部常見的摩門茶。我已見過那些結出紅果的常綠植物,第一次看到它們,是在秘魯的印加古道上徒步。
全盛時期的印加帝國曾建立起四通八達的道路,古道的一段也透過此地。我曾徒步的那一段,是從庫斯科走到馬丘比丘,但僅為古道的千分之一。西班牙殖民之前,南美大陸沒有牛、馬、狗等家畜,貨物和資訊傳輸全靠人類徒步。從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到昆卡大概2000多公里,如果傳遞加急雞毛信,投遞員靠接力長跑,8天就能傳到!那時的印加人除了捕獵,主要動物蛋白質來源於今人當寵物養的荷蘭豬。據說秘魯人也吃可愛的駝羊。再考慮到印加人缺乏蛋白質,具有那樣耐力和體質更加不可思議。在某種意義上,南美缺乏歐亞大陸的家畜確實影響了其近代歷史。馬能大大提升戰鬥力,牛解放了農業生產勞動力,可是古老的帝國即使是在全盛時期,也必須將大量的人口投入農耕,因而無暇發展其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皮薩羅征服秘魯的故事,以及《槍炮、病菌和鋼鐵》一書的有關總結。
離開國家公園後,高度一直在降低。沿途山景蒼綠,當看到紅瓦房和香蕉樹時,我們也看到了昆卡城。
二
昆卡全名意即“四條河匯流之盆地“。這四條河分別是託梅班巴(Tomebam-ba)、耶納坎(Yanuncay)、塔基(Tarqui)和瑪查噶納(Machangara),其中的三條源自卡哈斯國家公園。昆卡是繼瓜亞基爾和基多之後的第三大城市,其老城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經過託梅班巴河,沿河草地蒼鬱,花木扶疏。雖臨近赤道,但因海拔2560米而氣候宜人,人稱昆卡有地球上最完美的氣候。進城後,只見窄巷石路,街道縱橫交錯。然而從任何一條街向遠望去,盡頭就是綠色的山坡。據說早年當地一些富裕家庭喜歡去法國,此舉大大影響了當地的建築風格。風格各異的教堂,前有拱廊的西班牙式房子,純白、米黃、磚紅、鵝黃、藍色,民居的紅屋頂與教堂的圓拱尖頂構成了天際線,極為美麗。廣場、噴泉、花卉市場……玫瑰、康乃馨、杜鵑、百合、向日葵……街邊時見挎籃小販,多半是土著女人,賣的大多是水果。女人、貨籃和水果都打理得乾乾淨淨。此地乾淨得出奇,行人的舉止顯示出較高的文化教養,肥胖度顯然比瓜亞基爾低。聽說昆卡有三所大學,大學教授月薪6000美元,比總統略高,而政府僱員的最高工資都不得超過總統。
我們向聖母大教堂(CathedraloftheImmaculateConception)走去,遠遠就看到那三座藍色拱頂。這座教堂建於19世紀,並不古老,但因融合多種建築風格而成為昆卡最醒目的地標。昆卡是南美最天主教的城市之一,市政的座右銘是:“先是上帝,然後才是你”。當地文化保守,虔信和“正確”。據說有個昆卡人送女兒去美國上大學,數月之後,他委託一個去美國的朋友看望女兒,那個朋友回來說:“我帶給你一個糟糕的訊息。你女兒變成了一個……”他的話到此剛巧就被卡車的噪音蓋住了。那父親回答:“太可怕了,我正確地養大她,讓她上正確的學校,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那人接著說:”很可惜,我震驚地發現她賣淫。“那個父親聽了,大大地鬆了口氣 :”我以為你說她變成了一個新教教徒。“英文新教徒”Protestant“和 妓女”Prostitute“前三個字母都是Pro,那個父親最初只聽到前三個字母就緊張了,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是他們的政治正確。
居家陽臺上擺滿鮮花,此地不但街道有些像秘魯的庫斯科,也都是高海拔的山城,然而庫斯科老城的建築大多漆成藍色,固然漂亮,但也有點做作。高海拔區空氣稀薄,水汽也稀薄,但這裡屬於亞熱帶區,三角梅開得很豔,在洛基山中不能生長的馬纓丹在這裡長成了樹牆。走過那面樹牆,沿著階梯而下,一直走到託梅班巴河邊。沿著河邊,垂柳拂面,河上人家的粉牆上,一叢薔薇探出身子。當地人面板細膩,河畔青草柔嫩,讓我忘記身處高原。
在餐館難以吃到足夠的蔬菜,我們走到超市買菜。此地超市與瓜亞基爾類似,以百貨為主,蔬菜放在商店的最後面,很不新鮮。後來找到農民市場,那裡的蔬果十分新鮮,種類繁多,令人眼花繚亂。二樓賣各種湯和新鮮果汁,巨大的一杯鮮榨果汁只要五毛錢。市場上有好幾個草帽攤位,周邊很多村莊編織草帽,草帽的主要原料是龍舌蘭,舉世馳名的巴拿馬草帽最初產自厄瓜多。
在老城閒逛,看到一家英文書店,信步走了進去。店裡賣的多是英文二手書,書店主人叫馬文。聊起來,才知他來自丹佛。我知道一些美國人到國外,首選是哥斯大黎加,馬文也曾在那裡住過一段時間,因不喜歡溼熱的氣候搬來這裡定居。此地說英語的群體近5000人。馬文說住房和醫療保險相當便宜,“醫療保險月費是76美元。我在這裡換了胯骨,手術做得非常好,我只需自付65美元。”告辭馬文後,我又在老城遇到一對美國來的退休人士,她們熱情地請我到家裡坐坐。那對夫妻未到退休年齡,但因病不得不退休,選擇此地主要是因為醫療保險比美國低很多。他們還說厄瓜多的老年人坐飛機都有打折。看得出,他們的生活很快樂。
三
厄瓜多的觀光火車自基多開往瓜亞基爾,行程為四天。很多旅客選擇乘坐最驚險的那一段,始發站是位於昆卡西北的小鎮安勞西(Alausi)。
我們清晨出發,準備趕11點鐘的觀光火車。出城不久就經過阿左格(A-zogues)鎮,昆卡是阿蘇耶省的首府,阿左格已是卡納爾省的首府。這小國居然有22個行政省,估計一個省的大小和美國的郡縣差不多。我想設立這麼多行政區與其地理複雜有關,居住於地理複雜地區的人往往與外界隔絕,自成一體。中央政府對當地居民基本上沒有多少影響力,而居民對中央政府也無向心力。
一路都在攀山,沿途每一片谷地都住滿了人。綠色的山坡上,散落著黃紅相間的民居。城鎮連著城鎮,每個城都有至少一座教堂,而教堂都建在城中的最高處。聖法蘭西斯堂、雲中聖母堂、朝露聖母堂……就像咱們的觀音菩薩。雲中或朝露都是聖母瑪麗亞的不同化身,而不同化身的聖母又各有信徒,一些信徒會特別來此朝聖。南美的教堂煙火氣較重,聖母像都很本土化。我在巴西,看到過印第安人打扮的聖母,計程車駕駛座前放置的聖母戴寬邊帽著披風,懷中抱著穿土著服裝的嬰兒耶穌。得知外子1980年代在梵蒂岡天文臺做學術訪問曾下榻於教皇的夏宮,並不止一次見過教皇保羅二世,導遊哈維說:“當地有個被保羅二世摸過頭頂的孩子被視為吉祥物,如果他們知道你見過教皇,人們會爭著與你握手。”
繼續沿著35號公路向北,越往上走,草木就越綠。草地上徜徉花色不同的牛,農婦在路旁擠奶,鐵皮奶罐放在路邊,一輛收取鮮奶的車子剛剛駛過,顯然每天都有車來收取牛奶。這裡的牛顯然比養牛場的牛快樂,牛奶味道或許更加鮮美。沿途的住房大多是紅瓦黃牆,景色不輸瑞士,看起來居民生活穩定富足。這條路是泛美公路的一段,從理論上說一直向北可達阿拉斯加。西班牙人殖民南美之初,道路始於哥倫比亞的海濱城市卡塔赫納,繼而順著安第斯山在高原上延展,泛美公路基本也是循著老路而建。
遠處山窩裡白茫茫一片,那就是我們從瓜亞基爾到昆卡時看到的水霧。這片水霧從太平洋上飄來,逐漸向東飄升,等到傍晚就飄到這一帶了。霧林區幾乎每天都有霧氣,無所謂旱季和雨季。我記得奈米比亞沙漠裡的植被也是靠海洋飄霧存活,植被滋養了羚羊等動物。待過了霧林區,山谷又是一片褐色。
還有半小時就到阿勞西,前面卻開始堵車。這條路車輛稀疏,難道是出了事故?車行緩慢,20分鐘過去了。哈維前去檢視,回說,是阿勞西的民眾正在示威。
以前訪問利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時,我們都遇到過示威遊行,卻未想到這樣偏僻的地方也會遭遇示威。為了趕上觀光火車,警車為我們開道,但仍然無法駛過遊行隊伍。最後全車人棄車步行穿過遊行隊伍,再搭乘另一輛車趕到火車站。走進車廂後,又開始等待,等來所有乘客,火車鳴笛出發。
一駛出小鎮,旋即攀高而上。在一片灰色和深淺的褐色之中,仙人掌長到幾米高,粗大的龍舌蘭兩人都無法合抱。肉肉植物的根鬚長長地垂掛在懸崖絕壁上,其生命之頑強令人感嘆。據說雨季過後,山間會有萬花搖曳湧動。
山勢險峻,站在車廂裡勉強能看到山底那一線河流。雖然厄瓜多的面積與廣西相若,僅有28萬平方公里,但有高山、海洋、熱帶雨林和群島。從瓜亞基爾到基多的直線距離只有270公里,但在高速公路上要行駛一天。地形複雜,很難以公里數作為行程的時間引數。
1908年前,厄瓜多僅在海岸線上鋪設了鐵路。1895年,總統艾洛伊·阿爾法羅(EloyAlfaro)決定將海岸鐵路延伸,最終連線瓜亞基爾和基多。然而,從河口城市到海拔3000米,那意味著平均每公里要上升10米,其中最具挑戰就是我們乘坐的這一段。這一段路只有12公里,但地勢卻直下500米,因其險峻而被稱為“魔鬼鼻子”。1908年6月,鐵路終於通車。其後幾十年,該鐵路是厄瓜多運輸的主幹線。1990年代後,因高速公路修通,鐵路逐漸衰落,近年僅用於觀光。
快到魔鬼鼻子時,山勢已成絕壁,火車行駛在迂迴式軌道上。1930年代乘坐列車的德國人魏特默記述道:“我們爬升得更高,隨著火車駛過陡峭的山坡,我們有時會從車窗六至七次地看到下方的同一風景。有一次火車突然停在懸崖邊,然後開始向後衝入山谷。我想會被扔進下面的深淵了。突然它停止了,然後又猛地向前移動。如此遽停前進後退好幾次,列車長看到我臉色蒼白,解釋說一切正常,我們正在經過魔鬼的鼻子。”在經過數次進退之後,我們也終於下到谷底。眾人下車與魔鬼鼻子合影留念,並在車站觀看土著人歌舞。車站的牆上貼了鐵路圖和說明,記得北京八達嶺也修過類似的軌道,但好像並未自稱:“世界上最美妙和最勇敢的工程之一”。那天翻看雜誌,其中曾將基多的殖民前藝術博物館與盧浮宮、冬宮、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並列,令人莞爾。
四
下午兩點,我們從安勞西返回昆卡。出發不久,霧氣就上來了,樹木房屋時隱時現。一縷陽光透過霧氣,綠色中屹立著一座座紅瓦黃牆的農舍。那些房子建得方正結實,露臺或鑲於屋前或置於樓頂,個別的還有門廊,總之都是典型的西班牙風格。在一個公共洗手間不提供手紙的國家裡,這些住房已經相當好了。
可是,那些房子總有點不對勁兒。什麼地方不對勁兒呢?噢,原來它們用的是辦公大樓的藍玻璃。奇怪,這山野難道也需要這樣保護隱私嗎?反光玻璃不僅顯得窗戶很小,而且有點兒賊光四射的感覺。哈維似乎看出我的好奇,開口說:“你注意到那些玻璃了吧?這些房子的主人現在大都在美國。當年他們出國時還以為紐約是一個國家。到了那個“國家”,看到了摩天大樓的窗玻璃,以為那就是時髦。匯錢回來建房指定要那種玻璃,不是必要,而是炫耀。”我問:“房主不在這裡住嗎?”“他們大多是非法移民,不敢離開美國出境,也許以後會回來養老。我知道哈維也有美國綠卡,就問他:“美國有多少厄瓜多移民,包括非法的?”“大概100萬左右吧。”“啊,這麼多呀!我感覺在南美國家中,厄瓜多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比較好,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往美國跑呢?”“主要是因為1999-2000年厄瓜多實行美元化。”
他繼續介紹著,1999年之前,厄瓜多的貨幣是蘇克雷(Sucre)。1950年代,美元對蘇克雷的匯率為1:15,1990年代初匯率開始大貶,初期為1:800,5年後貶到1:3000,到了2000年1月則貶為1:25000。 為了穩定幣值,當時的總統宣佈採用美元,廢除蘇克雷。
“採用美元是正確的。”哈維說,“但美元化的過程中,出了大問題。宣佈兌換後,一些人沒能及時兌換,待他們想換時,銀行又不給換了。後來同意兌換,但只能給兌換卷。這樣一來一去,一些個人財產被剝奪得只剩原值的2.5%。全國因此爆發了抗議,民眾包圍了總統府,總統只得乘直升飛機逃跑。那些偷了老百姓錢的銀行家都跑到美國去了,跑到美國去的還有因此而破產的老百姓”。那時厄瓜多人口剛過千萬,也就是說十分之一的人口跑到美國去了,其中大多數為非法移民。哈維指著一座低矮石頭房子說,“之前,大多數人住的就是那種房子。跑到美國後,匯錢回來蓋了新房子,以前的舊房子就當牲口棚或工具間了。”記得以色列建國時也是靠外匯發展起來的。南美國家獨立後,政治經濟仍直接受大國影響,比如英國的債務、美國的聯合果品公司在瓜地馬拉的巨大影響力。再考慮到後殖民時代南美各國的內戰和國家之間的戰爭,各種軍事政變,厄瓜多的換幣危機已經算是很小的災難和不幸了。
哈維又說:“現在我們的醫療大學教育都免費,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但和委內瑞拉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他們很腐敗。”“查韋斯開始執政時做得很好,資源是拉美第一,後來越來越糟。其實即使不贊同美國也沒有必要反美,薩爾瓦多未必贊同美國,但和美國搞好關係,美國援助多,老百姓的日子好過。”
霧越來越濃,到達印加之牆(In-gapirca)時,能見度只有十幾米了。在印加人到來之前,此地的原住民為卡納爾(Ca?ari)人。據說他們的祖先於公元前500年就在此定居了,印加人透過戰爭與和親征服了當地土著,但那時的帝國也是強弩之末了。至今這一帶仍有很多卡納爾人,他們戴著很像呢帽的羊毛帽子。
濃霧中,我們在遺址徘徊。透過霧氣稍散的瞬間,我看到祭壇之下竟是險峻的深谷。曼陀羅花開得正豔,那花大多數是白色,但這裡有黃色、紅色和橘色,據說這種花有迷幻作用。雖然此地是厄瓜多最重要的印加遺址,但建築規模、複雜程度根本無法與秘魯的馬丘比丘相比。
回到昆卡已是夜幕低垂。次日清晨,我們從昆卡乘長途汽車翻山越嶺返回瓜亞基爾。
(記於2019年9月28-30日。作者現居美國佐治亞州。主要作品《恆河:從今世流向來生》、《此一去萬水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