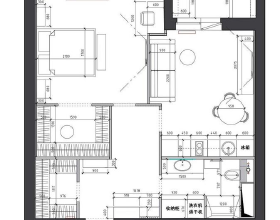我十四五歲的時候,眼睛有點兒近視,想買一盞檯燈。母親給我錢,讓我到鎮上去找姨夫幫著挑選,免得吃虧。
姨夫在中學當會計,吃國家糧,對鎮上很熟悉,在莊稼人眼裡算是有能耐的人。鎮醫院東邊有排門面房,第一家就是百貨店,姨夫帶我到店裡去。
老闆娘身材微胖,正在理一捆電線,把鬆散的大圈纏為緊密的一團。看到姨夫進門,臉上堆滿了笑,熱情地寒暄,很快明白了客人的來意。手裡的活似乎不能中途停下,她對姨夫說:“兄弟,你幫我撐著線,我快點兒纏完,給你拿檯燈。”
姨夫該是店裡的老主顧,嘴裡說著“我試試”,就伸出兩條手臂,去撐大線圈。老闆娘叮囑:“你小心撐住,別掉在地上,掉下來可就亂套了。”我在旁邊悄悄看著,感覺跟繞毛線有些像,一圈圈長線得慢慢理,就怕打結。
譁——啪!線圈冷不防從姨夫手臂滑下來,掉到地上。老闆娘臉色頓時變了,高著嗓門說:“這就是做買賣人的下賤!這就是做買賣人的下賤!”她連說兩遍,聲音顫抖著,像發怒,也像哭泣。
空氣彷彿凝固了,我心跳不由得快起來。畢竟起因是我要買檯燈,對糟糕的局面該負一分責任,就呆呆地站著,一聲也不敢吭。
“想不到還挺沉,滑下來了。”姨夫訕訕地陪著笑,彎下腰去整理線圈。不快歸不快,倒也沒傷和氣,過會兒老闆娘說話又軟了下來。姨夫幫我選中一盞綠色塑膠外殼的檯燈,離開了百貨店。
線圈弄亂了,接下來要理順,想必得花些工夫,假如不幸打成死結,店裡可就賣不出去了。當然也可能繞好。正是讀初中的懵懂年紀,我很納悶:老闆娘在鎮上開店做買賣,不僅脫離了農村莊稼活,比那些開三輪車賣菜的流動商販也強得多,當然是富貴人體面人,怎麼能說是“下賤”呢?
檯燈很好用,我就著光亮看書、做題,度過了少年時代。
“這就是做買賣人的下賤!”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耳邊不時響起百貨店老闆娘的吶喊,感受到生活的複雜滋味,得到警醒和寬慰。
那時,老闆娘看似作為生意人抬舉姨夫的體制內身份,更多可能是展現店家面對顧客、女性面對男性時的弱勢地位吧,用憤激之辭傳遞不滿,用自我輕賤表達抗爭。很難說這是她做買賣的策略,卻多少包含著生存的智慧。
參加工作後,我常怕自己的倨傲和無心之失給別人帶去傷害。旁人託的事情,能做則盡力做,做不到就索性推辭,讓對方另想辦法,別耽誤了。學生找來調課,理由充分就趕緊簽名。以前當記者,常遇到寫了稿子卻發不出的情況,那就事先把難處跟受訪者講明白,降低心理預期,而不要打“肯定可以發表”的包票。
我也曾像老闆娘一樣被人辜負,心裡覺得憋屈。業內名家幾次推遲見面,好不容易定好採訪時間,卻臨時爽約,且沒有一絲歉意,讓人氣悶。上面點題約稿,費大力氣採寫出來,最後卻沒發表,難免心生怨念。但我不能像老闆娘那樣大喊,最多嘟囔一句“早知後來何必當初”,然後收拾心情投入新的工作。
“這就是做買賣人的下賤!”在歲月的流逝中,老闆娘的告白清晰如昨。那是弱者在受傷後的自我保護,也是對信任與尊重的熱切呼喚。人在旅途,多有求人和幫人的時候,總歸要放平心態,不怠不矜,多站在對方角度想一想。
後來我離開家鄉去讀大學,檯燈就收起來,放到寫字檯下的櫥子裡。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常想起那盞綠塑膠殼的檯燈,想起老闆娘說過的話。
(作者繫上海音樂學院教師)
《中國教育報》2021年07月17日第4版
作者:董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