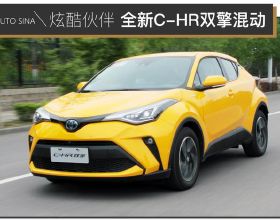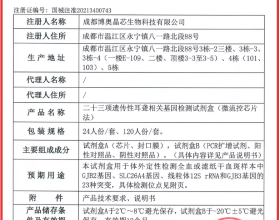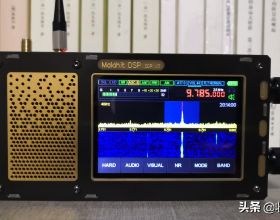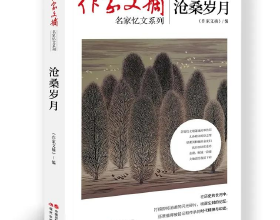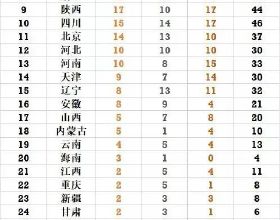劉遠舉,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上世紀80、90年代,主流輿論上經常見到一個批判性的概念:“小皇帝”,指那些被家庭嬌生慣養出來的驕橫的獨生子女一代。如今,時間過去40多年,這個詞很少見於中國輿論了。在搜尋引擎上搜索“小皇帝”三個字,返回的結果,都是歷史影視劇中的角色,不再是關於獨生子女的圖片與文章。
其實,當下的中國社會,一孩家庭仍然是絕大多數。那麼,為什麼在輿論中“小皇帝”這個概念卻消失了呢?
▌從優生到優育
1979年,中國政府開始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當年,610萬個家庭領取了獨生子女證。第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公開信闡述了控制中國人口增長、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這個月,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12月,寫入憲法。中國開始從國策層面,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
少生、優生了之後,自然要優育。某種程度上,優育,是計劃生育政策衍生出來的內涵。
一方面,對國家來說,優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手段;同時,優育也是制約人口發展的重要手段——精養了,單個孩子投入更大了,自然就不能多生了,“生不起”了。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當下所謂的“生不起”,其實是計劃生育政策長期影響家庭決策的結果。如果說“不準生”是一種在明處的制度,那麼,透過改變家庭養育模式,導致“生不起”,則是一種在暗處的長期的潛移默化。
優生優育,其實,更準確地說,是“獨生精養”。“獨生”則必然“精養”。小皇帝般的養育,是一個家庭對計劃生育本能的反應。
80年代恰好是物質生活水平迅猛提高的時代。那時的中國家庭已經初步有能力給孩子更好的物質條件。
1981年,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91元, 1990年,則達到了1510元,10年間增長了3倍多。此外,開啟國門後,湧入的新技術、新家電帶來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手電筒、收音機到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中國人在十來年內完成了西方上百年的程序。迅速增長的物質條件,生活一日千里爆發式的改善,必然體現在養育孩子方面。
其次,物質條件之外,養育孩子的精力、人力投入也大幅度增加。當時的輿論形容小皇帝,都是說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媽媽,6個人圍繞一個孩子轉,孩子享受著皇帝般的服務。其實,這就是如今的“六個錢包買房”的前世,但如今,這不再被視為“異常”。
▌“小皇帝”概念的出現
與迅速變化的物質條件以及家庭本能式的改變養育行為模式相比,社會觀念的變化更加緩慢。上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觀念對當時養育行為的改變,是迷惑而不解的。對這種養育行為的批評隨之在主流輿論出現。
1985年3月18日,美國《新聞週刊》刊登了題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借獨生子女父母之口,第一次給這一代獨生子女戴上了“小皇帝”的帽子:“拜倒在孩子腳下的父母稱孩子們是小皇帝,中國的報刊稱他們是嬌生慣養的孩子。中國實行‘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以來,已有3500萬孩子出生。小皇帝們指的就是這一代孩子。”
這篇文章並沒有被認為是惡毒攻擊,相反得到了贊同。短短11天之後,《工人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的譯稿。
第二年,1986年,一篇題為《中國的“小皇帝”》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報告文學,向全社會發出了警告:凌駕於家庭、父母及親屬之上的“小皇帝”,已遍及千家萬戶,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家家戶戶都有一個“小皇帝”。
這篇報告文學廣為流傳,還被拍成電視劇。一時間,獨生子女是“小皇帝”、“小太陽”的說法廣為流傳,並迅速在人們頭腦中形成概念,成為千萬人印象中獨生子女的代名詞。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客觀地說,這篇報告文學行文情緒化、觀念幼稚、甚至在事實上存疑。但無論如何,它是當時輿論的一個典型例子。
當時一般認為,人有兄弟姐妹,生活中必須學會分享、妥協、與人相處,但獨生子女的成長環境,缺失了這些密切的、同輩的關係,並不是一個人類生活的“自然”狀態,所以性格培養必然受到影響。80年代的社會輿論中,對獨生子女的印象是:自私、自我中心、不顧及他人感受、驕橫等。
不過,這種觀念被後來的研究證明是一種刻板形象。後續嚴肅的研究表明,獨生子女家長與非獨生子女家長在溺愛孩子的行為表現上,並不存在顯著差異,獨生子女並未表現得更糟糕。
所以,80年代的“小皇帝”概念,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主流人群,也就是40、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對80、90年代家庭養育行為模式的不理解。他們無法用過去的生活經驗來解釋計劃生育導致的家庭養育行為改變,無法理解這種高投入的精養模式。從這個意義上,當時輿論對“小皇帝”現象的批評,反映了計劃生育在改造中國人的養育觀過程中的價值觀衝突。這是傳統社會養育觀對計劃生育的最後倔強的反抗。
那麼,為什麼小皇帝的概念逐漸從輿論中消失了呢?
▌雞娃崛起
實際上,“小皇帝”概念所指的高投入模式從未改變,反而變本加厲。如今,父母、或者說4-2-1家庭體系,對孩子的投入更大,包括更好的物質條件,名牌衣服、國外旅遊。第一代獨生子女小時候,還會自己上學放學,現在的孩子由家長接送已經是標配。
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城市交通繁忙,社會更加複雜。其實,這些解釋都是站不住腳的。80年代隨著城市開始快速擴張,出現了大量的公交族中小學生,單獨坐車上學。如今,隨著就近入學的落實,這樣的學生已經大大減少。治安方面,80年代的治安,遠不如攝像頭密佈的今天,家長接送的必要性,理應是減少,但在今天,即便家校距離在1公里之內,紅綠燈更加完善,治安更好,家長仍然保證接送。
不過,沒人覺得不妥,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了。社會觀念雖然會慢於政策的變化,但終究觀念是柔軟卻堅韌的,它會遲到,卻從來不會缺席。
除了習慣之外,小皇帝概念源於一個時間上的錯位。計劃生育改造了當時中國家庭的養育行為模式,但還沒來得及改造其教育行為模式。孩子是4-2-1體系親子之愛的唯一物件,享受到了其中的好處,過著皇帝般的生活,似乎是純接受而不用付出的。
不過,如同獨生子女成為家庭所有愛的物件,他們也必然會承擔起作為家庭期待的唯一物件的責任,隨著家庭教育行為模式被計劃生育改造,家庭也有更大的期待,高期待模式成為中國社會主流。
這個期待的壓力從幼兒園階段就已經開始,逼迫孩子為升學考試做反覆的應試訓練。如今的家庭在各種課外輔導班上投入了巨大的金錢與精力。即便消滅了課外輔導,很大程度上無非變為家長自己輔導。在這種觀念之下,家庭教育開支迅猛增長,一個年收入30萬的家庭,每年拿出10萬元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上,已經不會被認為是一件奇怪的事,
規定的生育行為之下,產生了畸形的養育觀,最後,再配上畸形的期待觀,獨生子女們開始承受家庭更大的期待壓力,更苦更累,也就不再有做皇帝的感覺了。其實,換個角度看,這才是真正“做皇帝”的感覺:一方面享受最好,另一方面也需要承擔壓力,肩負責任。
所以,小皇帝的概念,始於社會最初對計劃生育導致的精養行為的不理解;然後,被計劃生育導致的“高期待”所消滅;最後,隨著中國人的習以為常、見慣不怪而消失。
▌現實基礎消失後的刻舟求劍
無論是精養觀、還是高期待,這些觀念、行為的基礎只有一個,那就是計劃生育。
法律、社會政策很多時候走在習俗、觀念的前面,因為它可以用一紙白紙黑字的檔案讓人改變行為,但觀念的形成需要漫長的時間。當初,“小皇帝”概念背後的實質是社會不習慣、不適應,發展形成批判。20年後,這個觀念消失。人們不再不解與困惑,習慣了精養、高期待,甚至久而久之,將之視為合理、不變的生活經驗,形成一種“生育理性”。

▲ 景軍主編《餵養中國小皇帝》圍繞食物、兒童、社會變遷等五個議題展開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遺憾的是,政策變了,觀念的基礎變了,過去的觀念就成了刻舟求劍。
當初,在眾人之前優先察覺到計劃生育對未來的影響,並率先採取精養、高期待模式,採取高投入的家長,是有先見之明的。比如,第一代獨生子女大多於80年代出生,如今大約40歲左右。在這個年紀,如果有高學歷、特別是出國的經驗,比起同齡人來說,就更有優勢。而到了2000年之後,才從眾地採取高投入的家庭,送子女留學,在就業市場上能獲得的優勢已經很小,而到了如今,海歸失業已經成為一個現象。
如今,政策再一次在短時間內改變,隨著2016年全面開放二胎,2021年放開三胎,以及一系列刺激生育的政策,短短六年間,中國的生育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的觀念已經沒有了現實基礎。然而,與上一次一樣。觀念始終會落後於現實。中國人放棄精養、高期待模式,或許還需要20年。當“雞娃”這個概念消失,才意味著中國人的生育觀、養育觀告別計劃生育的影響。
(頭圖出自電影《末代皇帝》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