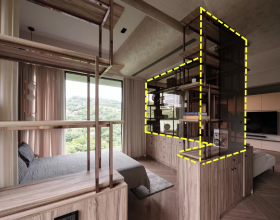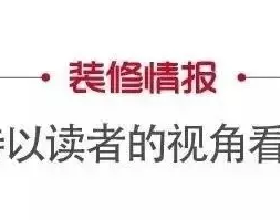今天我們來講蘇軾的寒食帖,乍一看感覺這字寫得不咋滴,亂七八糟的甚至還有點醜,但它卻是天下第三行書。
排名第一、第二的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和顏真卿的《祭侄文稿》。
其實,蘇軾的字並不一直這樣的。
你看,這幅字的飽滿。
這幅字的骨架。
還有這幅字工整中又帶著飄逸靈動。
但唯有這幅醜醜的《寒食帖》獲得了行書第三的排名。
寫寒食帖的時候,蘇軾被貶黃州已經有三個年頭了,他從一位天之驕子政壇新秀,一下子跌落到了凡間泥土。
他不得不像普通的農夫那樣,在田地間耕種,日子過得很艱難,心理也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有不甘,有憤懣,也有深深的落寞和無力感。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
打我被貶黃州,已經過了三個寒食節了。
寒食節通常在清明前兩天,此時節的黃州陰雨紛紛,透著陣陣涼意,所以他接著說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今年的雨水特別多,接連兩個月都陰雨綿綿,如同深秋一般蕭瑟。
農曆三月份的陰雨確實是多,但是否真得兩個月都在下雨,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只不過蘇軾那份悲涼的心情一直伴隨著他,使得他覺得這種天氣始終是淒涼的。
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
蔣勳老師曾說過:
他絕對不是在講花,我覺得他在講他自己,......,我覺得蘇東坡領悟到,原來自己一直把自己當花,你當花你就嬌貴,你當花嬌貴就不能夠下來。
他認為蘇東坡領悟到了自己一直把自己當花,你當花你就嬌貴,就不能下來。
但是再看看現在的自己,哪裡還是那嬌貴的鮮花兒,自己已經落入到了泥土之中。
回到泥土之中,他才發現自己並沒有那麼嬌貴,沒有特別之處,自己的生命與花的生命並沒有什麼不同,終歸要落入泥土之中。
龔自珍有兩句詩說得好,他說: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他認為花只有落入泥土之中,才算完成生命的一次輪迴,生命才得以完整。
我們再看花和泥這個兩個字,有一個線條把這兩個字聯絡在一起,花與泥土糾纏在一起。
在潛意識中,蘇東坡或許覺得自己現在如同這筆下的花一樣,迴歸到了泥土之中,褪去光鮮而返璞歸真。
但是蘇東坡又覺得自己不應該以這種被貶的方式回到泥土中,被貶謫實際上是一種無奈,所以他心中有不甘和悲涼。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
你看著四個字,”空、寒、破、溼“,透過這四個字,蘇東坡心中的那份淒涼一下子顯露出來,他在寫的時候連破字都沒有寫完整,是殘缺的。
作為文人,蘇東坡的情感是細膩的,由陰雨之境,而生淒涼之情,古來多少文人皆如此,只是蘇東坡透過”空、寒、破、溼“這四個字,把心中的那份悲涼刻畫地更加細膩,更容易讓人產生共情,我們在讀到這兩句的時候,也會感覺很慘很冷。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接著他抬起頭向窗外望去,正好看到烏鴉叼著尚未燒完的紙錢,才想起今天是寒食節。
到底是寒食節勾起了蘇東坡心中的悲涼意,還是他心中的悲涼意應了寒食節這時的景呢?
我們知道“境由心生”,倘若沒有蘇東坡心中的那份悲涼,就沒有寒食節的淒冷,或許就變成了“春江水暖鴨先知”。
接著他說,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國和家是文人心中最重要的情結,可是自己想要報效朝廷,卻君門深九重,連門都進不去;想要回鄉祭拜父母,可自己自由受限,想回也回不去。
很無奈,很痛苦,同時也有一些怨恨。
你看君前面這個字”紙“的最後一邊拉得很長,像一把鋒利的劍,直指這個君字,同時這個君字又寫得很小,就像被這把劍逼近了逼仄的角落。
因為他對這個君有怨言,正是這個君聽信讒言把他貶到了黃州這個地方,所以在他心裡這個君更像一個小人。
像“紙”這樣把最後一筆拉得很長的,還有“年、中、葦”。
他就是要透過這種鋒利的筆畫把心中的不滿宣洩出去,而不是我們書法中通常所說的要藏鋒,此時的他是鋒芒畢露的。
回過頭來再看,雖然這篇《寒食帖》看上去沒有章法,但每個字都帶有蘇東坡的情緒。
即便不懂書法,你也能被字裡行間的情緒所感染,這就是藝術的魅力吧,能夠讓人感受到彼時彼境蘇東坡心裡所想,也能夠在此時此境感染到自己,產生與作者的共情。
這或許就是這篇《寒食帖》位列天下行書第三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