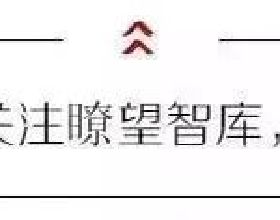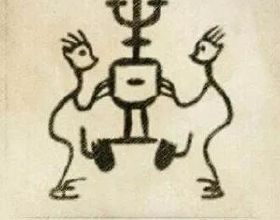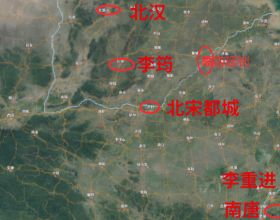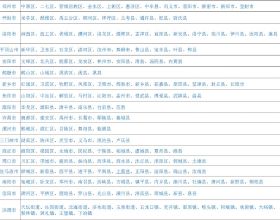文/Abram Brown
一週前,Peter Thiel宣佈他將卸任一個已經擔任了18年的職位:Facebook母公司的董事會成員。與此同時,他正在籌劃一個派對。
這場派對將在幾周後舉行,地點是他在邁阿密海灘附近的島嶼莊園,那是他一年前花費1,800萬美元購買的一處海濱聯排別墅。這是一場為Blake Masters籌集競選資金的活動,後者是一名Thiel的門徒,正在競選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活動的邀請函已經發出,邀請的物件都是一群支援特朗普的共和黨有錢精英,並且這次活動的出席人是分等級的:VIP從下午6點開始入場(每人捐款2,900美元),其他派對參與者6點45分入場(捐款1,500美元)。(VIP有更多的時間和機會與Thiel和Masters交流。)以及還有第三個等級:捐款5,600美元即可成為聯合主辦人。
這至少是Thiel第二次在邁阿密為Masters舉辦募捐活動了。去年12月,就有大約100人聚集在Thiel的泳池邊喝酒,拍照。CNN評論員Ana Navarro以及北卡羅來納州國會議員Madison Cawthorn均出席了那次活動。對沖基金創始人James Koutoulas也來了,還在他的藍色夾克上彆著一個巨大的“LGB”徽標。(“LGB”是反拜登的口號“加油布蘭登!”(Let 's Go Brandon)的縮寫。去年,Koutoulas還推出了一款以LGB為品牌的虛擬貨幣。)
Koutoulas說:“我認為Blake具備很好的技術能力組合。”Blake Masters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是Thiel資本(Thiel Capital)的管理人,該公司的投資組合包括線上貸款公司SoFi和新型電動水上飛機制造商Regent。此外,Masters還管理著Thiel基金會(Thiel Foundation),該組織每年向225名年輕人發放助學金,以取代他們的大學教育。Koutoulas認為華盛頓的官僚們缺乏Masters那樣的經驗。他感嘆說:“政府裡有那麼多人對技術根本沒有基本的瞭解。”
對於那些對Thiel離開Facebook後的生活感到好奇的人來說,答案很可能就藏在這些在南佛羅里達舉辦的這些派對裡。54歲的Thiel仍然非常富有(福布斯估計其身家為27億美元),很難想象他會完全放棄自己從20年前就開始建立的創業投資帝國。這些投資構成了他財富的基礎;同時他把這些錢注入共和黨政治,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以特朗普為中心的共和黨的領導人物。但很明顯,他正處於一個拐點:不僅是他在上週一宣佈了自己將離開Facebook,還有他在政治上的激增的開支。僅僅算上可公開追蹤的資金,Thiel在過去兩年中已經為競選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的候選人花費了2,200萬美元——是他在2015年和2016年政治花費的五倍。Thiel的大部分政治獻金都花在了兩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上:一個支援Blake Masters,另一個支援J.D. Vance,後者是《鄉巴佬輓歌》(Hillbilly Elegy)一書的作者,正在爭取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席位。與此同時,矽谷的民主黨捐贈者據說正在撤回捐款,比上一屆總統競選週期的捐款更少,因為他們對這一屆競選打敗了特朗普感到滿意,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於讓中期國會候選人自生自滅。
近年來,Thiel讓自己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個謎:少言寡語、難以捉摸、神秘莫測。(他沒有回覆記者就本文置評的請求,這倒很是符合他一貫的做派。)然而,如果你知道去哪裡尋找線索的話,還是有可能破解這個密碼的。在過去,這意味著審視他的業務——各種業務。但如今,想要了解Thiel,你就需要看看他舉辦的派對、他拉攏的捐贈者以及他資助的候選人。Thiel已經對風險資本進行了一次重塑,接下來,他打算在未來幾年裡對共和黨政治採取同樣的強力措施,挑選出最有可能被形容為“三分之二像特朗普、三分之一像Thiel”的候選人。
像Koutoulas這樣的人已經認同了Thiel對自己的重塑。在捐款給Masters之前,Koutoulas承認他並沒有對前者進行“超級深入的研究”。Koutoulas對Masters的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基於Thiel的背書。Koutoulas和Thiel是很好的朋友,他們住的地方只相距15分鐘車程。Koutoulas說:“自從Peter搬到邁阿密後,他就在支援‘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方面非常活躍。”Koutoulas繼而又對各州提出了一些共和黨的標準抱怨——它們的正確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屬於哪個政黨。“Peter的基本信條是:美國真的處在一個不穩定的臨界點上。看看所有海濱城市之間的分化吧。曾經輝煌的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現在只有高犯罪率和高稅收。”
在談論Thiel這個共和黨黨魁的擁立者之前,或許我們應該從一個更名不見經傳的地方開始說起。
那個地方就是加州福斯特城(Foster City)。它離舊金山很近——向南20英里就是,但當Thiel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和他的家人剛搬到那裡時,那裡什麼都不是,只是他們從德國法蘭克福出發、途徑俄亥俄州和奈米比亞的旅程的最後一站。(他的父親是一名化學工程師。)後來,Thiel在斯坦福大學讀了本科,上了法學院,然後在Sullivan & Cromwell律師事務所短暫工作過,90年代初又在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做過衍生品交易員。隨後,他決定更願意為自己工作,於是在1996年,他創辦了Thiel Capital,幾年後又創辦了對沖基金Clarium Capital。在金融危機之前,Clarium Capital的年回報率為30%(扣除費用)。它採用了一種新穎的經營模式,即每年收取25%的利潤,如果虧損則不收取任何費用(而不是傳統的20%和2%的方法,這種方法讓對沖基金的所有者在漲跌的年份都能賺到錢)。Thiel寫給投資者的信聽起來是這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傳統智慧已經不奏效了的時代……那些把自己限制在過去看似正常和合理的東西上的投資者,對他們現在身處的充滿奇蹟的時代毫無準備。”
在創辦Thiel Capital和Clarium Capital的間隙,Thiel還創辦了一家初創公司——他和聯合創始人Max Levchin最初將其命名為“Confinity”,也就是今天的PayPal。“一張20美元的鈔票的流通率是6,也就是說在一年時間裡,有6個人平均每人持有這筆錢兩個月。在數字世界裡,每當這些人中有一個把錢轉給我們,我們就會得到新客戶,”1999年,Thiel曾經這樣告訴《福布斯》說。他和Levchin在2002年2月將PayPal上市,8個月後又以15億美元的價格將其賣給了eBay。Thiel賺了5,500萬美元。
三年後,Thiel又創立了另一個投資工具,創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透過創始人基金和他的其他公司,Thiel積累了許多在過去15年裡具有重要意義的公司的股份:Space X、Lyft、Airbnb、Spotify、Stripe、ZocDoc和LinkedIn。(他還抽出時間與人共同創辦了監控軟體公司Palantir,雖然該公司目前備受爭議。)
不久之後,投資者Thiel就為自己建立了一個相當好的業績記錄。這個業績幫助他完成了眾多交易,當然他願意放棄矽谷的規則也是原因之一:對於那些由創始人擔任執行長並執掌大權、對公司保持經濟和投票權的初創公司,Thiel沒有任何不滿。雖然沙山路(Sand Hill Road,矽谷的VC一條街)上的守舊派並不喜歡這樣,但如果他的競爭對手想要跟上他的步伐,他們也必須進化,拋棄對執行長進行制衡的偏好,以保護投資。Breyer Capital的創始人Jim Breyer表示:“Peter的做法從根本上改變了風險投資業的性質。”(他已經與Thiel或他的公司一起投資了十幾次,包括Facebook。)“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是非常健康的,但其他人可能不覺得這是一種積極的變化。”
透過LinkedIn創始人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Thiel聽說了另外兩個年輕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他很喜歡他們的想法——Facebook——並立即投入了50萬美元,佔股3%,還加入了Facebook的董事會。Facebook當時正在摸索自己的發展方向,致力於增加一些我們現在認為是其基本特色的功能:動態訊息、通知以及大學生以外的使用者訪問Facebook的許可權。在當時以及接下來的幾年裡,Thiel對Facebook的影響不可能被簡化或低估。
“你知道,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董事會成員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他們應該具備精明的商業頭腦,對公司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且保持真正獨立的,”前《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Don Graham回憶說,他也曾經向Facebook進行了投資,並與Thiel(和Breyer)一起在該公司的董事會任職。“Peter對這家公司投入頗多,他非常努力地促使這家公司成功。我認為Peter既寶貴又聰明,馬克把他留在那裡是非常、非常明智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Thiel並不介意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並享受了幾年把他描繪成一個投資天才的公眾形象(雖然有些另類)。2015年前後,情況發生了轉變,似乎是受到兩件事的推動:名人八卦網站Gawker和特朗普。媒體嘲笑他是導致Gawker網站倒閉的誹謗案的幕後推手。(該新聞部落格網站在2007年揭露了Thiel是同性戀,讓後者大為光火。)2016年初,在共和黨的保守支持者支援特朗普之前,他就宣佈支援特朗普參加總統競選,這讓有關他的新聞頭條變得更加黑暗。那一年,Thiel向支援特朗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100萬美元,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捐款20萬美元。這引發了媒體和Thiel的同行對他的廣泛批評。後者之一就包括Netflix創始人裡德•黑斯廷斯(Reed Hastings),他同時也是Facebook的董事。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道,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Thiel:“我對你支援特朗普當我們的總統感到很困惑,對我來說,這已經從‘不同的判斷’變成了‘錯誤的判斷’。”
特朗普贏了,Thiel卻退出了公眾視野,雖然他對這位第45任總統的支援沒有太大的動搖,並且他在特朗普的白宮的活動也足夠頻繁。但對Facebook來說,特朗普的勝利代價高昂。從特朗普當選到今天,你可以追溯到一條該公司被內容稽核的爭議和其他問題所吞噬的相當直接的路線,這在去年的告密者洩密事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並且這些事件充滿了矛盾和複雜性,最明顯的事實就是,Facebook(Thiel幫助創立的公司)需要將特朗普(Thiel幫助當選總統的人)從其平臺上禁止。
如果沒有Thiel的直接表態,我們不可能確切知道為什麼他認為自己應該在現在離開Facebook,而不是在2016年之後或上次總統選舉之前。或許Facebook驅逐特朗普(他的夥伴)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又或許,這只不過是在共和黨失去國會和總統職位之後,Thiel覺得現在是時候給它踩油門了。(Facebook也沒有說太多。扎克伯格在宣佈Thiel離職的宣告中表示:“Peter一直是我們董事會中一名有價值的成員,我對他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深表感謝。”)
據《Trump World》的兩名訊息人士透露,顯而易見的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這些年裡,Thiel在保守人士圈裡的知名度大幅上升。在這個圈子裡,對特朗普的忠誠是必須的,而共和黨超級富豪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的死給這個圈子留下了一個影響力真空。
“他是一個如此深刻的思想家和戰略家,他的思想比大多數人領先20年,”創業公司投資者、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的前助手Darren Blanton說。“Peter Thiel一心想讓美國重新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Thiel正在資助像J.D. Vance這樣的人,後者正在競選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席位。Vance的想法與Thiel的非常相似。Vance第一次見到Thiel是後者在耶魯大學一次演講的時候,Thiel認為常春藤盟校(就是他和Vance都上過的那些學校)並沒有幫助學生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2017年,Vance開始為Thiel的Mithril Capital投資基金工作。三年後,Vance從Thiel等人那裡為自己的基金Narya Capital籌集了近1億美元資金。“Narya”也這個名字和Thiel的許多公司一樣,都是取自《指環王》(Lord of the Rings)一書。Vance和Thiel還都投資了右傾的影片平臺Rumble。他們的政治訴求和他們資金一樣保持著一致:以美國為中心的外交政策,更少的政府開支和更嚴厲的移民政策。
在下一屆大選之前,Vance正在為共和黨的初選進行激烈的競爭。一位競爭對手在俄亥俄州的電視上播放了Vance批評特朗普的一些舊推文的廣告。Vance後來刪除了這些推文,試圖和Thiel和特朗普站在一邊。最近,他還利用Twitter為他和Thiel主持的一頓價值10,800美元的晚餐做廣告。

還有Masters,就像特朗普可能會說的那樣,他似乎直接從中央選拔賽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一名Thiel支援的候選人。與Vance、Thiel和特朗普一樣,Masters傾向於更嚴格的移民規定和更少干涉主義的外交政策。和Thiel一樣,他也100%支援特朗普再次參加總統競選,並在一月份發了這樣一條推文:

和Thiel一樣,他也迅速抓住了新興技術的前景。Thiel創辦的PayPal有著最早的數字貨幣,Masters則善於利用NFT。去年12月,Masters以5,800美元一個的價格出售了一批限量版NFT;這些NFT是《從零到一》(Zero to One)的數字收藏版。《從零到一》是他與Thiel在2014年合著的一篇關於初創公司的論文,雖然廣受歡迎,但寫得相當抽象。除了NFT,買家還將獲得獨家邀請,參加由Thiel和Masters主辦的派對,並進入一個私人的Discord小組。他總共賣掉了99份NFT,籌集了57.4萬美元,這也是全美第一個將NFT用於政治的事例。
將特朗普主義與加密貨幣相結合是他們贏得了James Koutoulas的原因之一,這位對沖基金經理出席了Thiel在邁阿密主辦的募捐活動。“我們這個國家缺乏深思熟慮的加密貨幣監管......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Koutoulas說。“為了讓美國繼續成為金融領導者,我們需要找到一條使加密代幣和NFT合法化的途徑。”
現在要知道Vance和Masters是否會獲勝顯然還為時過早,畢竟在過去幾年裡,並不是每一位Thiel支援的候選人都取得了勝利。去年,他花錢最多的人輸了:Chris Kobach競選參議員失敗,100萬美元付諸東流。(作為堪薩斯州的州務卿,他制定了一些全美最嚴格的選民登記法。)在華盛頓州,Thiel給州長候選人Loren Culp的捐款要少得多(2,900美元),後者的競選活動也出現了螺旋式上升。在失敗後,Culp以特朗普的方式做出了回應,即起訴所謂的選舉違規行為。訴訟沒有獲勝,但他的新努力——對眾議員Dan Newhouse的初選挑戰獲得了特朗普的支援,Newhouse是1月6日國會山事件之後投票支援彈劾特朗普的為數不多的共和黨人之一。
向Vance和Masters提供2,00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可能足以使參議院落入共和黨手中,這對左派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局面。Thiel的支出讓民主黨人感到不安,因此他們正在四處尋找自己的金主。但Salesforce的執行長馬克·貝尼奧夫(Marc Benioff)仍在作壁上觀,這是他在2018年收購《時代》(Time)雜誌後許下的誓言。LinkedIn的雷德·霍夫曼也只貢獻了Thiel大約十分之一的政治獻金,這引發了人們對他是否對2020年在拜登總統身上投入巨資的結果感到滿意的猜測。(貝尼奧夫和霍夫曼對此都不願置評。)
“在共和黨陣營中,很難有比Peter Thiel更精明的捐款人了,所以我確實認為,一個無拘無束的Peter Thiel是我們需要非常、非常需要擔心和非常警惕的物件,”加州民主黨高階工作人員和籌款人Cooper Teboe表示。不過他預計該黨最終會團結起來:“我認為這種擔心不會得不到回應。”
但是就目前而言,如果你和Peter Thiel坐在泳池邊,你就可以清楚地聽到右翼人士清晰且資金充足的反對答案。
譯 Vivian 校 李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