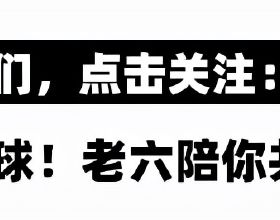——田山花袋《棉被》讀後感
◆程千凡
思前想後,感覺無從下筆。幾經努力,最後還是略有強制地讓自己伏案在電腦前敲打這篇讀後感。田山花袋的小說《棉被》,似乎與我以往所讀的日本小說不同,業界稱是一本“私慾小說”,其作者也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性代表性人物之一。
我購買的日語小說《棉被》,是魏大海翻譯;青島出版社出版,2021年3月第1版的。購書的時候,我對作者和書籍內容的瞭解幾乎都是空白的。應該說,這個標題吸引了我。“棉被”,看起來是每一個人都曾有過的睡具,但圍繞著這個睡具的軟硬、薄厚、大小、以及擺放位置和進出人物,只要肯於浮想聯翩,都知道這裡面不知會有多少故事,一種閱讀的慾望之火也會因此被點燃。別裝,誰不想知道一具“棉被”背後私人空間的故事呢?
我和中國很多讀者一樣,比較熟悉的日本作家是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三島由紀夫、森歐外,中島敦、北野武、東野圭吾、村上春樹等等........此次有幸閱讀小說《棉被》,讓我又多認識了日本一位新作家田山花袋。據說,他1907年發表的《棉被》,堪與歐洲的那位盧梭的《懺悔錄》相比,也被公認為是作者本人赤裸而大膽的人性懺悔錄。他也因此成為日本文化“私小說”的第一人。我個人的理解是:與其給這類作者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籤,不如說他們是敢於把人們靈魂隱蔽深處不敢表現出來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他們的見識、他們的觀察、他們的思維、他們的臉面、他們的魄力與行為擔當,都不是一般文人與作家所能夠有的。不要看現在有的作家視似性格光明筆端犀利,有的作家膩膩歪歪欲言又止字字行行背後不知有多少抒發不出來的幽怨,還有的作家有那種顯然帶進冰冷墳墓的內心鬱結,其心境的暢快與情感的爽快程度,都與奉行自然主義的文學家們是無法相比的。這些作家因為顧及重重,即寫不了那麼“露”,也寫不出那麼“深”,從而讓自己懸在空中,成為了日本文學界的一個“工匠”,或者叫做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話說《棉被》吧,這是一部中篇小說。開篇講到35歲男主角“竹中時雄”,那是一位文學追求者,受小出版社的囑咐幫助編輯地理圖書,但內心並不情願,因為他依然保留著有朝一日成為名家的願望,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初心”。精神的追求常常帶來精神的空虛。在他妻子懷孕第三個孩子的時候,新婚的審美快樂已經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厭倦了妻子那張永無變化的臉以及單調日常生活,感覺自己也寂寞得近無容身之地。讀到這裡,我就回望中國男人。在現實生活中,似乎中國的男人,三十四五歲的時候也都會這樣充滿煩悶。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七年之癢”,也是夫妻離婚率最高的時期....。也正是在這時候,《棉被》中的主人公竹中時雄收到了一封來自充滿崇拜之情的粉絲的手簡,這位粉絲就是女子大學的學生“橫山芳子”,芳子來信懇請竹中時雄幫助修改文章,自己也願意成為女弟子。從此,竹中時雄把所有的思緒轉移到這位粉絲身上,最終結成師徒關係。
竹中時雄那孤獨的生活被芳子打破了,生活又增添了一番蜜意,猶如新婚時期快樂,然而礙於師道的尊嚴和家庭的道德,雙重倫理關係的重壓下他又有許多難以啟齒的,唯有隱忍。此時,芳子真的陷入了一場熾熱的戀情,竹中時雄也不得不行動起來,不由分說地寫信與芳子的父親。他作為溫情保護者,希望獲得芳子的歡心,當然他也期望芳子的父母極力反對,這樣他就可以“甩鍋”。這位三十五六歲的日本男人,心中咀嚼著生活中最深的痛苦、感受著事業煩惱,還有那無法滿足的性慾,以及內心苦苦支撐這種壓迫的不堪。女弟子已經是他的鮮花,是她的食糧.......女弟子的美已經無以言表了。落入俗套的是,芳子的日本父親沒有翁帆父親的格局與大愛,他硬是把芳子接回鄉下,硬是活生生地親手拆斷了這對伴侶。芳子的離去,讓竹中時雄感到悲哀,感到絕望,感到那種還未能釋放的愛慾,他抱起芳子蓋過的被子,把臉埋藏在冰冷的並有著兩人氣味的被子裡,縱情哭泣不已。
這種感情,僅僅是一種性慾,還是一種愛情?那些相互表達感情的信函,證明了兩人非同尋常的關係,正因為家有妻小,估計社會的輿論對“師生戀”的壓力,兩人最終才僅算“試水”而沒有墮落愛情的陷阱......
愛情一旦被打碎,呈現出來的就是悽美;既往的情感猶如疾馳的列車徐徐駛入終點站的時候,生活還是要按部就班落入俗套的。這是不是所有文學青年一路小跑走來的內心之痛呢?那些理智者,不在我這篇小文的討論之內。
最後,我想呼應題目:激情“棉被”擋不住道德的重壓,自然主義的描寫不過是一種養眼的景觀。
【作者簡介】程千帆,河南人。走遍中國大江南北,愛讀書,還愛像喜歡文學的高中生一樣寫讀後感。在《日本華僑報》開闢“東讀西看”專欄。有一點點經營能力,但常常在自己任性的理性主義情感下讓位於“文”。